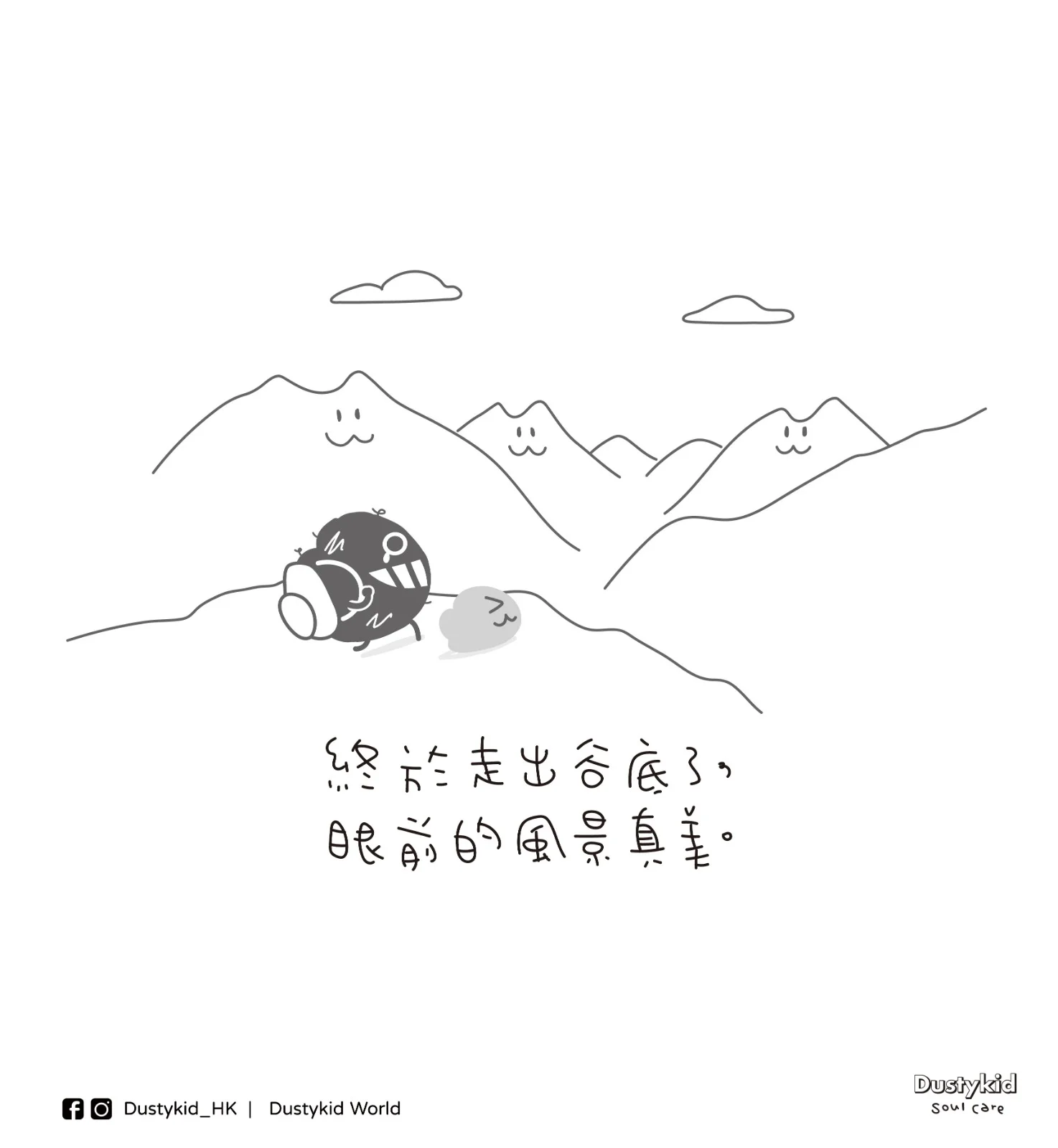我們到達國家兩廳院的時候,離表演的開場時間還有半小時,並不足夠讓我們去吃一頓輕盈的餐點。
「你有多餓呢?」
我需要一杯暖乎乎的牛奶或米漿,最好還有一碗湯。S的餓度則有百分之六十。
飢餓是從心臟下方伸出的一隻慌忙地要抓住什麼的手,我無法控制或抵擋那隻手,因為胃部是一個無法以腦袋分析的器官。
終於,在進入演奏廳之前,我們信步走到一家售賣茶葉蛋的小店,像快要溺斃的人抓住了浮木。我們坐下來,逛了半天的腿終得到休息的機會,而空虛的腸胃因為有五香的蛋的滋養,身體所有緊繃的神經都放鬆下來。我一邊咀嚼茶葉蛋,一邊提議:「我們來玩一個遊戲,從此刻開始,到小吃時間完結,我用H城語跟你說話,而你用台語回答,看看我們能否理解對方在說什麼。」
自我們認識以來,用作溝通的橋樑,一直都是共通的普通話,除此以外,雙方都不諳彼此的方言。語言是文明世界的規則,也是人類共處的表相,向對方擲出他聽不懂的我的母語,同時接住對我來說全是陌生音節的台語,這根本就是一個重返本能的遊戲。褪去了語言的表相,以及日常的共處的規則,人和人之間還可以依憑哪一條通道抵達對方?這樣的管道真的存在嗎?
由S先發球,我聽到充滿異國音調的句子,搜遍每個字詞,沒有音節能對應我可以聯想到的內容,沉吟半晌,正想放棄宣布投降,內容卻從我的肚腹深處湧現──不是從理性分析的語言轉譯,而是用另一種類似皮膚的觸覺去感受說話背後的意思。
「你問我茶葉蛋好唔好食?」我說。
他聽懂了,同時笑着點了點頭。
我再拋出了另一句H城語問題,他即時明白,而且從嘴巴裏跌跌撞撞地吐出了一句H城語答案。我說:「你講得很標準。」他有點得意,腔調歪斜地再講了幾句我的母語。

看着S順利駕馭H城語時,浮現在臉上的類近旅遊者在異地生活時出現的恍惚神情,我想到,他的語言適應力比我強,如果極端狀況忽然降臨,他必然可以仰賴這種能力生存下去。
譬如說,大量執法者突然把我們包圍,說出一種我們都聞所未聞的語言;或,我們因為不知名的,始料不及的原因,陷落在某種險境裏,各種語言(無論是從人的嘴巴裏吐出,或是動物的嘷叫、天色、樹葉碰撞的聲音、風向和海浪代表的意義)都需要記憶力、組織能力和邏輯去穿破和解讀。
我想起普利.摩李維的集中營回憶錄《如果這是一個人》裏提及的日常生活狀況──二戰時期被納綷德軍抓進去種族清洗順道強迫勞動的猶太人,如何能得到倖存者的身份,其中一項條件,即是其語言能力。在集中營裏,看守者來自不同國家,也說着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法語,以至意大利語,他們當然不會遷就在囚者的語言。要是囚犯,尤其是剛剛進入集中營,仍然深感錯愕,對於眼前的新世界規則一無所知的被囚禁者,不知道看守者對他們下的指令、勞動的細節、領取食物的地點⋯⋯他們很可能就是第一羣白白犧牲的人。在極端的例外狀況裏,安然無恙的機會,本來就是留給位於階級或運氣頂端的人。
而人常常都有着極大的機會,墮進各種例外狀況。肉身和世界,或許都由無數流動的粒子組成,這些粒子每刻都在流動和變更。佛家的語言,說這是因緣聚合。許多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事(例如明天清晨依舊能如常從睡夢中醒來),其實都是奇蹟──本來自由流動的粒子,又以相同的方式重新組織起來,形成了一個「一切如常」的畫面。但只要其中一顆粒子飄到另一個方向,這些粒子重新組成時就會出現另一個形狀(例如一次由地殼板塊移動所形成的地震;在一個擠擁的場所裏,其中幾個人不慎滑倒而令在場的人骨牌般倒下;或在街角突然鑽出來疾馳而至的把幾個人撞到半空中的車子),我們都會被突然丟到荒漠般無望的境地裏。在日常生活裏,人們常常忽略的一種正常不過的狀況,就是無常。
「捉要死/捉要死/擱生擱有咧/一隻鳥仔/三更半夜暝找無巢/不知要怎樣」我們吃過茶葉蛋後,坐在兩廳院的演奏廳,台上的歌手演唱其中一首日治初期人民生活苦況的民謠〈一隻鳥仔〉。
台語歌詞,哀傷旋律,先由男中音獨唱,接着,眾歌者一起用手掌半掩半拍打嘴巴發出哀音,恍如鳥巢被搗破後,幼鳥徹夜發出的悲鳴,也像是,被禁止發出聲音時不顧一切的號叫。
曲子充滿悲慟,但我們終究是幸運的。音樂會結束後,構成身體和世界的粒子,仍然是由相同數量組成了相同形狀,於是,飢腸轆轆的我們,可以趕往營業至深夜的店子,吃一頓清粥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