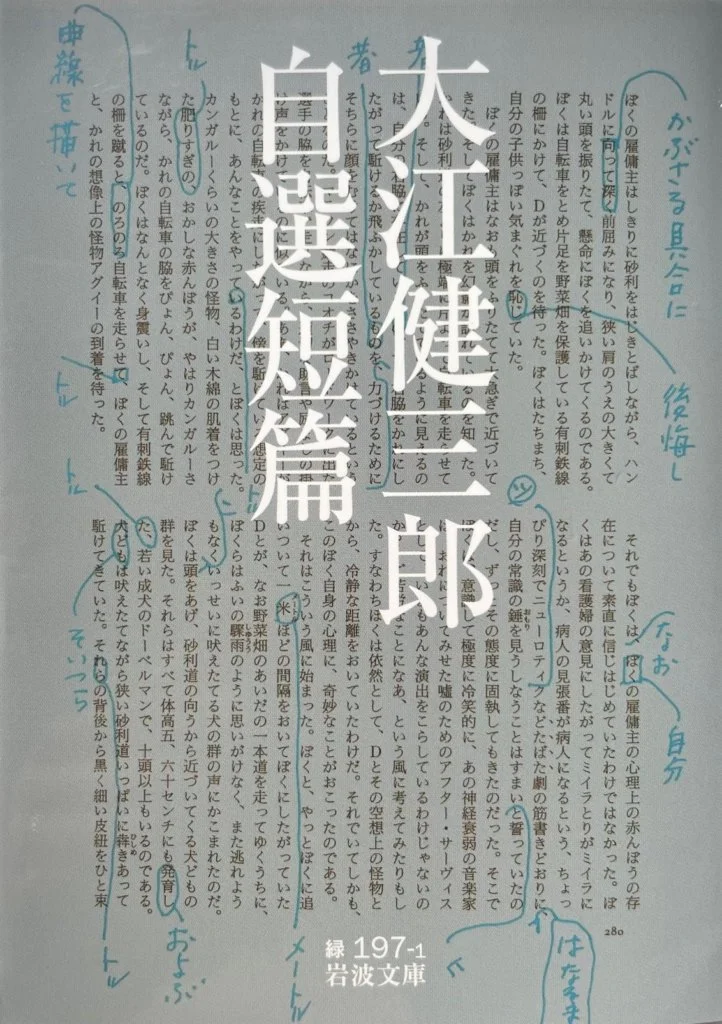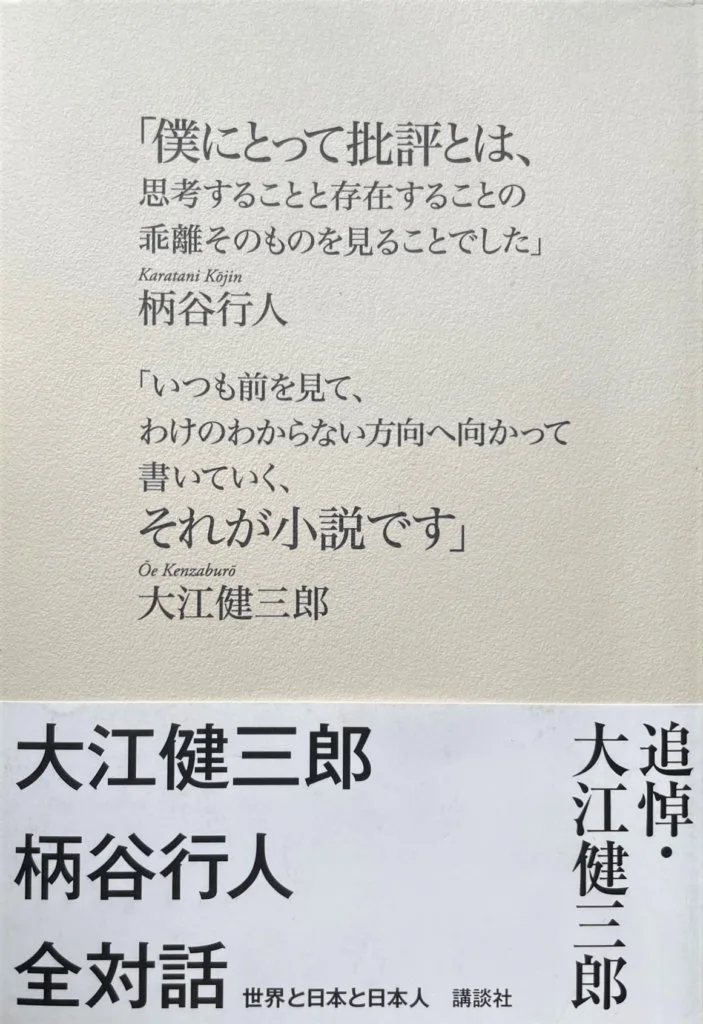柄谷行人在與大江健三郎的對談結集《世界與日本與日本人》的序言中,聲言「大江氏是第一位意識到小說終結的小說家」,而他自己則是「第一位意識到文學評論終結的評論家」。這樣的總結似乎未得到大江的同意,看起來好像是被柄谷騎劫了。
大江在文章和訪談中,雖然常常談到純文學面臨的困境,但未見他用上「小說的終結」這樣的字眼。他對新人小說家亦勉勵有加,沒有表示寫小說是死路一條。但是,縱使相信小說還會繼續存在,而好小說也會繼續被創作出來,並不等於說「小說的終結」不會發生。柄谷所說的「文學的終結」,其實是指「現代文學」的終結,即是十九世紀在歐洲確立、二十世紀傳播到世界各地的文學形式,在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前,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無法再適應時代變化的境地。這樣說的話,我認為大江應該會認同,他所參與其中的現代小說大業,已經是強弩之末。我甚至更大膽地認為,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大江已經親手把自己所代表的現代小說了結。他所解體的不只是私小說這個類型,而是小說本身。
在《大江健三郎短篇小說集》的導讀中,尾崎真理子如此引述了大江的話,作為集中作品文體的說明:「許多作家寫作是為了在其出發點上彰顯自己的個性,有些小說形式的寫作只是為了顯示『我是這樣的作家』。那些基本都是二百頁左右的作品,法國人把那種形式稱為récit。Récit的意思是敘述、在人前講述,與recital(獨唱音樂會)是同根單詞。某些作家的寫作就像是把自己最想講述的事情確鑿無誤地直接講述一般,作為那樣最初的小說就有récit。對於作家而言,那個故事或者人物只要那般描寫就足夠了。因此,他的表達已經達成,可以保證他在作為作家的路上走下去。然後我們讀者就發現了一位明確的作家……我認為那就是名為récit的小說。」
上面的引述是為了定義大江短篇小說中與作者有所重疊的「我」。而這個「我」的特性,並不是一般第一人稱虛構小說可以解釋的。不過,大江的解釋似乎也不是很清晰,令人覺得他在談論類似私小說中的「我」,也即是一種自我表現的敘述形式。大江曾經表示,自己的後期小說表面上是以自己為主角,其實是對私小說的解體。所以,他在這裏不可能反過來主張一種單純為了「彰顯自己的個性」的文體。
把récit直譯為「敘述」,幾乎等於沒有翻譯,因為廣義來說,所有小說也不外乎是敘述(narrative)。也許它的意思近似英文的retell或recount,即把真實的事再次講述。Récit是法國小說中的一個次類型,使用這個形式的代表作家有紀德(André Gide)和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根據文學評論家Roger Shattuck的解釋,在récit之中作者和讀者也自覺到敘述行為本身,並把注意力聚焦其上。作為一個小說類型,它不是平常用法中所指的、對事件的忠實報告。布朗肖這樣形容:「Récit不是事件的敘述,而是事件本身,是向事件的逼近,是事件發生的場地——事件未曾而即將發生,其中的吸引力令récit變得可能。」熟識法國文學的大江肯定深明箇中道理。
我認為如此定義的récit,不但是大江某些中短篇小說的寫法,甚至是大江晚期作品的根本模式。在一九七二年的《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中,雖然虛構程度甚高,不像作者的自然表述,但敘述者對自己在進行中的父親傳記(或同時代史)寫作,是極度甚至是病態地自覺的。對於材料搜集、記錄過程、引述方式、人稱運用,甚至是語言文字的可靠性,「作者」都以近乎妄想症的執著不斷思考。事件的真實性永不可達,而récit的行為本身就是持續進行的事件。用這樣的定義來描述大江的小說,是完全成立的。就算是表面上不像輕巧的récit而像全面的roman(法語中的novel)的長篇作品,例如完成度極高的《萬延元年的足球》、《同時代的遊戲》、《空翻》等,當嵌入整體的「私小說=共同體神話」的脈絡來看,其實就是大規模的récit——「我是如此地寫作」的展現。
最大規模的récit,當然是二千年之後的「古義人六部曲」。這批晚期作品表面上遵從現代小說的規範——人物鮮明、情節清晰、兼具個人心理和社會分析——絕對不是法國戰後「新小說」那種刻意破壞成規的作法。但是,我們始終覺得有甚麼怪異之處,令它們看來「不像小說」。那個奪取了小說之魂的東西,就是récit。首先,是「我是這樣的作家」的自覺表現,以及同時對私小說的顛覆。其次,是敘述的困難、失敗和再接再厲,所突出的「言說作為事件」的自我指涉性。再者,就是作為recital的述懷,而這種真誠的述懷是在私小說的幻影解體之後才成為可能的。這些都是揚棄現代小說之後才能彰顯的「敘述」。
九十年代中期和後期,大江在完成《燃燒的綠樹》和《空翻》之後,曾經兩度宣佈封筆,但隨即又寫出了《換取的孩子》,以及往後的五部長篇,並且不再提及封筆的念頭。柄谷非常準確地把握住這個轉折,指出了「小說的終結」。大江也在這時候停止創作短篇。他把récit的形式注入長篇,因此接下來的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小說了。然而也不是法國既有的récit,而是大江對過去的自己的引述和再引述(re-cite),也即是以不斷回顧來前進的方式。如此這般,小說來到終結。有了這樣的認識,無論喜歡與否,我們也不能詬病大江晚期作品的寫法違反讀者對小說的預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