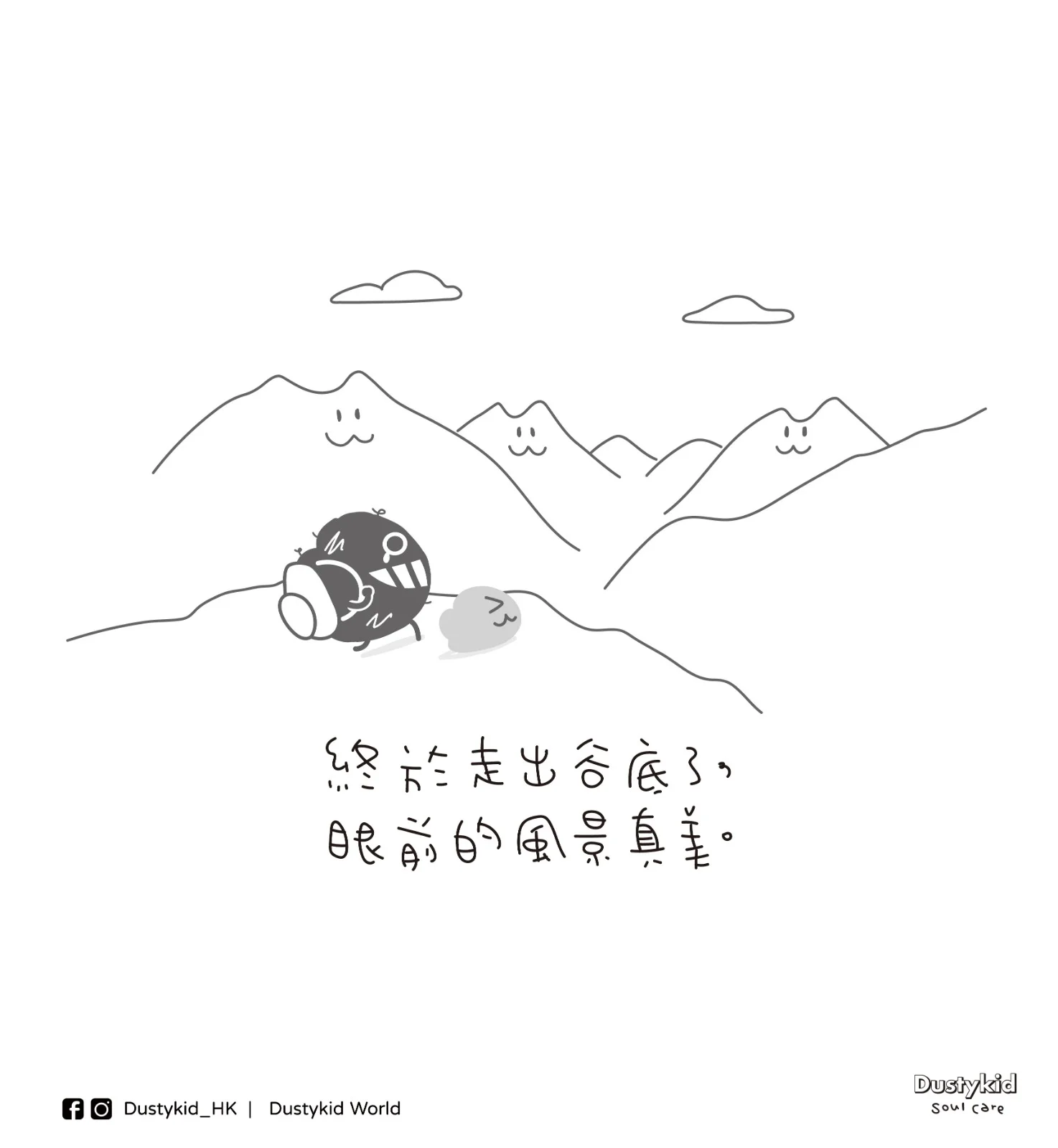森鷗外和夏目漱石並列為日本近代文學開創期的兩大巨頭,已經是近乎枯燥無味的常識。有趣的是,這兩人雖然當時已經備受尊崇,他們的文藝觀和創作方向卻和主流文壇背道而馳。自從明治中期引進西方現代文學,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成為日本文壇的兩大潮流。鷗外和漱石卻置身其外,從更高的角度思考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並以創作實踐尋找異於西方現代小說的出路。
和漱石一樣,鷗外幼時接受嚴格的漢學訓練,成年後又曾到歐洲深造,對西方文學有第一手閱讀經驗。與漱石到英國修讀英國文學不同,鷗外赴德國學習的是醫學和衛生學,但無礙他乘地利之便深入觀摩西洋文化。回國之後鷗外在軍醫部任職,同時在文學上初試啼聲,發表以留德生活為背景的浪漫主義小說〈舞姬〉,在文壇上一舉成名。那是一八九○年代初期的事情。
其後鷗外一度停止創作小說十多年。他作為軍醫官參加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到了一九○七年晉升至中將級的陸軍軍醫總監。這時候他看到同代人夏目漱石發表了《我是貓》並且大獲成功,忍不住也躍躍欲試,重新執筆寫出了接近私小說的《性生活》。以作家自身的個人經歷為題材創作的私小說,是自然主義小說輸入日本之後的變體。

再一次轉換路線的契機,是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駕崩,乃木希典大將違反禁令隨之切腹殉死。受到這件事的刺激,鷗外短時間內寫出了〈輕津彌五右衛門之遺書〉,假借歷史人物探討切腹殉死的習俗。從此便進入了歷史小說的創作,陸續寫出了〈阿部一族〉、〈山椒大夫〉、〈魚玄機〉、〈高瀨舟〉、〈堺事件〉等。經歷過早期的浪漫主義,中期的自然主義,來到晚期的歷史小說,鷗外的取向和風格變化非常巨大,當中涉及深思熟慮的文學反思。他開始對西方現代小說構造和呈現真實的方式感到不滿,對小說情節的完整性和人物的圓滿性也出現懷疑。換句話說,他對小說的虛構手段有所抗拒。但這並不是說,他想藉着歷史小說回到事實本身,或者恢復東方傳統。
人們對歷史小說的預期,其實和一般小說沒有分別。取材雖然是見諸記載的歷史事實,但採用的手法主要還是虛構的。對歷史材料提供的骨架或梗概,基於藝術上的考慮,作出增添、改動、串連、補充,構造出圓滿的人物和完整的情節,這是一般歷史小說的作法。這種作法是把歷史人物變成小說人物,在讀者面前演出戲劇化的人生。鷗外寫的並不是這種歷史小說。
初讀鷗外的歷史小說,多少會感到困惑,甚至懷疑它們算不算是小說。以〈阿部一族〉為例,歷史材料幾乎原封不動地從文獻搬移到小說裏去,乍看好像是一堆資料的羅列。每個人物一出場,必定先列出他的家族世系、名稱或名號、歷任的職位和過往的功績,簡直到了不厭其煩的地步。鷗外說這樣做是為了尊重素材的「自然」,不願隨意加以改變。不過,他會選取其中的一些場面,以精簡的筆觸進行小說化。所以不是完全沒有出於作者想像的敘事和描寫,只是限度非常低,以不破壞素材本身的「自然」為原則。也即是說,縱使存在虛構,虛構也沒有搶奪主導權。他要確保以素材方式存在的事實,不會受到虛構的扭曲。
這當然不是說,鷗外天真地以為素材就是事實本身,盡量不對素材加工就是重現歷史真相。如果是這樣的話,索性就不用寫小說了。他把這種寫法與自然主義相比較,認為私小說作家把自身隨機遇到的生活面貌寫進小說,同樣是尊重素材中的「自然」的作法。既然生活的「自然」可以進入小說,歷史材料的「自然」為何不可?換句話說,藝術不是橫加虛構、任意搬弄,而是在素材(人生、歷史材料)中發現詩意或意義,然後以盡量不破壞原貌的方式,運用準確和低限的手段加以呈現。所謂的「虛構」,是在這樣的特定層面中發生作用。歷史小說處理的不是事件的真實,而是史料的真實。
這同樣適用於歷史人物身上。我們無法知道歷史人物本身是個怎樣的人,更無法知道他們內心的真相,我們有的只是記載他們的事迹的材料。鷗外無意用這些材料來「還原」歷史人物,相反他試圖讓人物在材料中「自然地」自行呈現。超過材料所容許範圍,他寧願留白和從缺,也絕不強加個人的想像。再者,他捨棄了小說預設的「以主角為中心」的概念,讓眾多人物登場,卻不讓任何人佔據中心的位置。毋寧說,焦點隨着人物的輪番進出而不斷轉移。
現代小說的另一個重要預設,是人物的心理深度和性格的立體性。經歷過現代小說洗禮的鷗外,卻刻意反其道而行,拒絕插手人物的內心世界,只描寫人物的外部行為,據此以暗示他們的性格、情緒和動機。鷗外的高超之處在於,平面化的人物不但不覺單薄呆板,形象反而更加鮮明和深刻,而且極為耐人尋味。由此可知鷗外其實是兵行險着,故意拋棄現代小說的最強裝備,徒手上陣,以指為劍,以掌為刀,非高手不能如此。
與其說晚期的森鷗外寫的是歷史小說,不如說他破開了「歷史小說」這個概念,在「歷史」和「小說」的細微縫隙之間,尋找新的創造空間。這種既非「歷史」也非「小說」的文體,無以名狀,同時對歷史和小說作出質問。因為它太過前衛,不只前無古人,更是後無來者,成為文學史上孤懸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