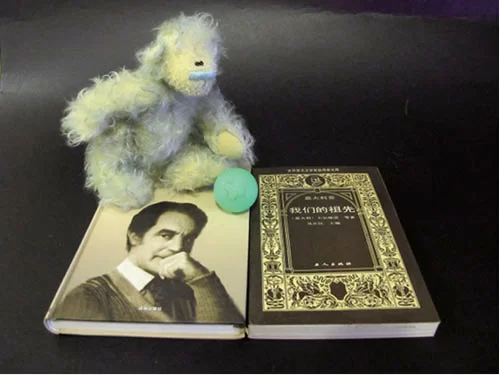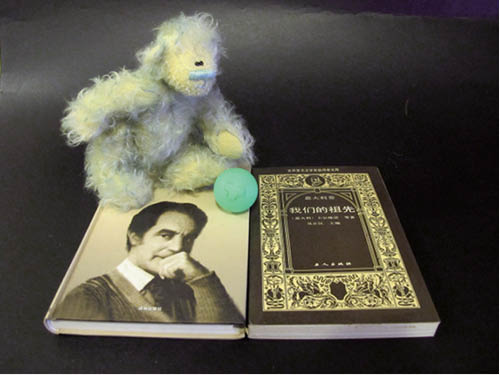
何:我並非那麼討厭摩連奴這個人,他只是乏味足球的標誌,一種愈來愈緊張,卻日漸失去快樂的遊戲罷了。他自己也是功利世界的受害者,所以他即使拿了冠軍,下一年成績不濟,就要捲包袱了。捲包袱之前,照例先和球員不和。而班主、觀眾,多年來已練成了只看成績。你看進攻足球的利物浦,曼城(領隊哥迪奧拿運用的Tiki-taka,意念是保持控球權、逼搶、地面進攻,在巴塞很成功,可一直受到義大利人的斥責),充滿趣味,阿仙奴,最好的時候也有這種趣味。對不起,你已經許多年不看足球,不看阿仙奴了。它們據說都不擅防守,為什麼不說它們入球入得不夠?比利的年代,你進我兩球,那我進你三球四球,讓你覺得自己是有機會的。當然,最好是入球又不失球,那個球隊叫烏托邦。但如果大家鼓吹防守,那就不好玩了。二三十年前是無所謂防守中場的,現在兩個還嫌不夠。
好,回到卡爾維諾的文學世界。我們要作家創新,要探險,要嘗試新的審美形式,而不是要他輸少當贏。如果你告訴我某某的小說很好,因為反映現實,我會說他寫的可能很好,不過那是報道,是雜文。對了,同樣可能是很糟糕的報道、雜文,我會再補充一句,我沒有文類歧視,但我不會認為報道和雜文優先。
西:早兩年白俄羅斯的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得諾貝爾文學獎,她寫的是報道文學,或者是紀實文學,這是諾獎本身的突破,不一定要小說家、詩人。她寫車諾比核事故,採訪當事人,寫人的無知、真相怎樣被隱藏,車諾比是人類苦難、哀痛的象徵。
何:那是不快樂的文學。
西:文學裏一直有快樂和不快樂兩條線索。不過快樂的,在過去很受歧視。比如喜劇的地位就遠低於悲劇。喜劇被視為滑稽、平庸、低俗。古希臘的阿里斯托芬,地位就比不上索福克勒斯。但喜劇並沒有消失,昆德拉、卡爾維諾起出這條不受重視的小說發展,像拉伯雷的《巨人傳》、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斯特恩的《項狄傳》、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等等。卡爾維諾到美國演講,起首就講輕Lightness,相對於重;兩者表現形態不同,價值可是平等的。而且,也不能分割。他是為輕發聲,認為輕,也有莊重的輕、輕佻的輕。
何:是的,不能二元劃分,而是相輔相成。比如王爾德的《快樂王子》,王子是沉重的,燕子則屬輕快,兩者合作,一個提供理想,一個實際執行。這童話真正的英雄,我一直覺得並不是王子,至少不全是王子,而是燕子,牠根本沒有王子那種要拯救人間苦難的沉重,牠只是幫助這麼一個愁眉苦臉的朋友罷了,卻為此輕生了。沒有燕子,王子有何快樂可言。
西:快樂的小說要寫得好,絕不容易,許多都運用戲謔、諧擬。你看差利卓別靈,再看也覺得好笑,笑,同時令人思考。是喜劇和悲劇的結合,Tragicomedy。
何:港式無厘頭是輕佻的輕,差利則是莊重的輕。我想,現實主義的作品大多是不快樂的,現代主義的呢,也快樂不起來。近年的科幻小說、科幻電影,也是充滿末世的情調,機械人不會哭,更不會笑。你被喪屍追殺,絕對不是有趣的事,你也幽默不起來。卡爾維諾也寫科幻,他不就是快樂小說的大家麼?
西:對,他從寫實開始,比較平庸,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寫出《我們的祖先》三部曲,好像長出了翅膀,才叫人賞心悅目;他用荒誕的手法表現現實,可沒有人批評他揭露義大利的現實不夠深入,變成美化現實。二戰後的義大利,是怎麼的一種現實?
何:比德國、日本稍好,因為義大利的反法西斯份子在補時反敗為勝,成為了「戰勝國」。戰後美國人要抗衡蘇共,提出「馬歇爾計劃」,義大利經濟稍稍得到支援。不過社會問題仍然很嚴重,貧富不均,充斥腐敗、不公……。
西:失業、貧困,我們看義大利的新現實主義電影就看到,新現實,就是要如實地反映社會狀況,不用職業演員,實景、自然光,狄西嘉的《單車竊賊》就是代表。但不是所有文學藝術都只能有一種內容,一種形式。那是另一種法西斯。大家對社會現實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卡爾維諾要是追隨寫實的潮流,充其量是個不錯的作家。幸好他沒有,他回到古代,回到民間傳說去,這對用濫了的做法,本身就是清新的空氣。三部曲中《不存在的騎士》寫空有一副盔甲的騎士,內裏沒有實質血肉,只憑意志「存活」,是思考存在的問題。我認為長篇的《樹上的男爵》是義大利二戰至今最好的作品,當然還有後來的《看不見的城市》、《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樹上的男爵》寫一位少年因為反抗父母,拒絕吃蝸牛餐,爬上樹上,誓言不再下來,卡爾維諾並沒有把反抗擴大為對整個不義的社會。初看時還嫌這少年過於激進,輕許諾言。
何:要批評的話,可說他的反抗只表現個人主義,高高在上,沒有組織一個蝸牛聯盟,揭穿人蝸鬥爭的本質。對,據說沒有挖出這個唯一的本質,就不能撼動世界的靈魂。
西:少年果然從此再沒有下來。他在樹上讀書、思考,談戀愛,還對抗海盜,和樹下哲學家交流。他仍然參與人間事務,卻保持一個距離。他從一棵樹跳到另一棵樹去,遊遍了歐洲。這是另一種生活方式,生活從來不是只有一種方式。讀這樣的書,我們不單要中止懷疑,更要擱置道德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