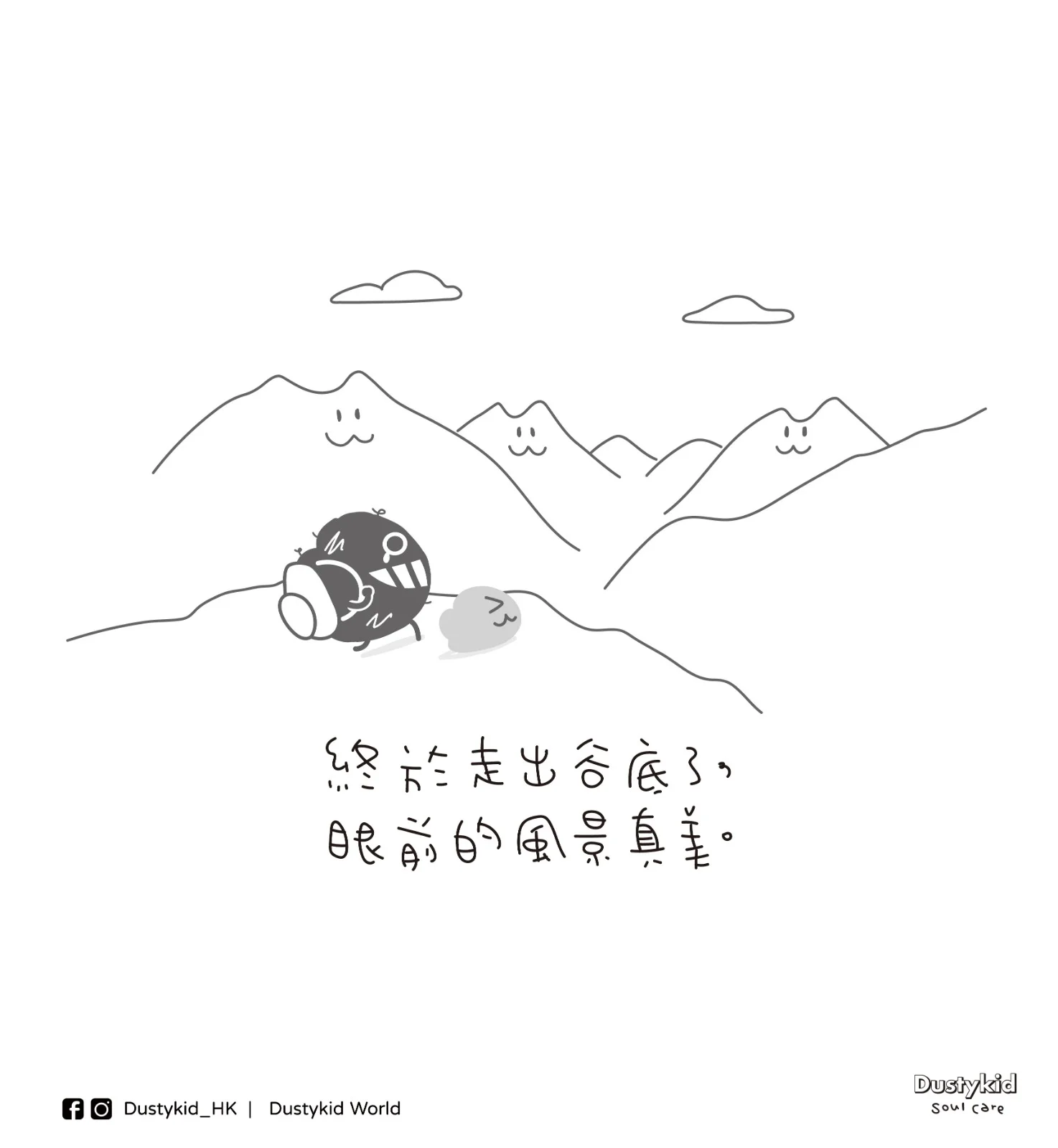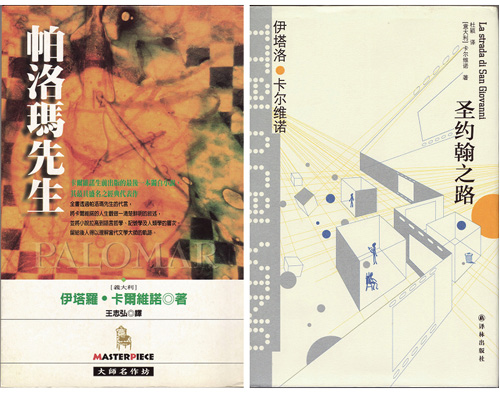
西:西西
何:何福仁
何:想譴責社會現實的讀者,如果不是通過報道、雜文、政論之類,而是通過小說,有時會找到了,大多時候恐怕是上錯了車。上錯了車,其實可以看到外面不同的風景,要是堅持要看想看的東西,於是大感失望,很不滿意,那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自己設定了路線,指定了風景。這難道是車的問題?好了,當所有車輛都必須按照規定,走一條指定的路線,看指定的東西,那時候,車輛只是機械運作的工具,它是載體,只是載體而已,無關審美。尊貴的讀者,你會因為乘車而快樂起來?你是否還會有發現的驚喜?
西:卡爾維諾是輕逸的小說家,這是他的長處,有時也會像科學家那樣,描述時好像拿起手術刀,寫各種自然的題材,也寫得好,但我始終覺得,他最好的作品是虛構、想像的小說,是探索、開拓叙事方式的小說,我讀他的這些作品,感到很快樂,我以為他也是寫得很快樂的。那是如魚得水的快樂。可是寫作《宇宙奇趣》的後期,卻愈寫愈沉重;到美國去演講,構思六個講辭一定成為他很大的壓力,看來吃盡苦頭。他告訴Gore Vidal,他到哈佛,打算用英語發言。Gore Vidal認為他的法語、西班牙語都很流利,獨是英語,其實結結巴巴。當然,是否自討苦吃,也許是我主觀的想法,我想像他游出了不屬於自己的海域,他勇敢地游,努力地呼氣。他很莊重,他的輕,是莊重的輕。但輕可要有一種放鬆、即興、流水行雲的意趣;而飛翔,必須扔下過多的行裝。否則就變得難以承受的重。
他顯然跟博爾赫斯那種圖書館作家、詩人不同,你看博爾赫斯,同樣的講座,多麼揮灑自如,隨口背詩,即使背錯了也沒有關係,沒有人會怪他,並不因為他失明了。他很輕鬆,聽眾也很輕鬆,也難得他會記錯。他好像不用怎樣備課,都在腦海裏。
何:他當然有腹稿,真是名副其實的腹稿。
西:對,他也是莊重的輕。中譯卡爾維諾的《宇宙奇趣》包括《宇宙漫畫》12篇,以及《零時間》11篇,這是我們一般讀到的,其中《宇宙奇趣》的主角是Qfwfq。後來加入了《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8篇;《新宇宙奇趣》2篇;以及《一個改編的宇宙奇趣故事》,共11篇。收集起來,有34篇之多,於是總名《宇宙奇趣全集》。在《零時間》最後一篇《血.海》,Qfwfq在交通意外中死亡。故事到此失去趣味了。好像我們讀《三國演義》,關公一死,再看不下去。卡爾維諾的植物學有家學淵源,投向科學,譬如天文學,可說是一種回歸,可這麼一來,就要求準確,知識上、邏輯科學上的準確,這就多少離開了想像,或者知性在一頭重了,感性在另一頭輕了,看來同時逐漸遠離了快樂的寫作了。不過也可能是他反而獲得快樂也未可知,因為寫什麼,怎麼寫,是作家的選擇。又或者他喜歡挑戰,他為什麼要討好我們。只是讀者如果不懂宇宙學、赫羅圖、天文學的術語,其實難以追隨。
他生前最後一本書《柏洛馬先生》,寫柏洛馬在大自然的種種觀察,從微觀到宏觀,又從外而內,這裏沒有虛構,沒有天馬行空的想像。那是對具體生命的肯定、頌歌,最後,自然而然,寫到生命的死亡。他的寫法有點人類學,令我想起蓬熱(Francis Ponge)、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喬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這些法國小說家,我稱之為「格物派」。
何:《禮記》說,我先翻一下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但文學裏的「格物派」和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並不相同,合理的人欲,何嘗不是合情的?法國人尤其不會「去人欲」。
西:格物而已,細緻地觀察,用心地考究,然後化為感性的筆觸。他們的年紀比卡爾維諾稍長,可算是同輩。卡爾維諾曾談及他們,可能受他們的啟發。我記得他寫的動物,長頸鹿、烏龜、白色大猩猩、爬蟲類。他寫墨西哥參觀古蹟時,有導遊講解一切文物,而一位帶學童來的老師,對各種文物則說:它們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世上的物事,我們不知道的,的確有許許多多。
《我們的祖先》中在樹上飛翔的少年男爵、盔甲中輕盈的精靈失蹤了,我想,巴黎那快樂的隱士多麼令人懷念呢。
他遺留下的文集《聖約翰之路》中,他又顯得多麼活潑,書中最後的一篇《昏暗中》,他獨自在這傾斜的世界想向哪裏走,怎麼走?他一段一段地獨行,每一個分段都沒有標點符號,直到最後,終於出現一個句號,我們這就失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