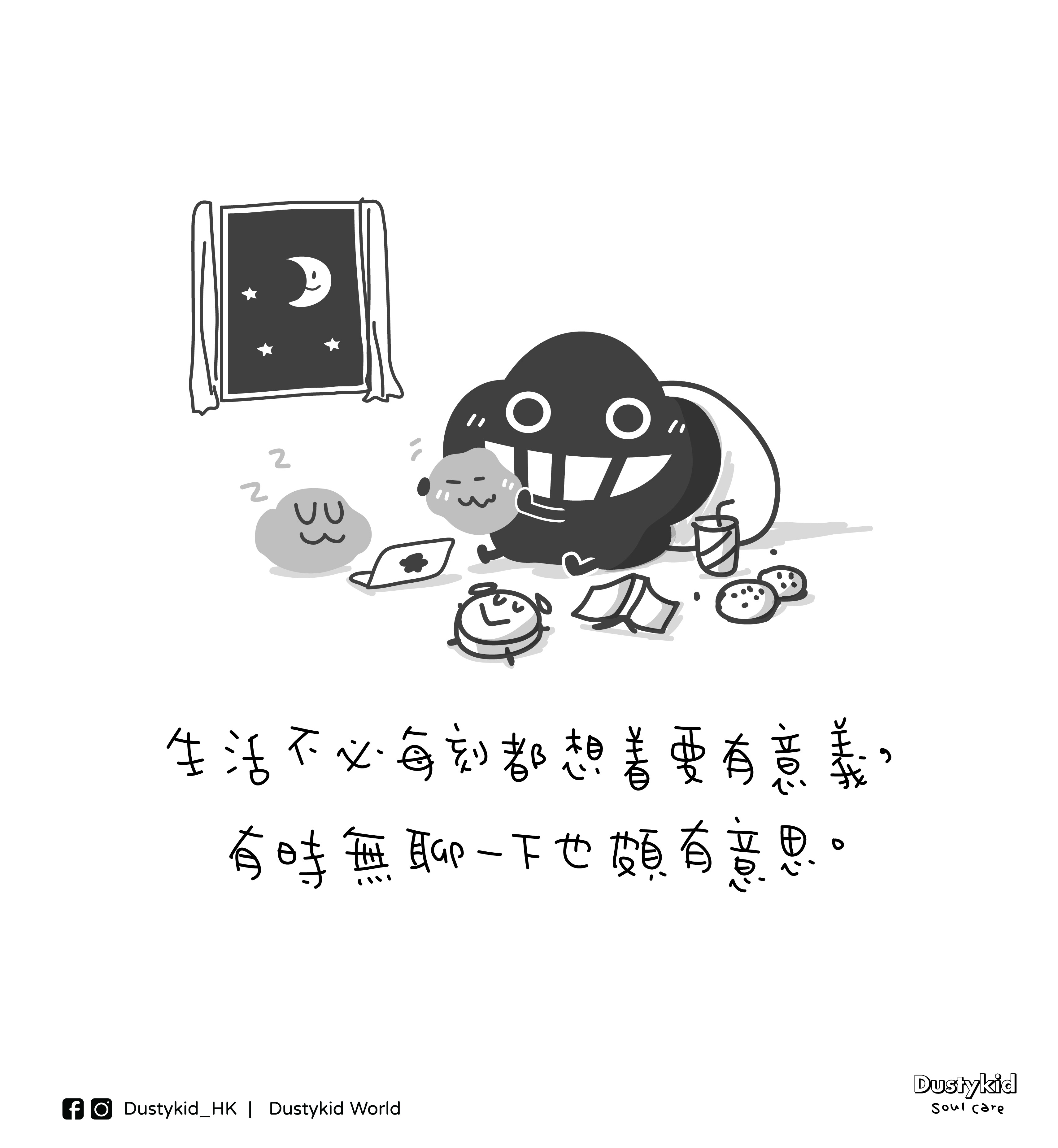S駕着阿紺到機場來接我。
阿紺是一輛墨藍色的車子,至少十五歲,以車子來說是一個資深的年齡,而且它有一個老靈魂。據說,坐在副駕駛座上的乘客,即使是第一次踏進車廂,也會得到阿紺為他/她點播的別具意義的音樂。不止一次,當乘客驚嘆被阿紺的隨機播放系統擊中內心深處的回憶,S臉上就會出現饒有深意的笑容。這樣的事,不止發生了一次。
無論是S或阿紺,都能以一種難言的直覺,不動聲息地讀懂坐在他們身旁的人。一個人的車子,其實是他投在地上的影子。一個人要積聚許多能量,才能豢養自己的影子,讓那個影子強大得可以盛載別人。因此,當朋友駕着車子來載我,我總是既感恩,同時在心裏猶豫。接載當然是一種慷慨的贈與,而進入一個人的影子,其實是一件冒險的事。

幾年前,當我仍然住在那個偏遠的小島,母親有時來看我或替我照顧獨留家中的貓,從城巿中心轉乘巴士幾次,再走路十五分鐘才到達。那是生命中唯一一次,我慎重地考慮去考一個駕駛執照,再買一輛車,以便接送她。可是朋友勸阻了我:「公路是另一個你無法適應的社會。」或許,我的影子終究是稀薄的,像《海邊的卡夫卡》裏,可以跟貓溝通的中田。幼年時遇到的家庭暴力,令中田的影子逐漸失色,終於成了被排拒於社會,卻得到自然界直覺力的脫序者。
疫情持續的三年,我都沒有見過阿紺,畢竟,S和它居於另一座城巿。無法搭飛機到外地的日子,我時常想起那些前往T地拜訪S的旅程,阿紺載着我們從台北到宜蘭,到台中,去阿里山,前往花蓮,去苗栗,跑過許多高速公路,甚至乘着颱風,從東部回到北部。很長的車程,除了斷續的、瑣碎的、深刻的或幽默的對話之外,我有時也會累得在車上睡去。直至在某個醒來的片刻,S帶着微微驚訝地問:「你這麼信任我(的駕駛技術),可以在我的車上熟睡。」
可以走進一個人的影子,被那人帶着前往某個目的地,確實需要信任,更準確地說,是對自身的信任。駕駛是一種能力,而被承載也是。一個人必須相信自己無論如何也是安全的,才可以相信別人,並且安居於不同人的影子。
即使身在自己居住的城巿,如非必要,我不會獨自乘搭計程車,對於跟素未謀面的人單獨共處於同一個車廂,我總是無法自在。當我在島上居住時,某夜,我打算步行十五分鐘,到超級巿場購物,卻被剛下班的保安員攔截,他無論如何要載我一程。我不好意思告訴他,即使我們每天見面,但我們還沒有相熟得可以令我安心坐上他的車子。當我戰戰兢兢地坐在副駕駛座,才發現那輛車子豪華得令我不敢相信,他有時要在保安室內,被上級以粗言穢語高聲責罵。他對我說,我令他想起當畫家的女兒,而他的妻子臥病多年,他的車子就是為了要接送她。
或許他需要一個聽眾,畢竟,影子就是一個人的心室,就像《Drive My Car》裏的家福。喪妻後曾經獨自待在自己的影子裏的家福,後來遇到擅長駕駛而且非常安靜的女司機美咲,才放心地,把自己的影子交給她。她讓他可以在自己的影子內休息,他們在他的影子裏交換秘密,然後,他和她終於可以走出彼此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