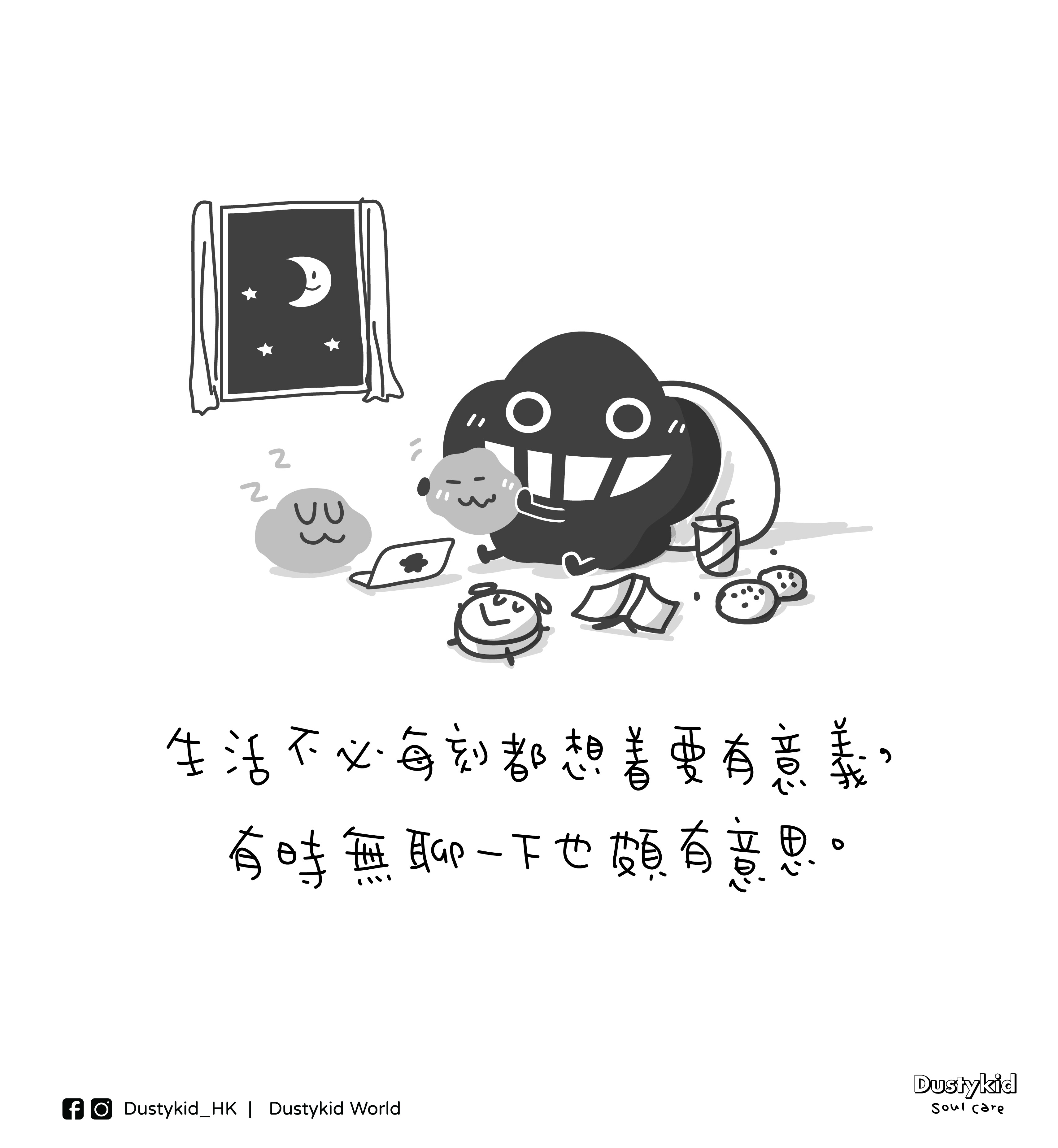她並不是因為需索無度,而要求他把她狠狠地綑縛,以彌補他讓她感到的疏離或冷漠,而是,移除了牙套以後,她才能肯定,愛只存在於某種緊張和強迫之間,那種要把人推向極限的力量──就像把一顆歪斜了多年的牙齒,推向那個應該,卻違反了它先天傾向的位置。
那是岩井俊二的《愛的綑縛》裏的妻子,她不由自主地綑縛身邊的一切,杯子、椅子、書、剪刀、甚至是,門。其實她最渴望綑住的是,無法緊捏的東西,例如空氣,以及和愛人之間所有不可名狀的。最後,她要丈夫用力地把她縛在牆的角落。當麻繩緊纏着她的皮膚,彷彿,皮膚和肉之間的空隙就被填滿了。實在,妻子並沒有發瘋,只是在愛裏的人會比正常狀態更清醒,稍一不慎就洞穿了虛假的表相,滑落到愛的深淵裏人和人之間,物和物之間,一切原是被距離所操控。
《素食者》裏的英惠,也跟她同樣清醒,只是,長久綑縛着她的並不是愛,或,更準確地說,那只是許多以愛為名但卻是粗暴地管制的繩子。
並不是愛,而是每夜出現的夢魘,使她再也無法吃肉,也不得不順從了自己的心意而不是他人的目光,再也不穿束縛着她身體的胸罩,不管是捱了父親的拳頭,被丈夫離棄,甚至被送進精神病院,也不改變地迎向夢魘對她的呼喚。夢不是魔,也不是愛,只是一種本能,讓她掙脫了一直把她圍困,使她自以為樂在其中的繩。丈夫所看到的英惠是外表平凡,毫不起眼的婦人,那是被繩子固定在一個形狀之中的她,攝影師的姐夫所看到的她,卻是美麗而帶有神秘魅力的女子。其實,無論丈夫或姐夫,所看到的都不是真正英惠,只是自己渴望的投射──順從社會制約的恰到好處的人,或,迎向本能的可慾的對象。順應本性是一種對自己的愛嗎?但,本性那麼龐雜,包羅了愛、憎、貪、嗔、癡,像一個可以包納一切隨時收縮的黑洞。
或許,那黑洞就是卡爾維諾所引用的關於查理曼大王的古老傳說,指環的中空部分,那些難言的執迷,人們習慣將之形容為「愛」。指環在日耳曼姑娘的舌頭下時,大王對她瘋狂,她死了,他仍着迷於她的屍首,大主教把屍首舌底的指環取出,大王便對大主教着魔,指環被扔進湖裏,大王再也離不開那個湖了。
這是一個關於癡戀的故事嗎?這是一個關於所謂的愛並非閃閃發亮的指環,而只是中間圓形的空虛部分的傳說。
(隔周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