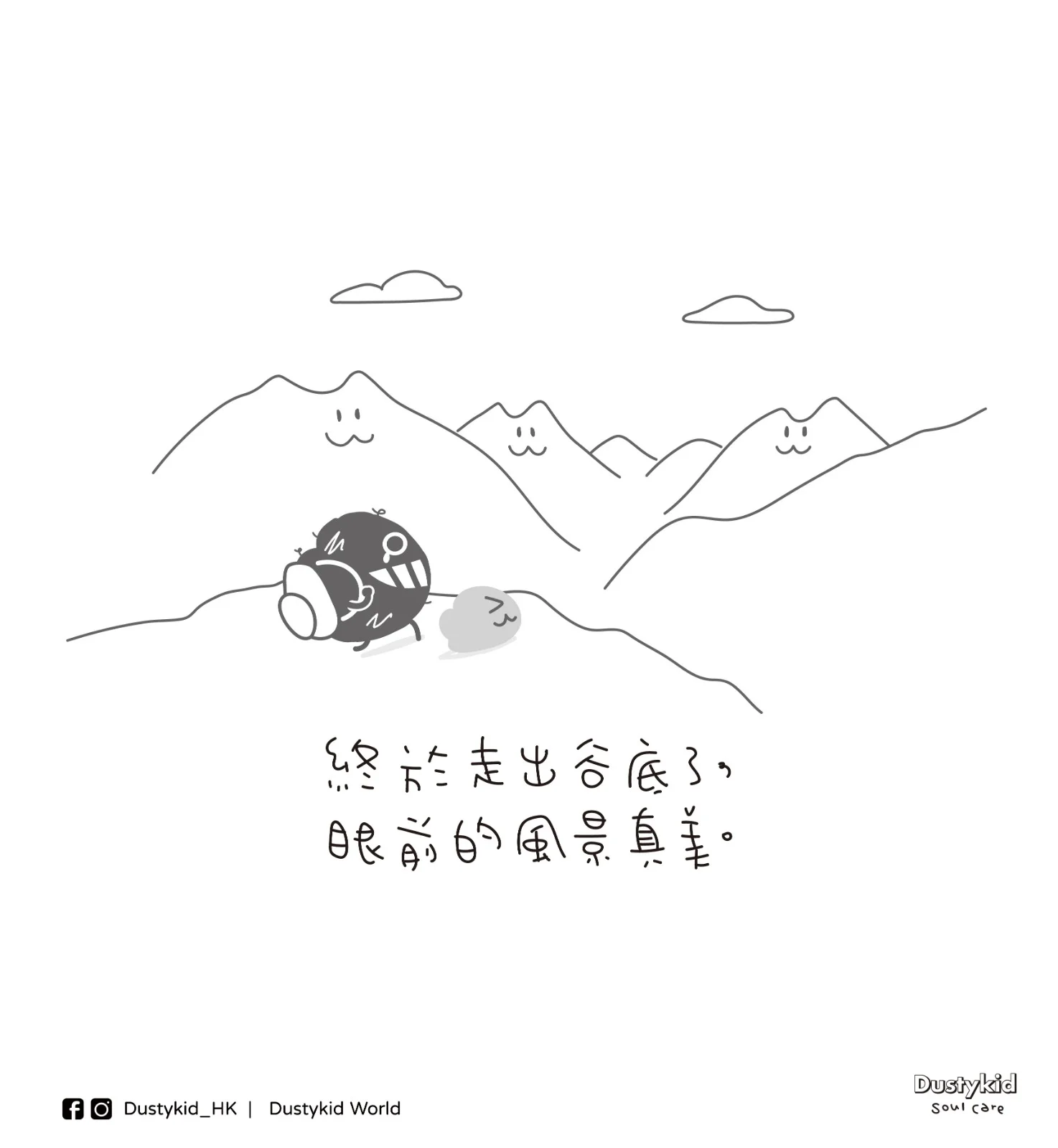林大海還沒有成為教主之前,是遺忘訓練所的導師;擔任導師之前,是防止自殺熱線的義工;當上義工之前,他在偏闢的Y地流浪,在那裏短暫出家;到Y地流放自己之前,他是教授,而且已在大學裏得到終身教職,同時是重度偷竊上癮者(這是心理諮商師X給他的稱號,而他對這稱號感到尚算滿意,畢竟,對於像他這樣的病者來說,得到一個正式的病理名稱,就像得到一個職位那樣重要)。在正式當上教授之前,他不記得自己是誰。
他只記得一縷光,在一個只有他獨自一人的木箱裏。四周一片漆黑,他不斷懷疑那絲僅餘的光其實只是他在絕望中的幻覺。對着訓練課裏的學員演講時,他會說那是一個反覆出現,持續多年的夢——以一個夢來包裝,比較戲劇化,也比較能抓住聽眾的神經。(多年來,他一直感到自己具備演藝才華。如果當年大學沒有聘請他,他或許會當上一個職業演員)有時候,他會稍為修改一下說法,說是上天給他的的異象,當他頭上的天線接收上天的訊息愈來愈清晰時,異象為他引路的功能就愈發準確。
他始終無法忘記多年前考完最後一科公開試,到試場附近的大型商場蹓逛,就在一家高級連鎖時裝店,看到一件最新到貨的春裝外套。要買下那件淡藍休閒麻質外套,他口袋裏也有足夠的現金。只是,他所渴望的比一件時尚好看的衣服更多,例如,克服一個考驗,而那考驗必須比考試更具挑戰性。多年來,他熟悉規則,甚至可以超越規則,但是,他也想要知道自己是否可以駕馭規則。
在時裝店內,他以具教養的有禮表情和口脗,請售貨員讓他試穿。在鏡子前撥弄頭髮,欣賞自己的五官和身材,對於售貨員的奉誠和遊說點頭示意卻不回話,趁店內的顧客逐漸多起來,售貨員被另一人叫喚過去之後,他捲了捲外套的衣袖,揹上背包,從容地步出店子。沒有人攔截他,外套裏似乎沒有掛着任何防盗的器物。從此,外套就是他的了。他漸漸累積更多這樣的經驗。
直至當上了遺忘訓練課導師,他向台下的學員講述曾經偷竊的經驗時,甚至大方地分享成功心得:「要打從心裏相信,那外套根本屬於你自己。其他人就會被你的心態感染。」然後,他提高聲線,說出其中一句課堂金句的上半句:「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假裝那人,直至你成為那人。 」接着把麥克風遞向台下,眾學員自動反應般喊出:「不怕暫時做A貨,終於我會是真貨。」
林大海懂得他們,在心裏深處,並不在尋求聖賢的指引,而是在追逐一個跟自己一樣,千瘡百孔,甩皮甩骨,卻也可以在台上閃閃發亮的人。
當然更獨特深刻的經驗往往無法言詮,甚至不方便跟任何人共享,那只能密封在心的瓶子裏,讓內裏珍藏之物一直滋養自己。比如說,他如何偷了好友的女朋友、同學的男朋友、上司的妻子、同事的工作成果;對情人謊稱自己生病需要藥費讓她心甘情願地給自己一筆鉅款。可是即使如此,那滿足和快樂都僅僅維持了一段很短的時間,而且感覺愈來愈稀薄,木箱裏的光線益發黯淡。不久後,他偷了別人的學術研究觀點,修改一點點寫在自己的論文裏。對於這類事情,他早已熟能生巧,可是那段期間,他迷上了一個只睡過一夜的女人,那女人對他厭煩,無論如何也不願再見一面的表情,燎起了他心底更多慾望的火。心不在焉的情況下,即使被告發論文抄襲,最初他並不當作是一回事,胸有成竹振振有詞地應對,面對着內部紀律聆訊,堅稱是他原創的意念。可是紀律聆訊團隊最後給予他的回覆是,建議他自行離職。
黑暗中,那撮光仍在。這次他看得非常清楚。木箱為他區分了內部和外在世界。如何不被外在世界的經驗影響,而始終穩住在如盲的漆黑裏,那一點渺茫的光?他在Y地荒原山上跟隨上師修行時,這樣問。上師只是似有若無地笑着問他:「你真的肯定自己置身在黯黑之中?那絕對不是幻象?」
****
「他是俄羅斯娃娃裏最核心的中空部分的空氣。」萬花回答說:「揭開了一個,又揭開了另一個,一個比另一個更小,最後的中央是空晃晃的,甚麼也沒有。」
自從馬其馬在回家的路上多次遇上她,又被她誤認為跟蹤狂之後,再次看到她時,他都走上前,一同走一段短短的路。不止一次,那段路因為對話、雲、樹的形狀或忽然在眼前的松鼠、貓或狗而不斷延展。有時,他們乾脆到附近的餐廳去吃一頓晚餐,或喝一杯。例如這天,他問她,教主是個怎樣的人,萬花便吐出了一幅又一幅像布幔那樣的情景、人臉和事情:遺忘訓練所的金句、林大海給她的留言、那些教練的眨抑、高舉雙手的學員。
「他在你心裏佔了很大的部分。」半晌,他忍不住說。
萬花停下腳步,睜大眼睛盯着他說:「怎麼會!這樣的人。難道你聽不到我的語氣裏盡是輕蔑和討厭?」
馬其馬細看萬花的臉像是在找尋甚麼,終於把想說的話吞下來,替換了他照顧過的一隻受傷的貓的事情。
「那隻貓年紀很小,被遺棄在雨天的路旁,我把牠撿回家後幫牠洗澡,給牠吃罐頭,牠也溫馴地吃飯,只是吃過飯後就不斷抓自己,把自己當作一個打架的對象那樣啃咬和抓傷,直至頭破血流仍不罷休。傷口好不容易結了疤,牠再次抓出更大的傷口。我給牠塗了藥,好了一點,牠又再次傷害自己。」
她看着他,等着在聽貓的下場。
「貓好像一直在揭開自己的臉面那樣,但最後我看到的都是自己,內疚、不安、不忍心給牠戴上頭罩妨礙牠的自由,卻也沒有勇氣去承受牠整張臉爛掉的結果。貓真正揭穿了的,其實是我。」
馬其馬揣摩着留在肚腹的那句話:「被我們所憎惡和怨恨的人,總是比那些被我們所愛的人,佔據了我們更多心神和時間。」始終沒有讓萬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