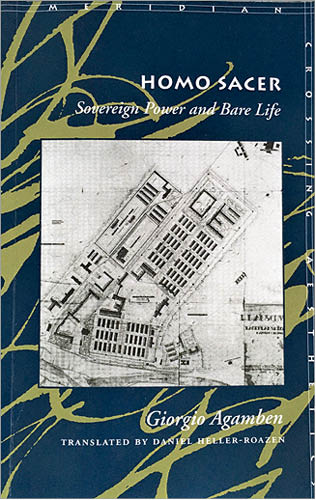
歷時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和新近爆發的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令人深切體會到生命與政治的密切關係。用「密切」來形容,其實完全說不到重點,觸不到痛處。生命與政治的奇異(甚至是詭異)關係,就好像痛感一樣,幾乎是一種無法形諸語言,而停留在動物性的吼叫或呻吟的肉體層面的事情。示威者被警察打至頭破血流、肢體骨折,被催淚氣體、胡椒噴劑或水炮藍水射中導致呼吸困難、皮膚紅腫,被子彈射盲眼睛或者貫穿內臟;武漢感染者奔波於醫院之間,物資短缺,一牀難求,身體發熱、呼吸困難,氣絕身亡,然後變成「屍體」,被裝進「屍袋」,像死物一般大量運送到火化場,親友連最後一面也不能見上。
生命變成非生命的過程,可以是陡然的瞬間。這不是說死亡本身,而是說權利和尊嚴被剝奪,所剩下的「爛命一條」。重點不是主動自招還是不幸中招的分別,而是原本由體制好好保護和管理的個人,因為政治上的專橫和制度上的失衡,而變成了被打擊、排斥或離棄的身體。政治和身體/生命不但關係密切,前者更加是通過對後者的支配而確立的。粗淺地說,現代社會和古代社會的分別,是身體/生命愈來愈以公民的身份,主動地介入政治領域,試圖從支配者手上奪回主權。弔詭的是,由公民組成的民主政體,並非就此終止其支配性,只是因為受到制衡,而比極權政體不那麼明目張膽而已。在政體面前,個人生命依然十分脆弱。
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國思想家傅柯提出「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概念,研究現代歐洲政體如何把人的生命本身納入政治管理和操控的範疇,當中牽涉到醫療衞生機構和專業的建立、精神疾病的斷定和治療、懲罰和監禁的方法和制度等。現代政體把本來屬於私人和個人生命層面的種種,都視為管治技術的對象,生命於是便完全被政治化。繼傅柯之後,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進一步認為,政治介入生命並不始於近代,而是在主權和法制的初創期,也即是古希臘和羅馬時期,已經形成。
人一旦進入法制社會(無論是多麼簡樸的古代共同體),便失去了自然生命的本質,成為了人為法制內的生命。(古希臘人把它稱為bios politikos。)法制一方面保障了個人的人身安全,令他免於自然狀態下的弱肉強食,但個人也必須把行為的自主權渡讓給法制。在這個根本性的渡讓之下,如何為個人爭取最大程度的權利,是現代民主運動的目標。但是,在推翻舊的專制統治和建立新的民主體制之間,卻出現一個難以跨越的空隙──以非法手段(革命)去推翻舊法之後,可以憑什麼基礎或法源去創造新法?這是個法哲學上的重大問題,不是純粹靠武力奪權可以解決的。面對這個難題,連主張共和制的康德也踟躕了,否定了革命的合法性。
法制的權力泉源問題還不只這個。阿甘本指出法權有兩種,一種是創法權(constitutive power),一種是創成法權(constituted power)。前者在法制創立之後理應消失,剩下來的任務便是維護法制。但是,所謂的「主權者」(the sovereign)(無論是君主、民選統治者,還是議會)其實還擁有創法權。小者如法律的修訂或增刪,中者如修改憲法本身,大者則是法制的(暫時)中止,也即是實施緊急狀態或例外狀態的權力。(特區政府援引的緊急法就是這樣的一回事。)主權者既在法內也在法外的特質,形成了現代法制隱藏的問題。
這跟生命操控有什麼關係?阿甘本把歐洲法政體制的源起,聚焦於稱為homo sacer的古老形象上。Homo sacer可以直譯為「神聖之人」。在古羅馬法中,它指稱被判定「可以被任何人殺死而不需負上刑責」,但又「不能被用於祭神」的罪犯。「神聖」但卻同時是「卑污」、「不潔」;既可以任意殺死但又不能奉獻給神靈;這意味着「神聖之人」同時被排除在人間律法和神聖領域之外。阿甘本借用班雅明的說法,把「神聖之人」稱為「裸命」(bare life)。他甚至大膽地把既在法內也在法外的「主權者」,和既不屬於人間也不屬於聖域(亦不屬於自然)的「神聖之人」,視為原始法體制的對稱結構。對於「主權者」來說,所有人也是潛在的「裸命」。而這個根本性的、潛藏的結構,也是現代法制和主權國家的基礎。
生命,從一開始就是政治的根基。主權者的本質,就是操控生殺大權。我們似乎還未能發現(或發明)一種體制,可以超越和克服這個弔詭,以及當中潛在的危機。當然,我們已經沒有「神聖之人」那樣的法律了,但這並不表示「裸命」的可能性已經杜絕。相反,它隨時會以其他形態冒出。在「正常」的情況下,我們以為現代體制已經解決了上述的問題,但當遇上「異常」或「極端」的處境,法制的內在矛盾和主權者的超越性權力便會顯露無遺。而此中的徵兆,就是「裸命」的出現。(根據阿甘本的觀點,這是由潛在的裸命顯化為實際的裸命。)
當有人因為政治抗爭而被警察以維護法紀之名施以過度的暴力,有冤無路訴,甚至出現懷疑「被自殺」的事件;當有病患因為政治制度的失衡而得不到適切的治療,陷於自生自滅的絕境,並且被系統化地毀屍滅迹;當連屬於體制內的醫護人員,也被迫處於防護不足的狀態,生命被用作賭注;我們可以肯定,「裸命」已經顯現為事實。許多人已經在體制之中,同時被排除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