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次談到凱薩琳.海爾斯(Katherine Hayles)的論著《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當中追蹤了cybernetics這個學科在二十世紀下半的發展,並配合對同時期科幻小說的分析,探討「後人類」這個概念為什麼會對人們帶來焦慮和恐懼,它又如何可以成為令人類脫胎換骨,重親自我創造的契機。
Cybernetics中譯為「控制論」、「自動控制論」或「模控學」,聽起來始終有點不明不白。其實cybernetics本身是個混雜的學科,橫跨許多個範疇,包括數學、統計學、機械學、生物學、神經科學、心理學、計算機學,甚至是人類學和社會學。控制論的創始人諾伯特.維納(Nobert Wiener)把它定義為「生物體或機器中溝通和控制的科學研究」。維納是數學家出身,二戰時曾替美國軍方研製反戰機自動攻擊系統,但戰後卻成為和平主義者,拒絕參與任何軍方計劃。控制論主要是在維納的鼓吹和推動下形成的學科,當中對「生命體」的理解涵義極廣,除了有機生物,還包括機器和社會等不同層階的自動系統。
上次我說控制論和人工智能的分別,在於前者重視實體而後者只關心數據和運算,其實並不十分準確。事實上,在稱為控制論第一波發展(1945–1960)的時期,研究者利用數學模型和機率函數計算自動系統應對環境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到了第二波發展(1960–1980),研究焦點才轉移到個體與環境的物質互動,認為實體(身體)和信息(意識)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控制論究竟傾向實體化還是去實體化(embodiment and disembodiment),端看研究者的對生命本質的不同觀點。比如認為可以把人的意識和記憶化為數據,下載到電腦中的機器人學家漢斯.莫拉維克(Hans Moravec),便相信生命的本質就是沒有形體的信息。
控制論和人工智能的最大分別,可能是對客觀現實的看法。人工智能研究者假設客觀現實是存在的,而技術研發的目的,就是要創造出雖然功能更強大,但模式上是以人類為參照的程式和機器,無論是下棋、駕駛、聊天、投資,還是在戰場上殺敵。另外,把意識化為數據,把人從肉體的束縛解放出來,也必須先假定有一個客觀的、統一的、獨立存在的意識,也即是有一個界限清晰的自我。相反,控制論對現實的看法是建構性的。現實世界對任何一種生命體來說,就是它的系統設計所容許它認知的現象。對青蛙、小狗或海豚來說,牠們的「現實」和人類所認知的極可能是差異大於共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人類所認知的才是最真實、最客觀的版本。它只是其中一個版本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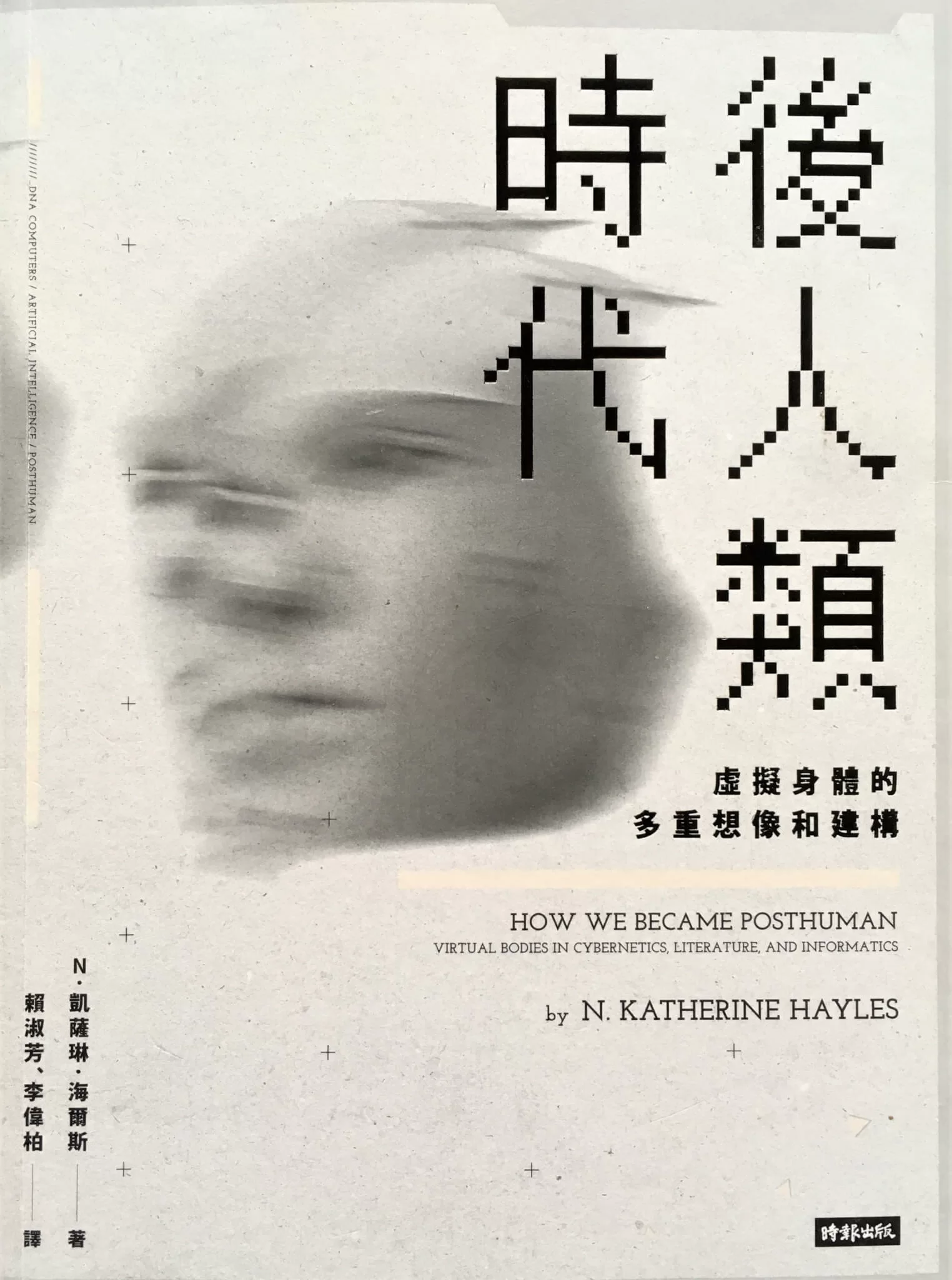
客觀現實不存在的另一面,是意識的非一致性。生命體對外界的反應以分層和分工的方式運作,絕大部分的情況都是自動的,無需經過思考和定奪。所以自我意識在生物演化中是個偶發或後起現象(epiphenomenon)。這和十八世紀在西方興起的人本主義(Humanism)和自由主義(Liberalism)所推崇的理性自主自我,是互相抵觸的。二十世紀末以來的文化批判理論,普遍認為自由人本主義與自由經濟理論同出一轍,並由此發展出現代時期的掠奪性資本主義,以及人類對地球資源的開發和控制的無限擴張。對《後人類時代》的作者海爾斯來說,控制論提出的分散式認知系統,是對自我本位的人本主義的批判。這就是她所理解的「後人類(本)主義」(Posthumanism)的積極意義所在。
從腦神經科學的最新發現可見,「自我」的確是個建構出來的幻象。在日裔美國科學家加來道雄(Michio Kaku)的科普著作The Future of the Mind中(中譯作莫名其妙的《2050科幻大成真》),舉出了許多證實「自我」並不存在的案例。比如說,為了防止一些癲癇症患者嚴重發作,會對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的連結進行切斷手術。手術後患者表面上沒有什麼行為異常,但研究者發現,如果分別給他們的左眼和右眼展示相同的問題,得到的卻是不同的答案。(左眼由右腦主管,而右眼由左腦主管。)這說明了左腦和右腦其實分別運作,各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取向。在一般的情況下,由於左腦是主管語言的區域,所以右腦的取向會被左腦的表述能力所凌駕。
科學家指出,腦神經元連結的運作是多線同步並進的,許多單元既互相補足,也互相競爭,產生出認知和述說世界的模型,而最後我們之所以感到有一個單一的、穩定的自我,是因為內側前額葉皮質這個區域,發揮了統領的工作,把所有混沌和矛盾的信息,建構成一個合理的、一致的故事,製造出我們知道自己是誰的幻象。問題是,這個所謂統領,實際上的決策能力是有限的,它的工作只是對無意識的自動行為加以自圓其說而已。人類所自傲的理性和自由意志,不但不是我們的意識的主要內容,甚至只是扮演着邊緣的角色。
控制論的其中一名重要人物,研究自生系統和人工生命的法蘭西斯科.凡瑞拉(Francisco Varela),是一位佛教信徒。佛教所說的「無我」,正正就是生命系統中的諸種運作羣龍無首的現象。可是,正如在《周易》乾卦中的「羣龍無首」是吉兆,從生命的角度,沒有一個既定的、固有的自我,也不一定是壞事。控制論可以導引出不同於人本主義的價值觀,更新對生命及其自主性的理解。凡瑞拉如此定義說:「生物自主性的解釋,就是考量行動和創造世界意義的方式。」所以海爾斯樂觀地相信,後人類解構了唯我獨尊的自我,創造出新的更開放的後自我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