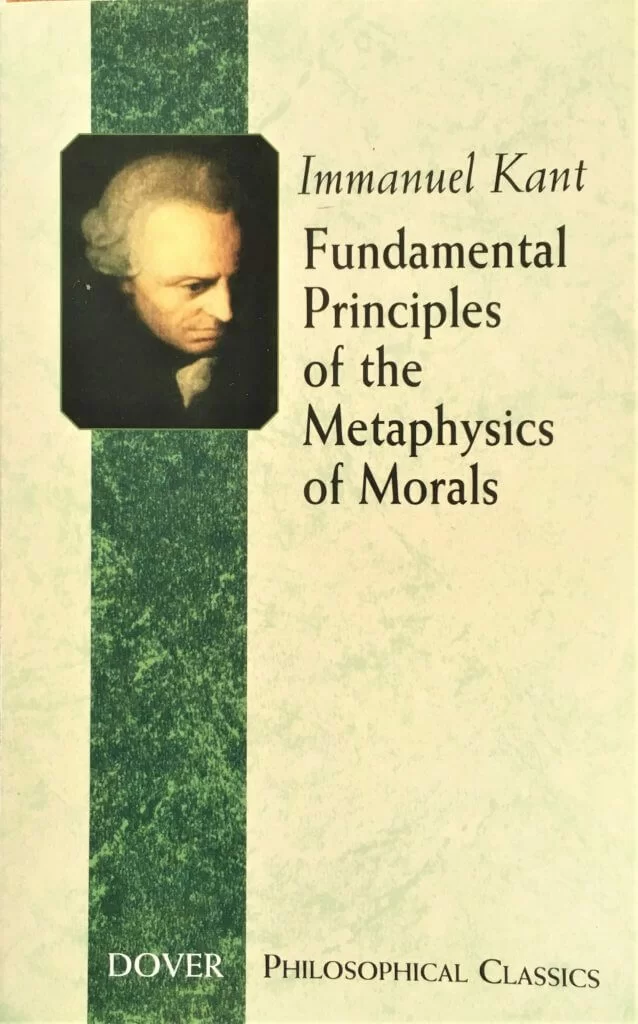長久以來,人們只把康德視為哲學家看待,忽視了他在政治理論上的貢獻。直至二十世紀下半,學者才開始確認康德在歐洲現代政治學方面的奠基位置。上次談到的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更加以康德(和馬克思)為出發點,建構自身的政治學理論,重新發現康德的當代意義。
康德並沒有任何一本著作是直接以政治為主題的,但是,從他的諸多文章中,可以清晰看到他有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理論建基於他的倫理學,一切政治行為其實也是道德行為。正如柄谷曾指出,這對馬克思有深遠的影響。追求政治上的平等、公義,不可能不同時是一種道德理想和責任。康德把他的道德論稱為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和純粹理性(pure reason)區分開來。實踐理性探討的是道德的形式,而不是道德的內容。所以康德不是宣揚美德的道學家。他想確立的是道德之所以能成立的原則,而不是道德規條。
康德提出的道德原則(或形式)其實很簡單,就是他稱為「定然律令」(舊譯「絕對律令」)的檢視方法。他在《道德的形上學的基礎原理》中,反覆以不同句式演繹「定然律令」,歸結起來即為:「只有當你願意把自己的準則,同時視為普遍的準則,才能按之而行動。」或「只有把自己的行為準則,自願地當作自然的普遍法律,才能按之而行動。」我們不妨把它理解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反面說法,即「己所欲者,亦欲人同所欲而行之」。這樣說的話,如果我容許自己欺騙別人,也即是接受別人也同樣可以合法地欺騙我。這個想法的內在矛盾,令它不能成為有效的定然律令。康德認為,道德的探究就是一檢視各種個人和主觀的行為準則(maxim),以斷定它們能否成為普遍的法則(law)。由於每個人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在生活中自我檢視,慢慢建立自己的道德性格,並以此指導自己的行為,所以它是實踐性的。
重要的是從個人和主觀的準則,過渡到法則或法律的過程。康德把這理解為一個「立法」(legislation)的過程。道德、法律和政治的基石,是個人的自由,但自由的實踐卻不等於任己所欲而為之。如何行使一己的自由,但又同時尊重他人的自由,已經成為了老生常談。康德的不同一般之處是,他所指的法律不是由外部強加的他律,而是自我通過理性和意志而施加的自律。最高度的自由的實踐,就是遵守自己給自己訂下的法律。用柄谷行人的話說,定然律令的意思不外乎是:「做一個自由的主體。」
從道德到政治的層面,康德主張的政體是共和制(republic),當中的立法權由民選的代表所行使,意味着人民是自身的立法者,但也必然是自身所立之法的遵守者。因為法律是人民自己(通過選舉代表)所制訂的,所以是人民自由意志的體現。這和道德法則上的「定然律令」的運作是一樣的。限制自由的法,是由自由的人,通過自己的意志所制定的,所以法體制的主權者(the sovereign)是人民。這一點跟被動地服從外在的律令(君王、極權者、宗教規條等)完全不同。
康德提出的另一條定然律令,也是他的政治理想國的基礎:「你的行為,永遠不可以把人性──你的人格以及其他所有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僅僅當作手段(means)來運用,而始終必須同時視其為目的(end)。」自己「做一個自由的主體」,也把他人視為「自由的主體」,這就是「目的的國度」(the kingdom of ends)是最高法則。把別人視為手段並沒有問題,相反,在人際關係上我們無法不視別人為手段,以及被別人視為手段。舉例說,我們坐巴士,便要把巴士司機視為我們到達目的地的手段;學生上課,便要把老師視為學習目的的手段;我們外出吃飯,餐廳廚師和服務員便是我們達至用餐的目的的手段。這種手段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正常的。但是,我們不應僅僅把別人視為手段,而同時必須把他們視為目的,也即是具有獨立性格、權利和自主性的人。後者不只是道德領域的事情,也是政治領域的事情。
觀諸香港近日發生的修例事件,我們會發現,政府漠視人民的立法意志(在此事上呈現為反對「被立法」),法律變成了強加於人民的他律。人民並沒有被視為主權者和目的,他們的自由也沒有受到尊重,反而面臨被剝奪的危機。至於商界在剔除影響自身利益的條文後表態支持修例,完全違反定然律令的要求。己所不欲,施之於人;自己甩身,你死你賤。於康德而言,這肯定是敗德之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