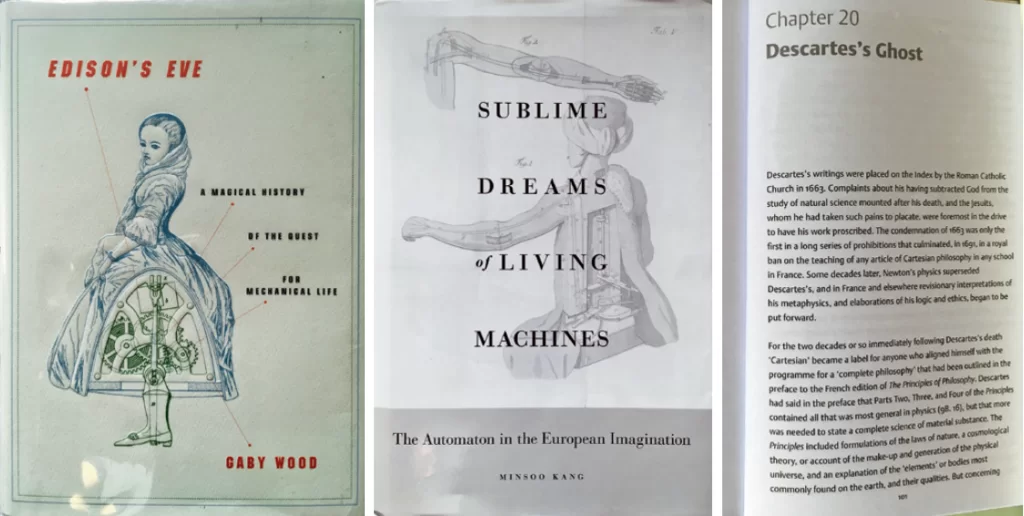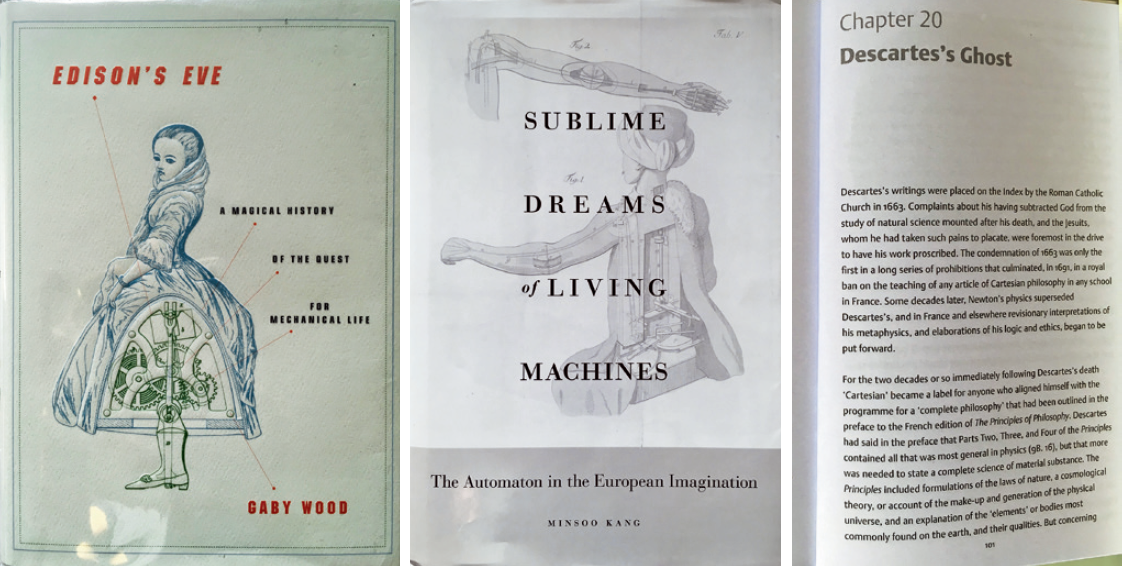
最近一直在讀笛卡兒的哲學著作和傳記。其中一本簡介書的最後一章,題目是”Descartes’s Ghost”,談到笛卡兒提出的哲學和科學觀點縱使已經過時,為何到了今天我們還是難以”lay his ghost”。”To lay the ghost of “這個說法,意思是擺脫或放下令人感到驚恐、不安或困擾的過去的事情。用中文的說法,大概就是「解除心魔」。但是,據說近年笛卡兒在學術界,特別是在機械人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地位,大有「鹹魚翻生」、「隔世回魂」的趨勢。
從啟蒙時期到十九世紀,笛卡兒曾經長時間被奉為現代科學精神的創始人物之一。尊崇「理性的自然之光」為尋求真理的唯一途徑,追求知識的明確和精準,以數學原理為理解自然的最可靠方法,從大至宇宙到小至人體的結構和運作的機械觀,如此種種都是現代科學精神的核心。就算笛卡兒自身的哲學諸多漏洞,他的物理學推論大都站不住腳,但他在西方社會邁進現代時期的關鍵位置是不容置疑的。
可是,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無論是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現象學或者存在哲學,都全盤否定笛卡兒的絕對自我肯定的主體性,以及由此而推論出來的身體和心智(靈魂)截然分割的二元論(dualism)。我八十年代在大學念比較文學的時候,是通過福柯和達利德這些後結構主義者的理論認識笛卡兒的。當時得到的印象是,笛卡兒思想幾乎等同於萬惡之源,是現代性的所有罪行的代名詞。說某某是 “Cartesian”簡直就是最惡毒的學術詛咒。
不過,風水輪流轉,據美國韓裔思想史學者Kang Minsoo的觀察,學界對笛卡兒的興趣近年有回升的迹象,這跟他作為人體機械論的先驅有關。在進入熱烈討論生化人、人工智能和後人類時代的今天,一個在四百年前便提出人體其實只不過是一部精密的機器的哲學家,自然再次成為焦點。(至於他主張的靈魂的非物質性,及其乃人類理性之源,並且由神所創造的觀點,就不必過於認真對待了。)我早前也談過Kang Minsoo關於自動人偶發展史的著作Sublime Dreams of Living Machines,以及「笛卡兒的女兒」的傳說。最近發現Kang去年發表了一篇關於這個傳說的演變過程的論文,又增添了我對這個題材的理解。
Kang的這篇文章題目是”The Mechanical Daughter of Rene Descartes: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an Intellectual Fable”,發表於劍橋大學的《現代思想史》學報。這個「寓言」(fable)簡單來說是這樣的:話說笛卡兒在五歲的私生女兒Francine死後,製造了一個跟她一模一樣的自動人偶,時時帶在身邊。在一次海航中,船隻遇到大風浪,船長發現了笛卡兒行李中的人偶,視之為邪惡的象徵和危難的禍端,把它投進海裏去,風浪也因此平息了。Kang認為這個傳說之所以在近十多年流行起來,成為學界(包括哲學、歷史學、政治學、心理學、教育學、機械人學、文學和電影學)討論和引述的寵兒,也在創作裏頻繁地被改編和應用,其中一個主要來源是英國作者Gaby Wood的普及歷史著作Living Dolls(2002)(美國版題為Edison’s Eve)。我在本欄寫過一篇〈笛卡兒的女兒〉,文首便引述了此書的開頭,關於這個傳說的繪影繪聲的描寫。據Kang所說,自此這個故事便被不同界別的研究者廣泛引用,並且擅自改動,加鹽加醋,以服務自己的論點。
事實上,Wood的描述本身便是想像和虛構。Kang以嚴謹的歷史研究態度,追本溯源,從這個傳說第一次出現,一直跟蹤它在二百多年間多次發生的變體。在一六九一年,Adrien Baillet寫作了第一部笛卡兒傳記,裏面記述了哲學家於一六三五年於阿姆斯特丹和女傭人誕下了女兒Francine,此女五年後因猩紅熱死亡。一六九九年,一位名叫Bonaventure d’Argonne的修士,以化名Vigneul-Marville寫了一部叫做Mélange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歷史與文學逸事》)的書。這位修士是個道德上的保守派,但又是笛卡兒哲學的支持者,所以,他試圖抹除哲學家曾有一個私生女的污點:作者說他從一個笛卡兒崇拜者口中聽到,所謂私生女的傳言,其實是假的。實情是,哲學家為了證明他的人體機械論,親手製作了一個和真人十分相似的自動人偶,作為示範之用。不幸的是在一次海航中,人偶被船長發現,並誤以為是巫術或不祥之物,而遭拋擲到大海裏。Kang指出,這個傳說的始作俑者的目的,是為了給笛卡兒曾經與女傭有染一事開脫,以保哲學家的清譽,而非像後人所說那樣,以人偶的製作說明笛卡兒對女兒的不捨,甚或是笛卡兒對人偶產生了變態的戀物癖或戀尸癖。
這個故事在往後兩個世紀裏,經過多次的轉述和再創作而變形,當中包括英國作家艾薩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和法國小說家安納托爾.弗朗士(Anatole France)的生動版本。故事蘊含的元素越來越豐富,細節也變得越來越確鑿,例如笛卡兒以女兒的名字Francine命名人偶,人偶的模樣和死去的女兒一樣,笛卡兒甚至把人偶當成親密的對象。至於人偶被發現的航程,最後被Wood戲劇性地定在一六四九年,笛卡兒從阿姆斯特丹坐船出發到斯德哥爾摩,也即是他的人生的終極之旅。到達瑞典幾個月後,哲學家便客死異鄉。
身為歷史學家,Kang感到驚訝的不是一個傳說的演變,而是當代不同專業範疇的學者們,竟然毫無例外地吝於花費任何功夫,去查證傳說的源頭,釐清故事的歷史脈絡,而只是順手拈來,甚至加入虛構的行列。如果是創作行為,當然沒話可說,但如果是學術研究,則未免過於輕率和懶惰了。不過,有像Kang這樣態度嚴謹的學者,笛卡兒的鬼魂應該可以安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