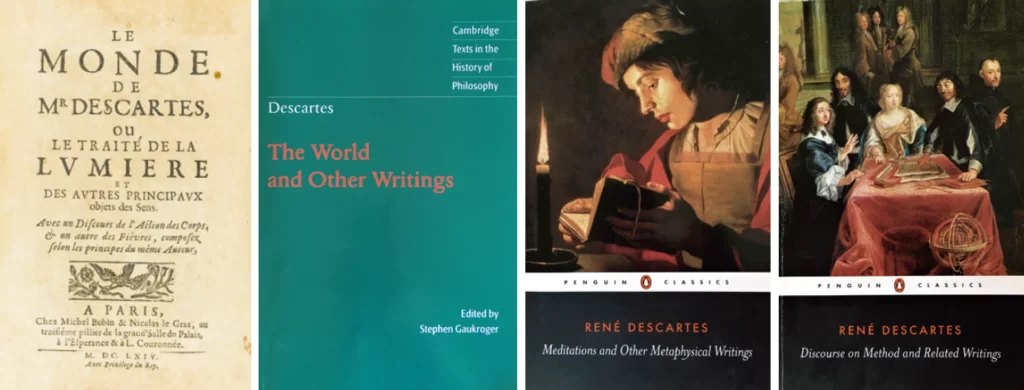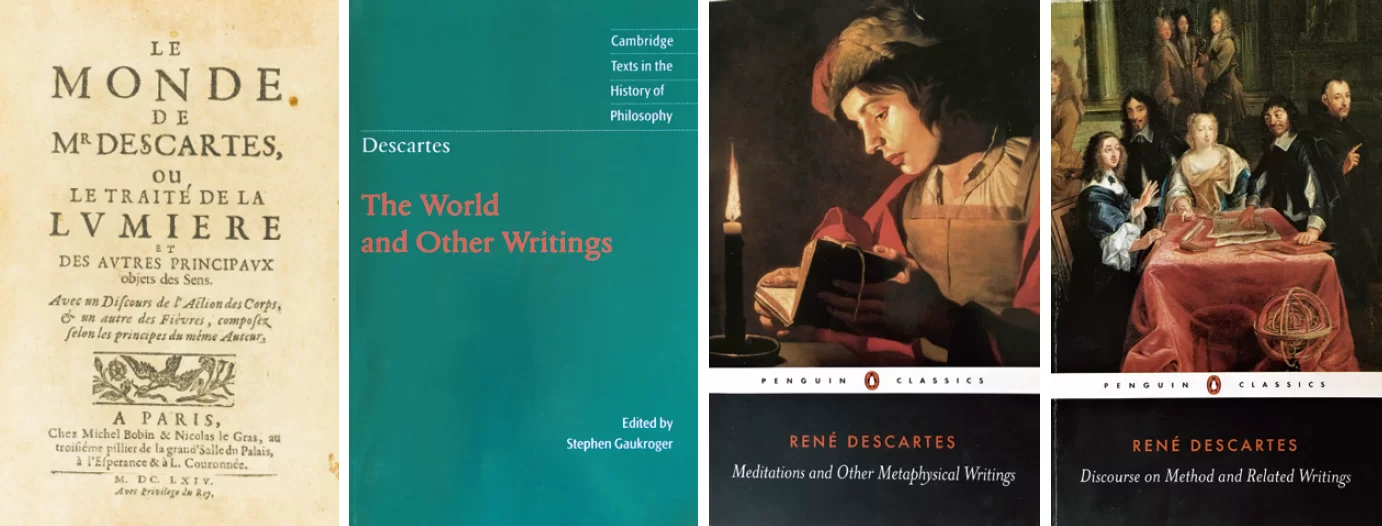
說起笛卡兒,人人都知道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此語第一次出現在他以法文寫成的《談談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原文為”je pense, donc je suis”。後來在《哲學原理》(Prinicipia Philosphiæ)(1644)中再以拉丁文表述為”ego cogito, ergo sum”,簡稱為”cogito, ergo sum”,英文譯作”I think, therefore I am”。這個句式往後成為了哲學史上最常被惡搞的對象。「我X,故我在」的玩笑層出不窮,大家不妨自行創作。
至於真的讀過笛卡兒的人,可能不多。甚至把他批判得體無完膚的人,也很可能沒有細心讀過他的著作,最多是翻翻《談談方法》和《第一哲學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大家感興趣,又或者是集中攻擊的,是他的形而上學。但是,笛卡兒從一開始,研究重點其實在自然哲學或物理學(即後來廣義的科學),而他到了命終之時,最重視的也是自己在這方面的成果。
笛卡兒在一五九六年生於法國中產家庭,家族多從事法律職務,可以說是國王的法務執行官。此類職位可以用錢購買,之後收入終身無憂,屬於「第三等級」中之高層。(法國舊王朝社會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為貴族,第二等級為神職人員,餘為第三等級。)笛卡兒大學畢業後,也曾多次考慮走這條路。在猶豫不決之際,他決定離開法國,見識這個世界。他加入過軍隊,當過紳士士兵,但似乎未曾參與實戰,只是乘機四處遊歷,有點像今天的工作假期。期間結交了一些學者,開始研究數學,以至光學等。
他一六二九年移居聯合省份(即以荷蘭為首的七省聯合共和國),一住便是二十年。他的所有哲學和科學成果,也是在這二十年間產生。他有一個奇怪的習慣,就是不停更換居住地。在荷蘭便住過七、八個城鎮,地址也很不確定。他的理由是逃避社交的打擾,專心從事研究工作。但他同時維持着一個有效的通訊網絡,讓他跟當代學界保持聯繫,獲知最新動向。他的一個主要通信人,是巴黎的梅森神父(Marin Mersenne)。此人亦是博學家,交遊廣闊,有「歐洲郵箱」的稱號。笛卡兒給人一個避世的隱居者的形象,連對梅森也不告知對方自己的地址,信件往往要經過多番的轉遞。
從一六二九年至一六三三年,笛卡兒潛心寫作一部自然哲學巨著,名叫《世界》(Le Monde)。《世界》的第一部分為〈論光〉,是通過對光的性質的探討,去推出他的物理學,即物質的構成、物理運作的規律,以至整個宇宙的生成過程。那是極具野心的一部著作,提出的是嶄新的宇宙機械論。此書第二部為〈論人〉,以第一部分的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人體機械論,以及靈魂和身體的二元論。後者所說的是,人的生理部分是機械性的,跟動物或自動人偶(automaton)沒有分別,但人具有理性,而此理性即人的靈魂。所以,「人」的定義是機械肉體和理性靈魂的結合。笛卡兒認為,兩者的接合點在腦部的松果體。
一六三三年中從羅馬傳來了壞消息。伽利略的《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即教會認可的托勒密地心說和哥白尼的日心說)被宗教裁判所查禁,伽利略被控以「違反教義和道德」及「高度懷疑為異端」被囚禁。笛卡兒立即終止了《世界》的寫作,甚至一度考慮把手稿燒毀,後來決定把它藏起來。往後無論朋友如何勸誘他,他也拒絕把它公開。他不願意成為真理的殉道者。但是,他還是忍不住把當中的一些不觸及教義的部分,以分拆形式發表。他的第一部出版的著作《談談方法》,主角其實是當中的〈屈光學〉、〈流星〉和〈幾何學〉三篇科學論文,而行文鬆散的〈談談方法〉只是前言。但是,後世幾乎都把三篇論文刪除,把序言當作獨立著作出版。
笛卡兒明知自己的物理學是不容於教義的,所以他千方百計去說服教會,自己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搞起形而上學來。於是便出現了一個科學家不應該染指的神學辯解《第一哲學沉思集》。他試圖以理性證明靈魂的存在和不滅(「我思故我在」,所以靈魂可以獨立於身體感官),以及神的存在。很可惜他在一開始便採用了懷疑論的方法,然後才一一把懷疑破除。這令一些批評者認為,他反而給予懷疑論者太強的火力,削弱了讀者對信仰的信心。他的論敵甚至認為,他根本就是個偽裝的無神論者。
可以說,笛卡兒在世時既嘗試討好教會,但又希望以偷龍轉鳳的方法,以他的一套新式學說取代過時的經院哲學。這做法並沒有取得成功,反而惹來了一次又一次的爭議,令他為自辯而疲於奔命。而他最在意的科學研究,卻沒有完整發表的機會,已發表的也沒有得到很高的評價。到了他生命的後期,一直驕傲自信的他的確變得有點心灰意冷。可能是因為這樣,他在瑞典女皇克里斯蒂娜的多番邀請下,終於答允了那趟「致命」的旅程。
一六四九年九月,笛卡兒從阿姆斯特丹上船,前往斯德哥爾摩。能成為一個女皇的私人哲學導師,無異於找到一個強大的贊助者,是以後發表著作的堅固後盾。但是,在出發前笛卡兒已有不好的預兆。他把重要的書信和手稿託付友人,並交代了自己的後事。克里斯蒂娜把哲學課的時間定在清晨五點,這對於懼怕北國嚴冬的笛卡兒來說是極大的折磨。一六五零年二月十一日,笛卡兒在瑞典因肺炎病逝。
《世界》於笛卡兒死後由追隨者整理,於一六六四年出版。隨後便開始了崇尚理性的啟蒙時代。
(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