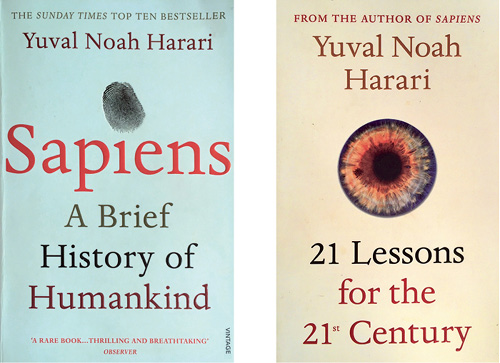
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的《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是兩年前出版的書,當時立即便買了,但卻一直擱着未讀。我一向對於「關於什麼的幾堂課」的書抱有懷疑,感覺好像商業味道濃於思想深度。最近由於疫情所造成的末日感,我覺得是時候打開這本書,看看這位「科技先知」有什麼好主意,可以讓我們這些死到臨頭的凡夫的心靈得到點滴撫慰。
歷史學家一向給人埋首於故紙堆的印象,研究的都是些對當下世界沒有影響,世人也不會感興趣的枯燥題材。哈拉瑞罕有地把歷史的作用重新提振起來,並且推到廣大的民眾的關注中,確實有過人的本事。他的首部著作《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把整個人類的歷史綜合在一本書裏,簡潔扼要但又面面俱全,觀點鮮明而又易懂,加上生動幽默的語言,具備了專門知識普及化的所有條件,立即成為全球性的暢銷書。
哈拉瑞之後再推出《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打破歷史學家只談過去的限制,把歷史分析功夫用在未來,對科技發展的趨勢及其危機作出預言和警告。有別於由科學家撰寫的充滿樂觀主義的同類著作,哈拉瑞更富有懷疑和批判精神,表現出歷史學家特有的憂患意識和人文關懷。這本書打通了過去與未來的既定劃分,從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廣度,審視它的歷史發展在未來可能遇到的挑戰。哈拉瑞以物種說史,採取的是科學的角度,因此延伸至未來科技的探討亦是順理成章。
有兩部大作在前,《給二十一世紀的二十一堂課》難免顯得單薄。書中部分篇章為已經發表的對特定議題的回應,經過改寫和補充,湊合成作者心目中對未來世紀具有重要性的題目。由哈拉瑞擅長的科技問題,到全球化的挫折和民族主義的復興,再而至於恐怖主義、戰爭、宗教衝突、難民與移民、後真相社會等。議題的覆蓋面可謂全面,但議論的深入程度則有參差。有的章節基本上是前作的盤點,但也有把觀點引伸至全新的領域。
總的來說,從《給二十一世紀的二十一堂課》可以看通哈拉瑞作為評論家的看家本領。說穿了就是懷疑主義精神,對種種既有的觀點和論述不予輕信,置於質疑,繼而大力拆解。歷史學家就是一個研究故事的人,哈拉瑞卻偏偏從源頭去揭破故事的神話(或稱迷思)。他不是揭破某些故事是神話,他是說,所有故事也是神話,也是虛構。人類的所有共同故事也沒有真實性,都是為了達至某種演化和生存目的而創作出來的。這些故事包括:宗教信仰、民族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金錢、法律、愛情、公義、真相,甚至是自我。
哈拉瑞最獨到的觀點是:人類是靠故事來自我塑造,靠神話來凝聚成強大的羣體,因而取得生存優勢和成功的物種。但偏偏故事也是造成人類世界種種欺壓、不公和盲目鬥爭的因素。一個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告訴人們他們相信的故事是如何構造出來的。他並沒有叫人完全不要相信任何故事,因為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但當我們選擇相信,我們要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麼。
閱讀哈拉瑞可能會令人沮喪,但他並非主張虛無主義。他依然堅持某些社會價值,並且相信人類不必依賴宗教或國家權威,也可以通過世俗社會的合作,共同建立和守護這些價值。在全書最為「正面」的一章《世俗主義》(Secularism)中,他列舉了這些價值—真相、同情、平等、自由、勇氣、責任。問題是,當他在其他章節毫不留情地掃除一切舊有的價值,讀者又怎樣可以重拾信心,相信任何價值的真實性?哈拉瑞無疑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任何時候也不會把事情說死。他總是在做正反兩面論述,一方面批評,一方面表示理解,在樂觀和悲觀之間保持平衡。他從不講理論,不試圖構造思想體系,所以他看起來不像一個思想家,而更像一個評論家。但在所有看似簡單易明的評論背後,他其實收藏着一個根本的核心思想。這個核心思想支撐着他犀利的見解,但也造成了難解的矛盾,或至少是未解的含糊。
在全書尾二章《意義》(Meaning)中,哈拉瑞打開了思辨界最巨大的黑洞—世間的所有事情,其實也是沒有意義的。在拆除一切意識形態堡壘之後,他把矛頭指向意義的最後要塞—自由主義的真我。所謂真我,其實只是腦神經活動建構出來的幻象。「相信自己的感受」、「尋找自己的真心」,是人類最後的神話。事實上,自由意志並不存在。哈拉瑞的推論非常具有說服力。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他之前推廣的那些世俗價值豈不是都沒有根基?我們還憑什麼去相信這些價值實有其事而且值得追求?
在最後一章,哈拉瑞罕有地談到自己的個人經歷和感受,並且揭開了他的思想底牌。他沒有說他是佛教徒,但他從博士研究時期便開始練習冥想(或可稱為靜觀、內觀、禪修)。冥想教曉他一件事—我們唯一能直接觀察和研究、完全不假外求的對象,是我們的心(mind)。每一刻的心的活動,是我們唯一能夠觸及的真實,其餘的全都是幻象。這很好。一個歷史學家從冥想中獲得啟發,開啟了一種新的史觀,這絕對沒有問題。問題是,他在明知是沒有意義的世界中,試圖從事有意義的討論,並且鼓勵大家建立意義、守護意義,這樣做究竟有否自相矛盾?還是這樣說只是為了安撫讀者?我相信心思細密如哈拉瑞,他是有解答的,但他沒有說清楚。我們留待下周繼續談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