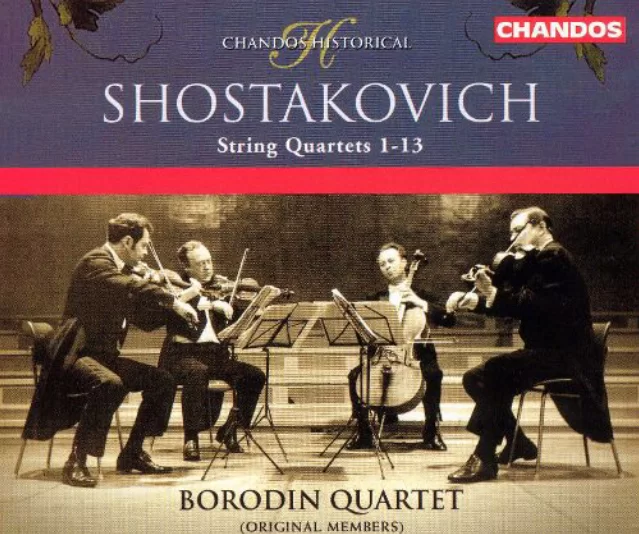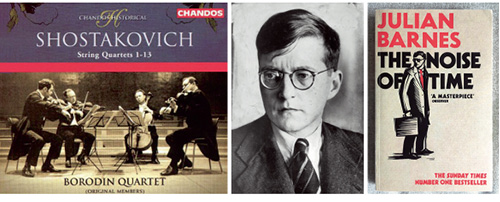有文學常識的讀者都知道,小說是虛構的。但是,某些類型的小說總會令人忍不住追問,當中的事情究竟有多少是真實的。這些類型包括歷史小說、傳記小說、自傳體小說,以及日本的私小說。其中傳記小說(biographical novel)的描寫對象往往是歷史上有名的人物,所以性質和歷史小說有重疊之處。英國小說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二零一六年出版的《The Noise of Time》,肯定會引起讀者對於內容真假的猜想,因為它涉及主角的政治和藝術人格判斷──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蘇聯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
當被問及為何要在這個時候寫蕭斯塔科維奇,巴恩斯說,自己在高中首次接觸俄語,又愛上了古典音樂,蕭斯塔科維奇早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蕭氏是二十世紀藝術和權力之間的鬥爭的象徵。他在斯大林治下如何受到打壓和限制,以及他如何嘗試保存自己的藝術完整性,甚至不惜向權力低頭和妥協,箇中承受的痛苦,並不是生活在西方自由社會的創作者所能想像的。巴恩斯表示寫作要求作家跨越到自己身處的世界的對立面,而現在正好是時候寫這個題材。但他連忙強調說,絕不是因為普京掌權而寫這部小說。
很明顯,巴恩斯拒絕所謂的政治動機,就算是在如此高度政治化的題材上。他甚至會令人覺得,他要在當今「泛政治化」的文化藝術氛圍中,替「為藝術而藝術」平反。只要讀到小說互相呼應的開頭和結尾,那個優美得不得了,但又瑣碎得不得了(因而非政治化)的場面,那個超越「時代的噪音」的畫龍點睛的美妙三和弦,我們對小說家抱持的藝術價值便心領神會。(這段前言和後語肯定是虛構的:在二戰期間,主角蕭斯塔科維奇和一位不知名的友人,在大後方的火車站月台上,跟一個行乞者碰杯小酹。三個劣質玻璃杯,盛着份量不均的伏特加,輕輕觸碰的時候,發出一下清脆的三和弦。)這就是作者假主角之口(或者根據他所理解的作曲家本人的想法)所說的:”Art is the whisper of history, heard above the noise of time.”
蕭斯塔科維奇絕不是英雄,他甚至可以說是懦夫的典型。在極權國度多次被整肅,音樂被禁,甚至曾經徘徊於逮捕和槍斃的邊緣。小說正文的開場,是那個流傳已久的場面。為了避免自己在家人面前被強行拉走,蕭斯塔科維奇連續多個晚上拿着行李,通宵站在家門外的電梯大堂,等待秘密警察的出現。事件源於他的歌劇被斯大林親筆在《真理報》上批判為 “muddle instead of music”。對一個音樂家來說,那等於宣判了死刑。蕭氏幸運地避過此劫,因為負責他的案件的主管者自己先被清算了。
到了戰後,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決定派員參加在紐約舉行的文化及科學界促進世界和平大會。斯大林親自打電話給蕭斯塔科維奇,指派他為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因為他在西方擁有很高的知名度。蕭氏在無可選擇下答應了,結果換來的是一趟屈辱之旅。他當眾讀出黨為他準備的講稿,公開否定他心中一直崇敬的同鄉史特拉汶斯基,完成了一場人格自殺。西方世界的支持者在他入住的酒店外呼喚他,只要他從窗口跳下去,他們會用救生網把他接住。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不願意遵從嗜血的人權鬥士的旨意,成為殉道者。
然而恥辱並未停止。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政治融冰,壓迫看似緩和,但蕭斯塔科維奇已經失去了抵抗的意志。他被「邀請」入黨,那個他一直拒絕加入的,殺人的共產黨。可是,他最後屈服了,為了保存自己的音樂。據說入黨之夜他痛哭流涕,之後寫了《弦樂四重奏第八號》以明己志。當然是以隱晦的,諷刺的方式。之後,他簽署過許多惡名昭彰的公開信,譴責過許多忠良的異見者,包括索忍尼辛和沙卡洛夫。蕭氏的後半生,無疑是不光彩的。如果要幫他開脫的話,也只能說他天真地相信,藝術超越政治;作為政治人的他只是一具行屍走肉,但作為藝術家的他,到最後依然奮力保護音樂的純粹。
以今天對正義的嚴格要求來說,這樣的理由肯定是不收貨的。連帶寫蕭斯塔科維奇而又不批判他,甚至還同情他的巴恩斯也很有可疑之處。又或者「懦夫」兼「同謀者」蕭氏根本就不值一寫。對於為何以這個人物為小說對象,巴恩斯除了訴諸個人喜好,似乎不願多說。他只是說:”At a certain point I thought now is the time to write about Shostakovich”。我私下認為,他對時下流行的簡單化和兩極化的政治道德思維,是不感認同的。
有評論認為,巴恩斯筆下的蕭斯塔科維奇的性情不夠俄國,太英國了。可是,什麼才是「夠俄國」呢?我倒以為,這反而是一個英國小說家寫一個俄羅斯音樂家的有趣之處。重點並不在於這部小說夠不夠「真」,而是在於,在這樣的文化落差和處境對立之間,如何產生另一種對於「真」的理解。這不是事實上的真,而是藝術上的真。
巴恩斯的成名作,一九八四年的《Flaubert’s Parrot》(《福樓拜的鸚鵡》),其實也可以算是局部的傳記體小說。二零一一年獲得Man Booker Prize的《The Sense of an Ending》,主題卻是記憶(以至歷史)的不可靠。(去年電影改編上映,港譯片名《謎情日記》。)難怪《The Noise of Time》出來的時候,讀者會猜想這次不知會玩些什麼花樣。巴恩斯誠懇地說:「當你閱讀的時候,我希望你相信一切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