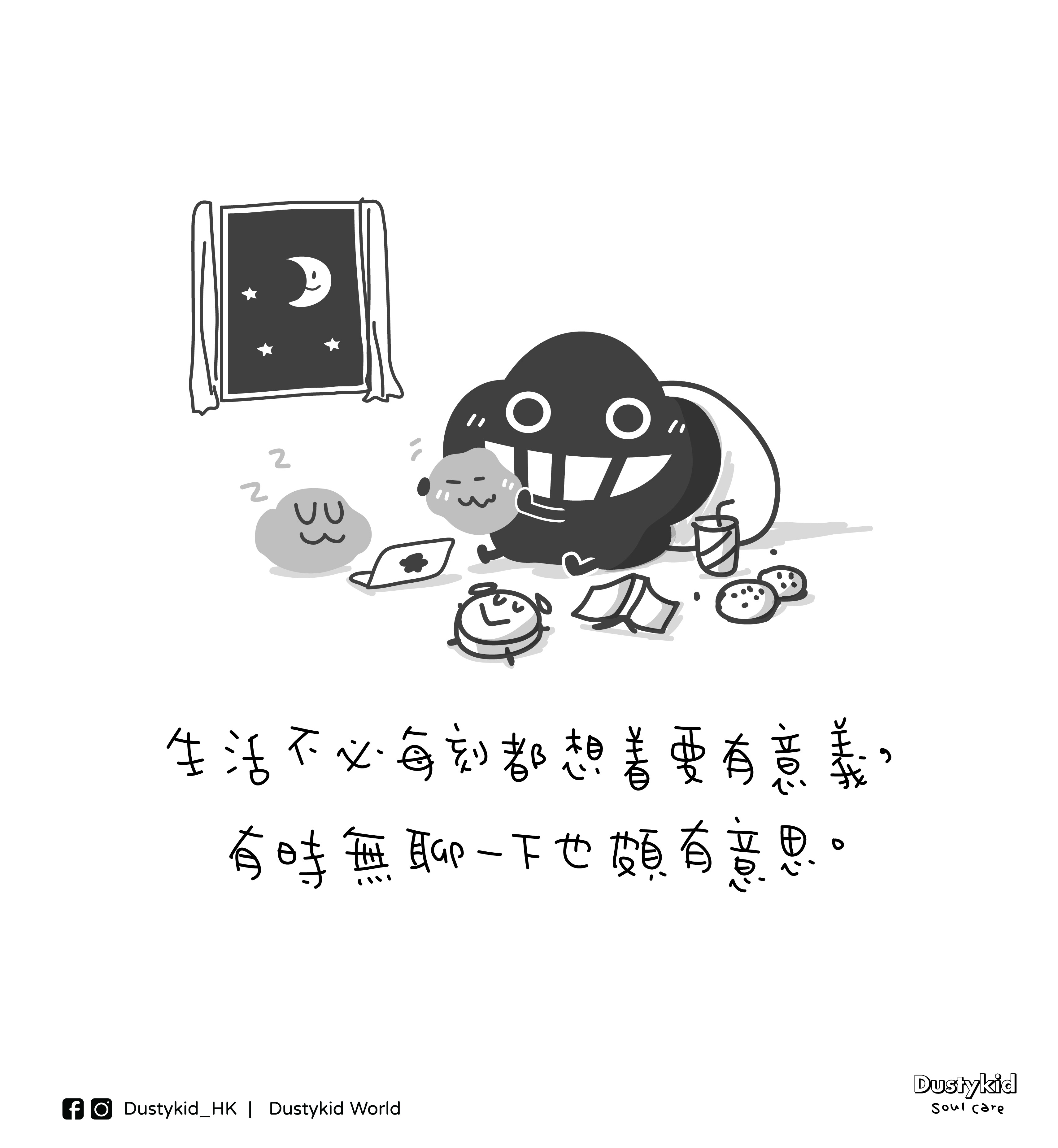十二歲那年,輝仔在練習打水漂時遇上了阿奀。
嚴格來說,輝仔從來沒有練成,當水漂掠過海面然後彈跳出來,輝仔以為自己成功了,卻見波濤中冒出了一頭藍色怪物,水漂只是剛好敲中了它的頭。輝仔嚇得想逃,不慎被石灘上的蠔殼絆倒,只能撫着擦傷了的膝蓋說,好痛。此時怪物也走出水面,摸着腫起了包的頭說,好痛。
輝仔這才看清,怪物也是個人,身高與他相約,有着人類的臉容,唯一分別是怪物皮膚呈淺藍,手和腳掌有着魚一樣的蹼。怪物察覺到輝仔的詫異目光,看着自己的蹼說,那是用來游泳的,在水裏會變大,只要用力游,速度跟人類的水面飛行器不遑多讓。輝仔說,那不叫飛行器,叫水翼船,專門載人去澳門玩。怪物問,澳門,是指大海的另一頭嗎?輝仔說,對,大伯說那邊有個主題樂園,可我沒去過,然後你是一隻盧亭吧?怪物有點傻眼,像盯着一種異樣生物地看着輝仔,說是的,雖然用一隻來形容有點冒犯,可你比我之前遇過的人類都淡定多了。輝仔帶點神氣地說,也是大伯教我的,他說大澳海裏住着不少盧亭,有時候會偷偷上岸,偷村民的雞來吸血。怪物說,那是污蔑,我們是只吃魚和海藻的素食者。這時輝仔有點沒那麼懼怕了,站起來伸手說,你好,我叫陳旭輝,村裏的人都叫我輝仔,你呢?怪物說,真羨慕,在我們的習俗裏,我們跟貝殼和石頭一樣,都沒有名字。說罷,怪物跟輝仔握手。
第三次見面時,輝仔為怪物取了個名字,阿奀,原因是怪物跟輝仔一樣,都長得瘦削矮小,像永遠長不大。不大合起來,就是一個奀字。輝仔沒告訴阿奀,其實這是他的乳名,他討厭極了,如今轉贈給阿奀,算是轉移了詛咒,把不喜歡的那個自己永遠留下。
二人每次都相約在黃昏,以輝仔失敗的打水漂為記,只要聽見水裏傳來連續的石塊沉沒聲,阿奀就會飛速游至岸邊石灘,上水相見。他們習慣躲在一株細葉榕樹下聊天,從大海聊到星辰,從電視裏溫兆倫推邵美琪出火車聊到珠三角白海豚的歌聲,直到夕陽完全隱沒在海平面,輝仔才會摸黑趕回大澳市中心的家裏吃飯。有好幾遍,輝仔晚了回家,到市中心卻趕不上橫水渡,知道到家就要被阿媽教訓,阿奀居然叫輝仔踩着他的背,載着他直接游過水裏,穿梭在棚屋底下的水道,直抵輝仔家裏廁所後門。吃飯時,阿媽不虞有詐,只問輝仔怎麼混身魚腥味。
阿奀告訴輝仔,盧亭的歲數跟人類迥異,身體會隨着潮汐起落而變化,某些盧亭族羣為求長生不老,會不斷追逐海平面的高度而遷徙。輝仔為這文化差異感到奇妙,說你和我這麼聊得來,證明你的歲數也跟我差不多吧。阿奀笑笑,說大概吧,希望如此,像你這樣歲數的人類通常都在做甚麼?輝仔想了想,說,上學。
學校長跑日那天,大嶼山西受一股雨帶影響,傾盆大雨,準備在大澳的大街小巷裏好好發揮的長跑高手無不掃興。輝仔讓阿奀換上了自己的校服,趁着大雨,帶着他在大澳和學校裏繞了一圈。阿奀咬着輝仔買來的砵仔糕,滿足地說,這是他第一次偷上陸地那麼久,盧亭流傳着不少關於人類的恐怖傳說,沒想到都是假的,他也要帶輝仔去一個地方,以示還禮。
輝仔從大伯那邊借了一隻小舢舨,訛稱要跟朋友去釣墨魚,然後在一個大霧的清晨在舊碼頭等待阿奀。沒多久水裏泛來波影,阿奀如約而至,只見他一手抓住小舢舨,雙腳往水裏一撐,舢舨即像裝上了摩打一般運動起來,速度飛快。阿奀帶着輝仔來到香港水域的西南邊,是一面無際的伶仃洋,阿奀說這裏水底下埋藏着一隻人類的沉船。只見阿奀不用吸氣就往下沉,到再次冒出水面時,手裏已多了一塊金色的方塊,是黃金。輝仔詫異,說不可能,沉船寶藏該只是出現在書裏的橋段。阿奀讓輝仔親手摸了摸金塊,接着又把它重新沉沒,說,從海底來的東西,只屬於海底。後來,輝仔在圖書館裏找到一本掌故,記錄了一段日佔往事,日本商船在白丸號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十三日後,在前往廣州的途上誤觸水雷沉沒,傳說船上包括漢奸廖永清,及他從民間搜掠回來的八噸黃金。輝仔在書上塗鴉補充:不是傳說。
看沉船那天,連夕陽也是金色的,輝仔孤身飄浮在伶仃洋上,沒半點懼怕,看着這距離地球一億多公里的熾熱恆星被海水逐點融化。輝仔說,我大伯病了,親戚說不樂觀,叫我明年開始轉去九龍念書,跟我姑媽一起住。阿奀說,嗯。輝仔說,每個周末,不,每個星期五,一放了學,我就會趕回大澳,無論這個世界怎樣變,我們一直都會是好朋友,對吧。阿奀沒答話。輝仔等了片刻,再問,對吧?阿奀終於說,嗯。輝仔察覺阿奀反應有點奇怪,只見他把半張臉隱在海裏,有無限心事。輝仔說,怎麼了,哭嗎。阿奀沒回話,轉頭盯着只餘半邊的夕陽,頓了良久,說,有件事,我一直沒跟你說,是關於盧亭和人類的。輝仔說,甚麼。阿奀說,盧亭和人類之間有一個詛咒,注定兩個物種要互相遺忘。一,只有未成年的人類才會看見盧亭。二,只要人類在成年後有過一次戀愛,就會對曾經見過盧亭的事忘得一乾二淨。輝仔愣了愣,說,不好笑。阿奀看着他說,是真的,不然你猜,為何千百年來,盧亭於人類來說只是傳說?這是因為你們跟我們不同,你們終會成長,終會變老,你們會戀愛,你也會,你會離開這裏,會結婚生子,輝仔,早晚一天,你肯定會忘記我的。輝仔說,不會,不可能。阿奀沒有說話。輝仔焦急說,我肯定不會忘記你,我會記住大澳的一切,輝仔焦急地伸出小指,要跟阿奀拉鈎,說,我們約定,我不成長,不去九龍,更不談甚麼戀愛,我們待在一起,好不?阿奀始終不敢伸出小指,不敢輕易許下這不會成真的諾言,說,輝仔,感謝你,你是我第一個人類朋友,謝謝你給了我一個名字。輝仔的舌尖嘗到了鹹,說不清來自海水,還是眼淚。
許多年後,大澳對開的海域建了大橋,四十歲的陳旭輝和老婆和兒子乘坐金巴從澳門回香港,他看見一望無際的伶仃洋,剎那間,一個遠古的名字蹦進了腦海。陳旭輝若有所思,於老婆耳邊說,我有沒有跟你說過,小時候的我特別瘦,村裏人都叫我奀仔?老婆半睡半醒,說,沒。陳旭輝再問,那我有沒有跟你提過一個朋友?老婆說,車到了再跟我說吧。金巴沿着大橋越過了大嶼山岸邊,陳旭輝遙遙看見大澳的石灘上站着一個少年,正朝着大海打水漂。水漂在波濤上跳彈。一下,兩下。最後沉沒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