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咔嚓」一聲,錄音帶播完了,夜涼如水,萬籟俱寂,我甚至聽得見我茶杯內一朵茉莉花綻開的聲音,月亮自水平線外墜下的聲音,整個獵戶星座燃燒的聲音,和我早逝的三哥死去的聲音。」
以上來自羅啟銳收錄於《兩毛錢往事》的文章《愁時獨向東》。
二○二二年,導演兼編劇羅啟銳走了,他曾說過,電影前的酒會和喪禮一樣,忙亂,猝然。記者相機「咔嚓」一閃,把人生的遭遇,完美地跳接起來。羅啟銳就像他筆下剛烈的木棉樹,火紅的花,「撲通」一聲,從天上決絕地掉到地上,然後,化為輕煙,又回到了天上。
作為電影人的羅啟銳,帶給人難以忘懷的光影;作為寫作人的羅啟銳,好像是從《新報》開始,一路寫到《明周》,或斷或續,寫了幾十年,陪伴許多讀者一起度過人間的悲歡離合。羅啟銳不管是寫往事還是人物,佻脫之間,總帶着湮遠的哀愁。這種「羅啟銳體」,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羅啟銳下筆,經過深思,可是,往往橫加一筆,突然逸出常軌,帶着畫面,帶着聲音,帶着傷懷,帶着諸般冷知識,在你猝及不及的狀熊下,給你一場捧腹大笑,或者一種月照底下蕩漾在咖啡杯裏的愁緒。
他寫一位水上新娘,不着墨於水上新娘遇見甚麼遭遇甚麼擁有甚麼,而着墨於水上新娘沒有甚麼,結果他寫的是「沒有丈夫照片的女人」。他寫深水埗一位盲眼乞丐,一開頭寫他「其他感官也還未發展得好」,後來寫他沿街逐戶行乞,一直摸到街尾,猶不知已到盡頭,站上了欽州街口,靦覥地對着寂靜的橫街行乞,面前空無一人,長街落寞,孤清的呢喃,甚至沒有回響。他寫自己認識的印第安人,那人的曾祖母叫「忽然大笑」,祖母叫「偷眼瞧人」,愈聽愈覺好笑,到印第安人問他姓名,他說是「鋒利地打開」時,他們簡直笑至人仰馬翻。一刻歡笑,一刻哀愁。這邊廂,一個叫阿崩的乞丐笑他「和矮」(儍仔),那邊廂,「傻仔」一個人獨坐向東的露台感念逝去的親人,想像他們幻化成南加州的一口空氣,或者黃山上的一塊巨石。
他出席陳百強的喪禮,喪禮播着歌曲,他想到了電影的術語「剪畫留聲」,那是因為畫面太長,但是聲音仍然重要,所以聲音保留到下一個場景。
人生,也有許多「剪畫留聲」。我們無法告別一個作家,因為作者透過文字,形成了另一種生命形式,自此以後,生命與生命之間,還會有無數次相遇。直至最後一個讀者忘記了一切,作者的聲音消逝,作者才會真正離開。
「只是,已經牢記了的東西,原來是不能忘掉的。」羅啟銳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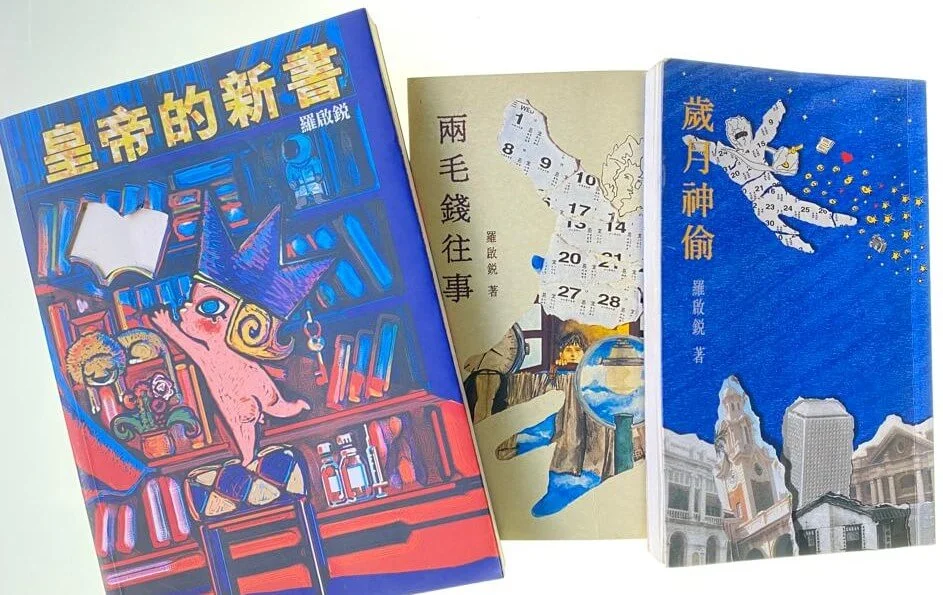
以下節錄羅啟銳的文字片段:
《沒有丈夫照片的女人》:
社工為她申請公共援助的時候,問她還有甚麼需要,她想一想,說跟了男人多年,連他的一幅照片也沒有,可否問電視台取當日遞解返大陸的錄影帶,社工說可以,之後又是一段淒冷的沈默。
我忽然記起當日拍下了一些他們一家回鄉的照片,回家尋找,底片已不見了,只好從剪貼簿上撕下照片,像撕掉一些借來的記憶般,還給這個飄浮海上、沒有丈夫照片的女人。
《阿崩》
阿崩每天穿七、八層髒臭衣服,沿門求乞,咧開崩口傻笑,問些似是而非的問題,沒有人知道他在說甚麼,除了我的祖母。
……他笑着用髒手為我剝龍眼殼,我更不要;他竟然跟我的祖母笑起來,指指我說:「和矮!」像長輩取笑小孩「傻仔」一樣。
那天晚上祖母跟我說,阿崩想返大陸,因為上邊有他舊日的朋友。祖母給了他三十塊錢路費,那時候我很奇怪,一個如此醜陋襤褸的人,是怎樣過海關的。
接着的兩天,我還開始想,阿崩是怎樣理頭髮的?他到那兒上廁所?他可以進戲院嗎?……直至他忽然又出現在我家門前,忿忿地告訴祖母,原來因為「無證件,過唔到關」。
「喎興顯,啊唔奧甖,囂!」他說。
《亡目》
「俾少少錢……俾少少錢我食飯……我未食飯。……」就是這樣。
惟是小時候的我,卻聽得又怕又感動,沒有零錢給他的日子,甚至有點不好意思地別過頭去,不敢看他,彷彿也怕他會看見我。
亡目的他當然甚麼也再看不見,事實上,他的其他感官也還未發展得好。有一回我看見他自青山道逐戶逐戶的摸,逐個門口停下行乞,直至他最後停在街尾的欽州街口,還以為是另一個大店舖的門前,於是又靦覥地對着這條寂靜的橫街行乞,面前空無一人,長街落寞,他的呢喃也只好孤清地散向處遠貧瘠的舊深水埗,甚至沒有回響。
《輪迴人間》
我是真的相信,世上有輪迴這麼一回事。
……
只是往事前塵,已無從追認;血肉相連,刻骨銘心的感情,已無從思憶。
細想起來,其實十分悽愴。自從父親猝然逝世之後,我想這問題想得更多,聽說輪迴轉生,全因修為不足,才會再次投胎做人,受人間的苦痛,假若通靈得道,是會輪迴幻化,作一朵雲、一棵樹、一隻信天翁、一下閃電、一段時間、一種感覺,甚或一些我們完全想像不到、理解不來的存在方式。
每念及此,便猛地感到一腳踏空,心事浩茫。
所以,如今我默然獨處的時候,常會神經質地用我一切形而下、形而上的感覺,去試圖接觸我已逝的親人,他們正以甚麼形態探問我呢?
是我在南加州唸書時偶然吸入的一口空氣?在黃山高峰上攀過的一塊大石?還是我每天早上盛咖啡的那隻瓷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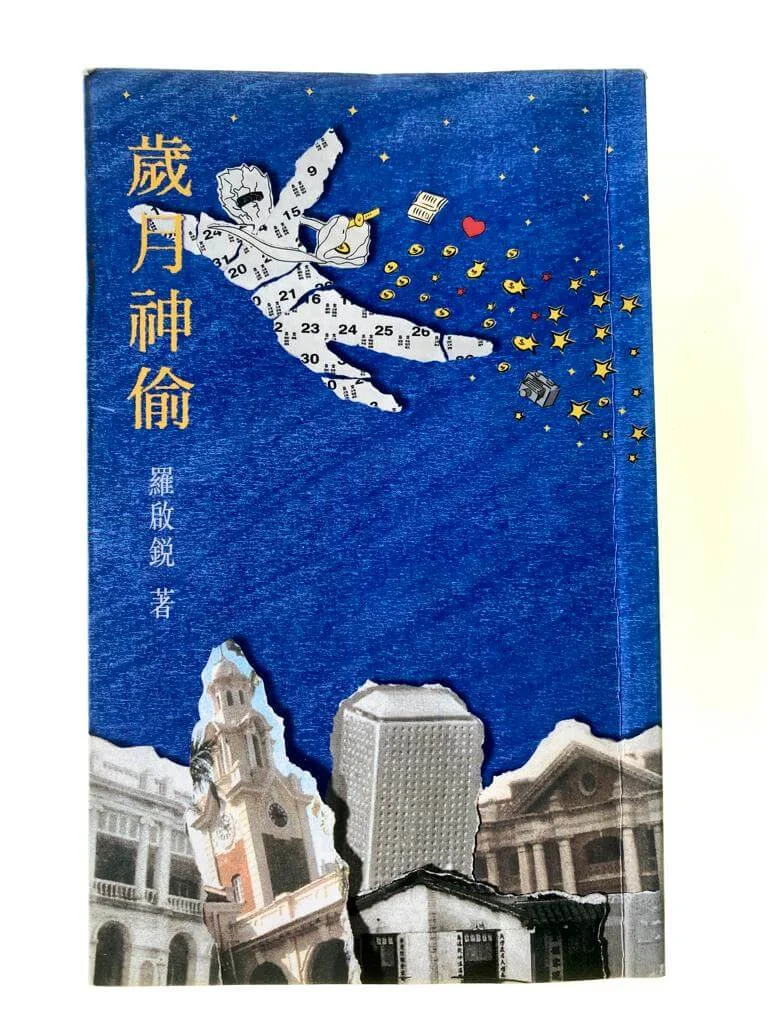
路也有疲倦的時候
。
(原詩和羅啟啟銳的引述都這樣,句號另開一行——純猜想:因為太疲倦,路也要中斷,而作者要費力歇息好長一段時間,第二天才能補回那個句號)

《怪名字》
我朋友的曾祖父中國名字是司徒耀祖,印第安名字是「斑點尾巴」,曾祖母叫「忽然大笑」,祖父叫「盤坐思想」,祖母叫「偷眼看人」,我越聽越覺好笑。
他祖父不明白我笑甚麼,反而問我中文名字的意思,我說是「鋒利地打開」。
他們聽後,簡直笑至人仰馬翻,問我其他中國人的名字是否一樣怪。我說大概是吧,我們有一個議員叫「飛行的鵬鳥」,另一個叫「銘記一根柱」;我們最紅的演員,一個叫「光潤地發射」,一個叫「疾馳的星星」。
《倒轉唸英文》
一老一少,一中一西之間慢慢居然做了朋友,玩得非常痛快,巷頭追到巷尾。有時吵得太厲害,爸爸會不以為然地瞅我一眼。
記得這見習幫辦曾跟我說:在香港,英文很重要,二十六個字母要熟得能倒轉來唸,才可以出頭。
稚氣又好勝的我,真的開始ZYXWVUT……地倒轉練習起來,跟着的那個星期天,他又跑來爸爸檔口,我正要洋洋自得地表演我的新伎倆,卻偷聽到他跟爸爸說:
「新嚟嘅『大寫』話以後每檔要加廿蚊,過節就一個『綠衣』五雞。」
我看見爸爸跟他抗辯了一會,終於頽敗地從抽屜取了些錢給他,有大紙也有碎銀,又看見大哥冷冷地望了這見習幫辦一眼,我忽然明白過來。
到今天,我仍然可以流俐地倒轉背誦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並且非常痛恨自己懂得這雕蟲小技,只是,已經牢記了的東西,原來是不能忘掉的。
《愁時獨向東》
直至現在,情緒低落的時候,我還是會坐在向東的露台,從月出看到日上,整整十二個小時,靜聽着自書房傳出來的蔣月泉,或者母親為我錄下來的「南音蛛絲琴」,直聽得肝腸寸斷,萬念俱灰。
歌聲隔着玻璃傳來,隱隱約約,尤其淒美動人——
「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
有時「咔嚓」一聲,錄音帶播完了,夜涼如水,萬籟俱寂,我甚至聽得見我茶杯內一朵茉莉花綻開的聲音,月亮自水平線外墜下的聲音,整個獵戶星座燃燒的聲音,和我早逝的三哥死去的聲音。
(以上節錄均來自《兩毛錢往事》,羅啟銳,1994,天地圖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