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人生中填過幾多張form ?幾多張要填寫婚姻狀態?」岑子杰問記者。「每一次要填寫婚姻狀態,代表那一項措施也是與婚姻狀態有關。」報稅、買保險、申請學費資助、申請公屋居屋法援……數也數不清。
大多數人看婚姻,只見誓約的「神聖」一面。假如婚姻神聖不可侵犯,為什麼還要分成各種狀態?未婚、已婚、離婚、喪偶,狀態分類透露了婚姻的「功能性」一面,其實也是一個用作維持社會穩定和便利行政的制度。
既然一個人的「婚姻狀態」是如此重要,何以香港的婚姻法例,依然未能涵蓋為數眾多的「一小撮人」?

⚡ 文章目錄
不如先歸還所有人權?
岑子杰是彩虹行動成員,早前入稟高等法院,要求法庭聲明本港法例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的做法違憲,於九月中被裁定敗訴。法官周家明認為,申請人要求法庭將同性與異性婚姻完全視為同等,此舉野心太大(too ambitious),法庭只能審視特定政策或法例,視乎個別情況是否違法或違憲。
法官引述平機會去年六月發表《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的研究報告,假如有人挑戰現行政策涉及性傾向歧視,許多政策將會不堪一擊,部分甚至可能違憲。假如市民逐項政策覆核,或許會有勝算。早前有另一宗同志平權的司法覆核,法官認為香港公屋制度旨在滿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裁定政策不容許同性伴侶申請公屋的做法違憲。
「一條叉燒唔會賣,斬開十嚿,逐嚿賣就可以賣俾你。」當日往法院領取判辭後,岑子杰如此回應。今日接受訪問,他深入解釋了背後的理念。「如果人權是與生俱來,是否應該先將完整的人權歸還性小眾,再視乎社會有效運作的方式,決定『秤走』幾多人權?」
每一條法例其實都是一種限制,每一條法例都必然犧牲了部分人的權利。如何決定限制措施是否合理?政策需要符合「相稱原則」,其中一個重點是社會利益與個人權利之間是否取得合理平衡。正如司機有權在馬路上胡亂駕駛,但是行人就無法過馬路。交通燈的設計,其實分別限制了行人和車輛自由行走的權利,但是平衡了雙方合理使用道路的權利。

小眾議題 民主平台也難以處理
「現時的法例是先剝奪部分市民(性小眾)的權利,然後法庭要求市民逐項權利爭取,這種先後次序不是有問題嗎?」岑子杰不解。正如有人欠他一千元,為什麼他要求對方一次過還款是「野心太大」?為什麼要讓對方每次只還一元,分一千次還款?「就連對方是否欠債,法官都沒有明確判決。」
岑子杰認為,同性婚姻本來是政治問題,應該在立法會討論,法庭以三權分立的原則處理是無可厚非。「法治不止是由法庭把關,假如立法機構本身是邪惡,法官依法判案同樣是執行邪惡的人。」在目前的香港社會,明顯有一些人的權利被剝奪,立法或行政機關都未有處理。岑子杰質疑,法庭是否仍然可以視若無睹?
「即使少數社羣透過民主的政治平台爭取權益,其實都是浪費時間,因為永遠都是少數。」岑子杰表示,歐洲人權法院也有案例,小眾議題並非一定要交由立法或行政機關處理。「就算香港立法會全面直選,當選的議員會有幾多個是性小眾?就算選到兩個陳志全入去,面對另外六十八個議員,可以點打?」反之,法庭可以用一種超然於政治的視角,以公平、公義、平等的原則審視少數人的權益,相比之下是一個較為理想的平台。「這一切,視乎司法管轄區的人員,有多大道德勇氣。」

司法覆核不再是一個人的戰爭
「假如香港的司法機構跟得上國際趨勢的進步,司法抗爭的路線再辛苦,也不失為一條出路。因為在目前的香港,少數社羣難以透過立法或行政的方式,取回平等的權利。」岑子杰坦言香港的社運路線頗為可悲,無論如何改變受眾,也無法改變政治現實。這些年來,同志運動團體付出極大努力游說和教育,性傾向歧視立法的議題終於取得接近八成市民支持,相關立法卻依然停留在九十年代開始的諮詢階段,「諮詢期」已經超過二十年。
為了減少司法覆核的法援分擔費,岑子杰盡量令自己「保持貧窮」:寄人籬下、壓低自己的人工,甚至去讀一個社工學位散盡積蓄—最後「窮到」只需要支付七百多元的分擔費。然而,去年當選區議員,岑子杰上訴的話,分擔費會大幅增加至十萬元。「行入一條不一定見到出口的隧道,而且起碼兩年不能甩身,我並不傾向上訴。」

岑子杰從社運出身,一直相信羣眾力量。「司法覆核是一個人的戰爭,過程中難以有社羣參與。」他覺得自己不能代表社羣做決定,收到判辭之後,透過多個性小眾團體,發出「眾籌分擔費」的邀請。金額達標後,他再邀請社羣成員參與「傾偈會」,邀請法律界人士到場分析案件,由與會人士討論後決定是否上訴。
當日共有二十多人出席「傾偈會」,大多數人的擔心都非常一致,就是岑子杰一旦敗訴,會否牽連其他正在司法覆核的平權案件?律師解釋,當年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入稟,司法覆核公務員事務局的福利決定,以及挑戰稅務局以至政府對「配偶」的定義,在終審法院取得終極勝訴,案件已經「刻在牆上」。即使岑子杰敗訴,也不會影響「逐嚿叉燒買」,只是暫時不能「原條叉燒買」。
假如上訴的話,屆時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將會換成張舉能。假如張舉能一如坊間形容般保守,上訴是否浪費金錢?「張舉能上場後,司法制度會倒退還是進步?假如之後會有改善,我們也可以在十年後翻案。假如司法再倒退,不趁現在上訴還待何時?」岑子杰引述律師的解釋。

背後有三百多人同行
參與傾偈會的二十多人,最後一致決定繼續上訴,「我本來不想上訴,因為對人生有太多掣肘。當我發現有三百三十三人眾籌支持,加上二十多人一致決定,這次上訴不再是一個人的戰爭,背後有很多人與我同行,我反而覺得開心。」
「反送中運動改變了我。」岑子杰坦言,自己是從非牟利機構(NGO)出身,其實NGO也是一個專制的架構,缺乏民主成分。正如各大機構的年報,總是強調自己完成了多少工作,某程度上是需要顯示自己的能力,證明存在的需要。「在整場反送中運動,每一個團體都只是其中一部分。即使民陣遊行有二百萬人參加,當中起碼有一百九十五萬人,都不是對民陣有認同感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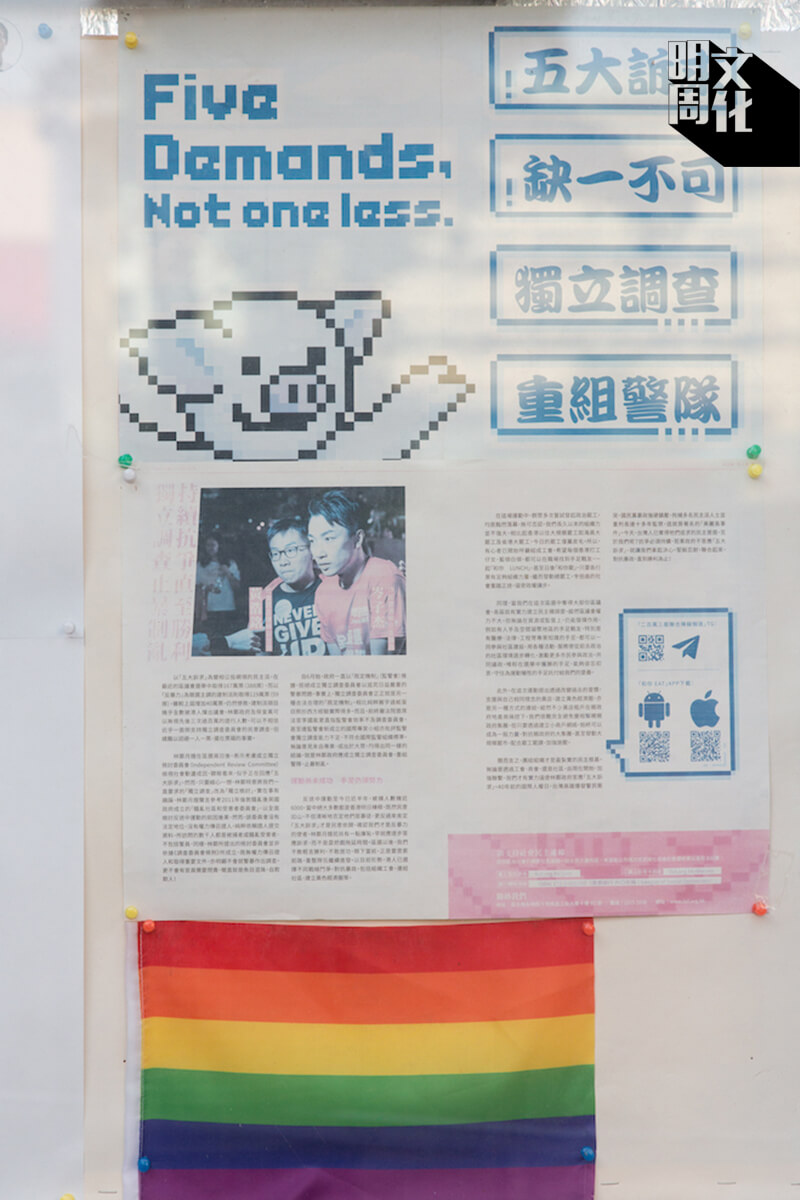
岑子杰領悟到,同行的人應該是持份者。以眾籌分擔費為例,他刻意不在個人專頁發布消息,而是透過各個同志團體轉發消息給社羣成員,用了一段時間達到籌款目標。「這樣說或許有點自負—在個人專頁出一個post,我相信一日內就可以籌到十萬元。」岑子杰希望集腋成裘,每一個付出的人都有份參與這一仗。「我不是社羣的戰士,不是比任何人聰明,也沒有付出得特別多。我只是希望關心性小眾權益的人能夠同行,共同選擇未來的道路。」

反對婚姻 為何司法覆核?
「其實我是反對婚姻制度。」岑子杰坦言,早於十年前,他的興趣是在於摧毀婚姻制度,而非爭取婚姻平權。他曾經認真考慮過,在外國與男朋友結婚後,在香港再找一個女性結婚,測試香港政府會否控告他重婚。「只要搞清結婚的先後次序,任何人都可以擁有『一夫』和『一妻』。」他打趣說。
反同陣營的其中一句口號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其實,直到一九七一年,香港才廢除「一夫一妻多妾制」。婚姻作為一種制度,方便社會運作,自有其功能。然而,假如所有親密關係都只能以婚姻來定義,岑子杰認為是不符合人性,等同立法規定每一個人都要在中午十二點進食午餐,而且只可以食豬扒一樣—一樣戇居。「假如每一個人的情感需要都只是來自一個人,這個世界就不會有人出軌,也不會有第三者。」
即使岑子杰如此反對婚姻制度,他依然在二○一四年與男友在美國結婚。他笑說:「其實我一直嘗試說服他,兩個人之間的關係神聖,在於彼此相愛,不在於一張證書,證書不會發光。」相處下來,他才發現,原來有人真的十分想要結婚。岑子杰反思,自己過去的倡議,似乎不是想摧毀婚姻制度,而是想摧毀「一對一」的選項。「膚淺、天真、沒有深度……我可以用任何形容詞貶低想要結婚的人,我可以選擇不結婚,但是我不可以否定別人想要結婚的權利。」

人際關係 何來等級之分?
突破思想框框之後,岑子杰終於願意答應男朋友提出的婚約。結婚一年多之後,岑子杰曾經問過丈夫,如果可以再選擇一次,還會否結婚?「老公說不會!到底是他明白了我的理念,還是開始對我厭倦?作為一個聰明人,我就沒有再追問下去了,哈哈。」
直到今日,岑子杰對婚姻的看法依然沒有太大改變,他本來就不認同狹隘的家庭觀念。「結了婚就是家人?如果我的老竇是何君堯,老母是譚惠珠,我不會有這些家人。」直系親屬、旁系親屬、遠房親戚、朋友、hi-byefriend、陌生人、敵人、仇人—岑子杰認為人際關係遠比這種等級分類來得複雜。
申請法援的時候,岑子杰需要申報家庭狀況。
「已婚。我不是和老公同住。我與前度同住。前度由我供養。(我答應過養他一世,難道要反悔嗎?)老公養得起自己。家母有男朋友。家父已婚。我由朋友供養。」
可以想像,法援署的職員在一問一答之間,相信是完全摸不着頭腦。
「我冇飯食,黃浩銘一定請我食飯,只要我夠厚面皮就可以。我全心投入貢獻社會,透過左翼的資源再分配理念去維持生活。」岑子杰直言,自己的人際關係觀,與社會主流的親密制度格格不入,他也不能清楚描述那種狀態。正如當初男朋友求婚,岑子杰開出三個條件:「我和所有的前度都藕斷絲連、你不會比我的社運工作重要、我一定會和其他人發生性關係。」

何謂家人? 血緣關係與親密無關
有一段時間,岑子杰與六、七個人同住,大家會經常討論共同關心的事情,那個也是他的家庭。這種人際關係,是流動的,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大家未能同住,但是並不代表關係因此疏離。「經常見面的人,關係也可以相當疏離—例如你的同事。」岑子杰相信,擁有相近的價值觀的確較易建立關係,但是並不等於價值觀愈近似,關係一定愈親密。多年之後,岑子杰發現,人際關係其實沒有道理可言。「熟得到就熟到,熟不來就是熟不來。」
當選瀝源邨區議員之後,有做過紅衞兵的街坊表示非常鍾意他,有藍絲朋友會在疫情期間關心他的口罩存量是否充足。在岑子杰眼中,瀝源邨有好幾戶街坊都已經是他的「家人」。過去一年,大家一齊打選戰,一起面對疫情,一起處理三級火災。一年之間,生生死死,大家都經歷過。街坊有時會叫他放工上樓食飯,又會主動到辦事處執拾。「所謂家人,不一定要有血緣關係,而是大家的親密程度足以與家人相比。」
說到最後,重點又再次回到婚姻。「我與老公對於婚姻制度的看法可謂南轅北轍,我相信自己改變了他不少,但是他對我的影響,對我而言更重要。」丈夫為他帶來另一個視角,令岑子杰明白,自己曾經有一段時間,無視了其他人相信「一對一」的選擇。「在爭取民主的過程,往往會發現自己也有許多不民主的特質。我要一直提醒自己,永遠都要重視人的權利,人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