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春天,全城戴著口罩迎戰那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抵抗SARS (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這場令人聞「咳」色變的SARS疫症,一共奪去299名香港人的生命,1,755人受感染。在集體恐慌的情緒蔓延下 , 香港彷彿呼吸到末日的濃烈氣息 , 我們經歷過怎麼樣的恐懼?時隔十年,SARS給港人心靈留下了 什麼印記?
曾經,沙士康復者吳女士在電視台訪問後第二天,一位街坊在搭電梯時劈頭蓋臉地問:「你是不是那個沙士康復者?」電梯到了G層,門一打開,街坊就衝出電梯門喊叫:「她是沙士康復者,她是中沙士的!」
即使時隔十年,歧視還在。也許只是少數。但無論是被歧視者, 還是歧視他人,心中都有一份恐懼。
「四月是恐懼高峰期,甚至有一種絕望感。」精神科專科醫生李德誠說,當特首夫人董趙洪娉「全副武裝」保護衣示人並連聲「 洗手、 洗手、 洗手」,重重保護令人感到沒有一處是安全的,每一秒鐘吸入一口空氣都可能隨時沒命。沙士疫症不知何時會結束,哪裏是盡頭?這是令人恐懼之處。
最初,大多數人以為只要不出門就可避免SARS。當疫情在社區爆發後,政府封鎖淘大E座,二百多名住客被隔離。此時家反而成為一個危險區。不少家庭開始每天用1:99稀釋漂白水清洗家具和地板。刺鼻的漂白水味時時刻刻經常提醒我們正置身於不安中。
2003年,有財經公司在金鐘一間快餐店做了一份調查,觀察午餐時間途經的頭一百個人有沒有戴口罩。恐慌和焦慮聚焦在4月22日,71%路人都帶上了口罩。

⚡ 文章目錄
回家像進入手術室一樣
從公眾場合回家,大家開始例行「脫衣」流程。李德誠這樣形容:「從外面回家好像是要進入無塵手術室一樣。在門外換拖鞋,然後蛇狀溜進屋內,讓兩歲女兒先等一等,徑直衝入臥室抓出早上準備好的塑膠袋衝入浴室,以慢動作脫衣服,以確保病毒不會擴散。脫下的衣物塞入塑膠袋立即打結。然後,將全身徹底沖洗清潔以確保無任何細菌會遺留。換上一身乾淨的衣服,小心翼翼地將打結的塑料袋交給菲傭,放置二十四小時後才清洗──確保衣服上的任何病毒開袋之前已死。一些朋友甚至將袋子放置四十八小時,他們在抵達辦公室開始工作之前會換一次衣服、離開辦公室準備回家時又再換一次衣服。
「進出車子前後,總是用消毒紙巾清潔雙手,有人即使單獨在車裏都戴着口罩。地鐵內有人咳嗽一聲,周圍的人可能四散。大家在公共場合都戴着口罩,用鑰匙按電梯、將超市買來的東西包裝都用消毒藥水擦拭才放入冰箱。
「不得不出去就餐的時候,我們來到死寂的餐廳,所有服務生都戴着外科口罩。 我們預訂包廂以策安全,我們不敢接觸門,只是輕輕踢開。許多餐館只提供一次性筷子,以及消毒酒精洗手液。陸羽過去給你一包牙籤,現在換成了給消毒濕紙巾 一包。」
他形容,當時的醫護團隊被分為「dirty team(抗疫隊伍)」和「clean team(非抗疫隊伍)」,dirtyteam專責在疫區護理與日俱增的疑似或確診的沙士病人,clean team與疫區隔離,一來為了避免感染,另外還有一種不言而喻的恐懼感覺,一旦抗疫隊伍「陣亡」,非抗疫隊伍將繼續日常工作保留火種。這是一種面對死亡的本能恐懼: 一些受感染的醫護人員病情嚴重,有的用上呼吸機,有的甚至隨時喪命。
醫護人員雙重擔憂
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何敏賢,曾研究過八十二名醫護人員和九十七名在醫院工作的沙士康復者。他的研究發現,兩組樣本的受訪者既害怕自己受到感染,又害伯傳染給他人,甚至怕傳染他人(親友、同事等) 超過了害怕自己感染。 而未得病的人比康復者更害怕被傳染,康復者更擔憂日後的健康問題,亦害怕被歧視。在康復者當中,對SARS的恐懼與創傷後壓力症密切相關。
沙士爆發初期,醫學界還未揭開SARS的面紗,對疾病源頭和傳播方式毫無頭緒, 當年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呼吸科主任許樹昌形容,情況就像「在黑夜的戰場打仗,看不到敵人在哪裏」。他於威院內科病房工作,上街吃飯湊巧碰見父母, 只可離遠打招呼。為了不讓鄰居知道他在 8A病房工作而產生恐慌,每晚午夜時分才回家,幾乎沒有和醫院及傳媒以外的人接觸。
除了威爾斯親王醫院,瑪嘉烈醫院亦是重要「戰場」,2003年3月底政府指定其為「沙士醫院」,集中處理相關個案,醫治了全港超過三分之一的沙士病人。蕭醫生當時就在深切治療部工作,他每天披掛上陣照料沙士病人。戴着N95口罩,進出病房要更換消毒帽、防御袍、手套、鞋套。有一次要給沙士病人插喉,感染機會很大, 更要穿上最高級別防備的「太空衣」。
同事間交流減少,面對面吃飯,卻隔着一塊玻璃。當接二連三有醫護人員中招,眼見同組深切治療部同事一個個染病,他心中更感害怕和難過。「最擔心傳染給家人。當時掙扎過,是否不回家了, 但疫情不知道什麼時候完,是一個月不回家,還是一年呢?」在宿舍小住幾天後, 他最終還是決定要回家,盡量如常過日子,「要盡力最大程度做好防禦。」他每天下班離開醫院前,先洗頭洗澡換一身衣服。回到家第一時間再洗頭洗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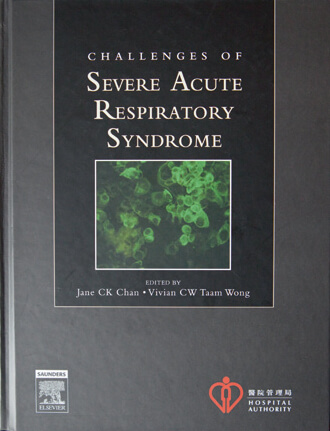
相較其他災難,香港人對沙士的恐懼有何不同?
精神科專科醫生麥永接說,第一、沙士是傳染病,源頭是什麼,怎樣傳染,如何避開,當年連醫學界都搞不清楚,充滿了未知。第二、沙士有別於911襲擊或地震持續時間短,病毒蔓延了幾個月,且不知道什麼時候完結。第三,沙士割斷了人與人的社交網絡。社會支援是面對災難的強大力量,但沙士病毒會人傳人,需要採取強制隔離,令人更為孤立。第四,沙士造成人對人的恐懼,互相躲避,引發歧視問題。

「不少康復者、喪親者仍受情緒困擾。例如每年三四月,天陰陰時,他們會觸景傷情。看到新聞會驚慌不安,有人出現回閃──回憶當年在醫院的恐怖畫面仍有身臨其境之感,依然感到恐懼。」作為 沙士互助會榮譽顧問,麥永接長期關注沙士康復者的心靈創傷。
就連心靈有創傷這個事實,有些康復者亦會一直逃避和否認。時隔十年,有位病人最近終於答應接受系統的心理治療。 麥永接說,如果不去處理,問題不會自動消失,「記憶好像一個衣櫃,裝了一些衣服。若你一直不去處理創傷的記憶,一直逃避,只將衣服塞入去就關上門,但每次有事要打開衣櫃,衣服排山倒海跌出來, 就會處理不到。如果要處理,就要把衣服拿出來,逐件逐件摺好,再放入衣櫃把它處理好。」

他說,沙士康復者要適應角色轉變, 從健康的人變成一個病患的人。身上的痛楚會不斷提醒心靈上的傷痛,心理創傷亦 會轉移為身體的痛感。對醫護人員來說, 康復之路更難,因為多了一重角色轉換,不僅從健康到病患,更從醫生變成病人, 從「醫人」變成「被醫」。
治愈心理創傷有幾個要素:人有盼望、 動力,多角度正面看問題、感恩自己所擁有、身處逆境時接受已經發生過的事情。「一切要從接受開始。如果好不了,也要原諒自己。看到自己有情緒,不要立即迫自己開心,不要與情緒打架,允許自己低落, 理解自己,也是情緒的一個出路呢。」


Q&A 恐懼是一種學習?

李:李德誠,私人執業精神科專科醫生、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
明:恐懼給身體的信號有哪些?
李:通常會腎上腺素大量釋放,瞳孔擴大、發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作嘔、肚痛、腹瀉、胃口減退、失眠、 腦海裏一片空白,回憶不起來,感覺不真實等等。
明:恐懼的本質是什麼?
李:恐懼實際上是一種學習。恐懼感是一種避免威脅和傷害的情緒,源自人類自我保護的生理本能,遇到危險或刺激時,伴隨恐懼而來的是心率改變、 血壓升高等生理上的應急反應,提醒我們防禦或逃跑。例如見到老虎,如果我們害怕,就會逃走。避開了之後就安全了。恐懼也可以是錯誤的學習,例如逃避了之後感到安全,不再恐懼,因此會不斷逃避。恐懼還可以是愉快的學習,例如有人喜歡看恐怖電影、玩蹦極等尋求刺激。
明:恐懼都需要克服嗎?
李:只要不過度,不影響生活和工作,大多數恐懼是不需要克服的。可問問他人,自己的恐懼是否合理?有沒有傷害自己或別人?
明:香港人最常見的恐懼是什麼?
李:在我的診症經驗中,最為普遍的恐懼是對人的恐懼,以辦公室欺凌為多。其次就是對死亡的恐懼,擔心自己的病好不了。「香港的焦慮症患者是抑鬱症患者的幾倍,而在外國則以抑鬱症居多。」李德誠指出,香港人敏感度很高,容易恐慌,一有風吹草動,容易過度憂慮,當然,忘記得也很快。他認為,當中的原因與歷史有關,香港曾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有種過客的心態,匆匆賺錢才是根本。還與教育有關,不主張獨立思考,「跟風」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