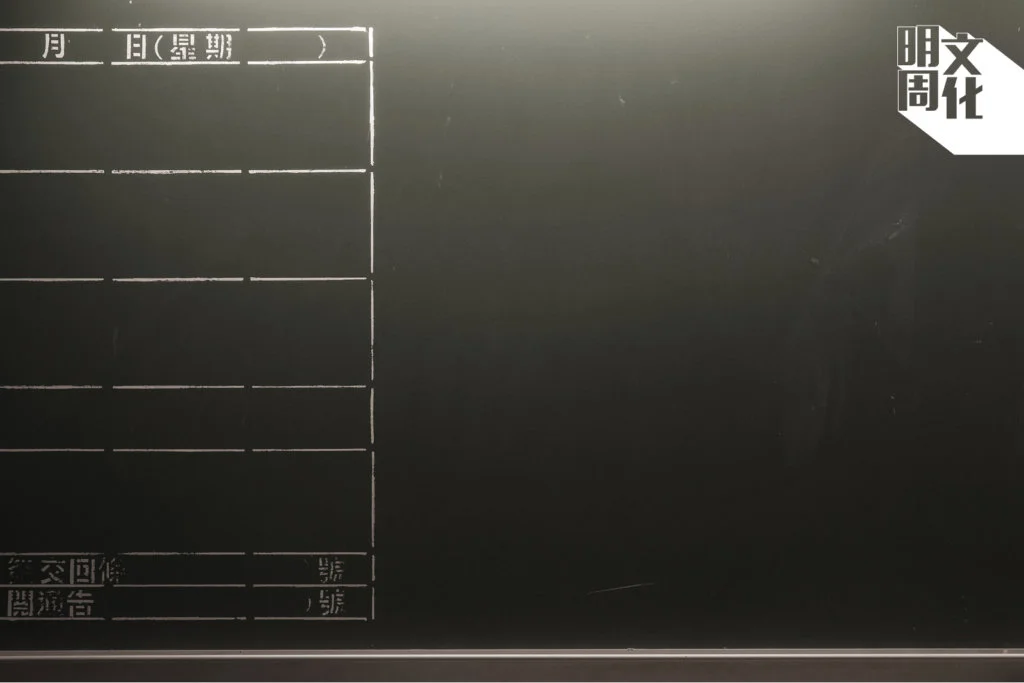幾年前興起悄悄話挑戰(Whisper Challenge),大夥兒輪流戴耳機,看別人口型猜句子。音樂遮蓋人語,對方臉孔愈是一頭霧水,答案愈偏離軌道,便愈好笑。但若然遊戲變成生活日常,大概就不好玩了。
聾人潘頌詩(Joyce)從幼稚園到中五都在聾校就讀,一直接受口語教學。小時候坐在班房,知識繞室而飛,她未能捕其聲,便捕其形,堂堂緊盯老師的唇,像在追撲轉瞬即逝的蝶。到底是「美國」還是「蘋果」?是「爸爸」還是「媽媽」?字庫有限,口形相似,思索得來,腦海已一片空白。老師愛在班房來回踱步,寫黑板時背對學生,頓時聲音畫面有問題,卻反斥學生看不懂是蠢。
一根稻草,可讓瀕死的人續命,也可壓垮駱駝。口語教學,或是後者。潘頌詩幽幽地道,中學生涯只學到兩成,壓力大得想過放棄。六小時後放學回家,一副乾癟皮囊癱軟在牀,像個洩氣的氣球,但魂魄的苦,絕不能告訴爸媽,因為他們覺得手語是歧途,想她走「正常」的路。
如今老舊時光都翻過去了,她闖出了一條新路,體驗過美國的聾人大學生活,回港後當上教學助理,更獲得特殊教育教學資格,透過「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在小學教英文和數學。課室內聾童和健聽學校一起上課,而她和一名口語老師同步授課。老師除了言傳,還要身教。過來人成了聾童的樹洞,從前走過未走過的路,都陪他們度過。
(對話經手語傳譯員萬可靖 Heidi 翻譯)
⚡ 文章目錄
學校煩惱
第一次與潘頌詩見面,是在語橋社資,她剛從學校趕來訪問。第二次相約在中環街頭,雨沾濕了薄衣,她面容始終和煦,打完一輪手語忽爾停頓下來微笑,接話前眼睛擠成兩條縫,直接豎起拇指說「是」,像鼓勵答對問題的孩童。
在學校裏,身為聾人成人榜樣的她也是笑笑的,待學生如子女。課室內,聾健接受同等教育,不刻意簡化課程,沒有誰比誰優勝。社交圈子有聾人,健聽同學老師願意學手語,甚至連校長也在跟她學手語。
這是三十年前的她無法想像的。她在家中排行第一,二妹健聽,三妹也是聾人,母親跟很多健聽父母一樣,篤信學習手語會阻礙學習。面對升學分岔路,手語與口語,須二擇其一。三妹到主流學校讀書,她從幼稚園起入讀口語主導的聾校,只有和同學聚在一起玩,才自然地接觸到手語。
當初她好不容易升上中五,內容卻與中一課程相若,不溫習已能考取好成績,會考還不能報中英數。於是她轉到主流學校,由中三重頭讀起。她覺得自己已很幸運,許多朋友讀主流學校都慘遭欺負孤立,只有自己未被訕笑,或許是因為擅長打籃球和游泳,老師都會請她出來示範。不過全校只有她一個聾生,又沒手語傳譯員,上理科堂時有圖片輔助,文科完全看不明白。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列明,聾童在教育場所應獲平等對待,以及學習手語的權利。如今望着爛漫小孩,她總覺得他們比自己幸福多了,至少在教育上體驗到公平,也有她這樣的一個伴。她跟同學打成一片,學校裏較調皮的,或有嚴重家庭問題的學生,會被捉去見社工,有聾童會跑來跟她吐苦水,訴說的都非學習困難,首當其衝的是家庭。
家庭裂痕
別人的說話,大可當耳邊風,但家人關係愛恨交織,似乎是聾人畢生的課題。九成聾人的父母是健聽,聾人夫婦的子女亦有九成健聽。同一屋簷下,言語不通,文化不同,容易遺下裂痕。作為過來人,潘頌詩擁有一顆同理心,容易代入那種揣揣不安的狀態。
小時候她想做老師,常在家豎起白板,佯裝教兩個妹妹有的沒的。全世界都跟她說,聾人只能做低下階層工作,連媽媽也覺得,做醫生律師老師只是在發夢。在家比劃手語時,二妹看着有趣,有樣學樣,手指一縮一放,原來能接通心扉。每次爸媽見狀,都會責罵妹妹做壞手勢,她看着不好受,心裏涼了半截。後來一家五口外出行街吃飯,二妹遞手比劃,媽媽怕路人目光在指間流轉,隨即板起臉孔,猛力撥開或箍住她的手指。手背烙下酡紅,妹妹扁嘴不敢說痛,但也在心中輾過不能磨滅的痕。
急性子的潘頌詩覺得家人橫蠻,根本沒耐性跟他們筆戰,動不動就生悶氣,暴躁陰鬱嵌於眉間。小鳥圈在籠中,學業和家庭問題捏住頸項,發不出啼聲,就想找一扇窗逃逸。她希望繼續升學,但香港的大學缺乏對聾人的支援。她轉而到銀行擔任保險文員三年,後來領取獎學金,決意離巢,隻身飛往美國讀數學。無聲鳥趕上千里路,順着自由的風漂流異鄉,抖落親情憶念,倒是一身輕。
香港沒有的自由
被折的雙翼,終能展翅。當時許多美國大學都為聾人安排專人,即時打出老師的講課內容。她的落腳點美國高立德大學,更是全球首間聾人大學,結合手語教學。《美國殘疾人法案》下,聾人使用學校醫院及康樂場所前,可申請安排手語翻譯員,絕大部分免費。「聾人想要的是平等機會。」她習慣了獨立,吃飯買機票活動訂位去銀行,按一下就有視像傳譯,不用勞煩健聽朋友,也毋須看臉色做人。美國生活拓寬視野,讓她首次體會到,什麼是快樂,什麼是人權。
在最自由的日子,她想起崩塌的家,思考怎樣重新建立關係。分隔異地的距離,反而醞釀出愛。二妹開始學手語,轉而從事教育聾童工作,媽媽也改變了想法,跟着一起學。她有她活在無聲世界,媽媽仍活在有聲世界,但有了手語,誤會少了,彷彿又融和在同一天空。
她想過從醫,美國有儀器代替聽筒看心跳,也想過做科研,但回港可試試推動社會對聾人的關注。回到香港,明明隔了六年,感覺卻像兜了個圈回到原點。在香港看電視直播仍然沒有字幕,聾生想入大專都要靠運氣。時至今天,看醫院急症,也未必有手語傳譯服務;想申請興趣班,攜同手語傳譯員,還得多繳一份學費;到聾會參加心理輔導小組,手語翻譯質素參差,無法療傷。

聾人可以做到任何事
世情千迴百轉,最後她到底也是投身教育界。她曾任職於聾人學校,其後到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任研究助理,先後到兩間學校做聾人教師。全職工作期間,她修讀教育榮譽學士(特殊需要)學位,希望為聾生和健聽生樹立榜樣,為殘疾人士充權。這是香港首次有使用手語的聾人,獲得特殊教育教學資格。她想用自己做例子,向學生證明美國高立德大學首位聾人校長 I. King Jordan 說過的一句話:「聾人可以做到任何事,除了聽。」
潘頌詩伸個懶腰,鬆一鬆久未舒展的骨骼,說今晚要出席攝影班,拍攝燈光閃閃的夜景,但翌日就要開學了,要早點睡,想精神奕奕地迎接學生。對着這班迷途小羔羊,她不會叫他們「看開一點」,也不會說「加油」,因為她知道他們已經很努力了。
一路走來,聾人努力學習從墮後的起跑點追上,但從來沒有人調整起跑線,沒有人拔走滿途的釘,也沒有人教過他們,跌傷後該如何包紮傷口。問她最想對聾人說些什麼,她揚起嘴角,轉出手背舉起拇指、食指和尾指;另一句是,伸出兩手食指慢慢靠攏、指向前方、兩個人字向前走路。
意思是愛你,與你同行。
聾人?聽障?: 「聽障(deaf)」從醫學角度出發,將焦 點放在聽力上的殘缺;「聾人(Deaf)」 則從文化角度出發,強調他們作為一個 人的特質。聾人社羣有屬於自己的手語、 文化、藝術、歷史和體驗世界的方法, 更以此身份自豪。
手語敗部復活記:一八八○年,米蘭第二屆國際聾人教育 會議通過議案,規定聾校禁止手語,使 用口語教學。 二○○八年,中國簽署 《國際殘疾人權公約》,列明要協助聾人 成長。二○一○年,第二十一屆國際聾 人教育會議宣布,推翻禁止手語的決定, 呼籲世界各國確保聽障兒童教育,尊重 所有語言和溝通形式。 過去數十年來,聾童只能接受單一口語 教育,令他們面對溝通障礙和社會孤立。 現時懂得手語的聾人只有不足四千,佔 全體比例僅約2.5%。中大手語及聾人研 究中心從二○○六年起創立「手語雙語 共融教育計劃」,每班級都設有一班共融 班,當中有五至六位聾童與健聽同學一 起上課,健聽和聾人老師共同教學,希 望促進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