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ROR事故】資深編舞批演唱會設計、服裝不顧舞者安全 不忿行業對舞蹈員剝削多時 倡設立工會爭取舞者權益 :業界要團結 行內人幫返行內人

上月舉辦的MIRROR演唱會,從綵排到正式演出,頻頻發生意外。最終,在上月二十八日舉辦的第四場演唱會發生嚴重事故,懸掛在高處的大屏幕突然墜下,至少兩名舞者受傷入院。及後,主辦方取消餘下演唱會場次。MIRROR演唱會事故一事,揭示了一直存在於舞者業界的問題,如舞者權益不被保障、舞台表演未顧及舞者安全、工傷索賠困難重重等等。資深編舞Alan提倡組織工會,團結業界力量,對抗不公,惟目前響應的舞者不多。但Alan盼感染更多同路人為行業發聲,同時,他祈望更多舞者願意參與籌辦工會,長遠改善行業生態。

舞者的無奈:他們並非不想發聲 而是不敢發聲
在MIRROR演唱會正式開始前,網上有傳資深舞者在總綵排時受傷。舞者疑似不滿製作單位忽視舞者安全,紛紛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全黑限時動態(story)以示不滿和抗議。其後,MIRROR的第四場演唱會更發生嚴重事故,意外除震驚全港外,亦續把舞者行業生態及權益問題,曝露於公眾視野中。
業界創意總監及編舞Alan在舞者受傷後所分享的IG Story,就曾被多次轉載。他在Story提到,「大部分舞蹈員都是年輕的,不敢發言不敢要求,怕得罪人,有地位的又不敢亂説話。」但他認爲,「如果連第一步發聲都唔敢做,更加唔好講要爭取之後嘅權益。」因此,他希望大衆能持續關注工傷舞者的賠償問題;同時他鼓勵同業勇敢站出來,為自己發聲,爭取應有的權利。

Alan擁有十五年跳舞經驗,曾擔任孫燕姿和郭富城演唱會的舞者。但在二〇一四年,他捨棄了舞者的身分。「當時慢慢意識到自己身體狀態變差,無辦法再做dancer。」Alan轉行的原因,也揭示着舞者的無奈,「編舞寧願搵後生嘅,都唔用啲有經驗但年紀大啲嘅dancer,依行嘅淘汰係好殘酷。但當新人上嚟,佢哋可能無咩工作經驗就會俾人打壓,同時,佢哋唔識deal價錢又得嗰幾年經驗,想有個高啲嘅價錢都好難。」雖然Alan不再是演唱會舞者,但他仍然關心這個行業。無奈的是,即使他願意為舞者發聲,但他所得到的回響仍然不多,暫時有十多個舞者回應他表示願意分享自己昔日的工傷經歷及發聲,他亦有感有心無力,「呼籲完大家關注,但下一步我仲可以點做,我都未知道。」
舞者除了被打壓薪酬外,還可能因綵排不足或舞台設計未有考慮舞者安危等原因,因工受傷。他留意到近年有主辦方或為了節省開支,縮短綵排次數和時長。然而,綵排不僅是為了讓舞者熟悉演出流程,更是為了讓舞者熟悉台燈、音樂、特效和機械等設計,與之配合。他指,不少舞台效果,如噴射紙碎和煙火,會導致舞台地滑,他亦曾見舞者因此受傷。「Dancer正式on show嘅時候,無時間諗下一步係點,都無辦法再去顧忌你啲燈或者機械啱唔啱,佢哋只可以完全咁將自己嘅安全交托比舞台製作組。」
除了舞台效果,Alan指出,服裝同樣會影響舞者演出的安全度。「啲服裝多數都無保護性,真係純粹為靚。」他舉例指,部分演出服裝的配飾會阻擋舞者的視線範圍,如頭盔和眼罩等等。加上,舞者身處鎂光燈照不到的地方,舞台照明度不足,會令他們容易踢到舞台裝置或不慎掉落舞台。因此,Alan認為綵排對舞者來說極為重要,「每次嘅綵排都可以增加dancer喺台上的信心,減少受傷嘅機會,但講真,好多時都只可以靠自己『執生』。」
更無奈的是,Alan表示舞者薪酬長期受剝削,演唱會舞者薪金三十年來都沒有上漲。擁有十五年的舞台表演經驗編舞及資深舞者Franco也認同。他向記者分享一個社交媒體訊息,當中列出舞者的薪酬。演唱會的主要舞者薪酬,一場公價為二千八百元,當中需參與演出八首歌曲的演出,若主辦方要求增加表演歌曲的數目,則會再按歌曲的數目來調整費用,而綵排費用則是按鐘收費,每小時一百元。而演唱會次要的舞者薪酬則更低,只有二千至二千五百元,綵排更只得五十元一小時。Alan認爲,舞者有時甚至需自行負責膳食、梳妝及服裝等開支,故酬金水平確實偏低。由於薪酬追不上通脹,Franco指普遍舞者均會發展副業來維持生計;最可悲的是,不少舞者的副業甚至比舞台演出的薪酬還要高,繼而放棄成為舞者的夢想。

若舞者不幸受傷,他們往往因無合約保障,導致索賠之路困難重重;或僅獲得一次性醫療性賠償,而非針對工傷損害工作能力而作的補償。Franco就曾在一次演唱會總綵排中不慎掉落舞台受傷,導致身體出現大片瘀傷。他估計可能因排舞師與舞台工程組溝通不足,導致綵排時,舞台突然無預警下降,令他一瞬間便掉下台。當時的他感到十分徬徨;加上他並沒有跟演唱會主辦方簽約,只跟舞蹈總監就工作詳情達成口頭協議,因此擔心難以追討賠償。最後,雖然主辦方主動為他承擔醫療費,但卻沒有保障其工傷後生計。他亦補充,他相信主辦方有為舞者購買保險,但保險並非針對個人,而是整個舞台演出,故他沒有得到保險賠償。因此,Franco在接受治療後仍堅持重返舞台演出,「搽啲遮瑕膏遮住啲瘀傷就照上台,你唔做就唔會有人工,所以都要照做。但如果有工會可以確保我哋工傷後仍然可以有人工,起碼唔洗擔心工傷之後嘅生計,咁我當時就唔會照上台。」
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倩文指,舞台表演行業普遍有三種聘用舞者的形式,分別為簽訂「服務協議」、自僱人士,及由「判頭」(承包商)分派工作予舞者。但絕大部份情況下,僱主和舞者間只會有口頭協議,但過程並不會簽約,屬短暫和單次聘用關係。蕭倩文亦指,即使有簽訂文件,大多僱主不會列明僱員的權益,例如工傷賠償及保險細則,故三種受僱形式皆對舞者不利。
Alan認為,雖然今次作出組織工會的呼籲,得到的回應不算熱烈,但他也理解為何舞者不敢發聲。近年的演出雖多了公開招募舞者的機會,但他指編舞和舞蹈總監仍有慣用的「班底」,或會固定錄用某些舞者。因此,若主動發聲或申訴,舞者擔心會被標籤,影響日後工作機會。作為編舞,Alan亦曾擔任「判頭」(承包商)。判頭是客戶與舞者間的溝通橋樑,舞者不會直接與客戶對話,故其角色較被動。加上,他指「Dancer比較年輕同乖,他們唔敢越權同製作方溝通。但說真,就算你去找他,佢連你叫咩名都唔知啦。」因此,舞者只能依賴編舞和舞蹈總監來為自己爭取權益,如加薪和追討工傷賠償。
成立工會阻力重重
有見舞者的種種無奈,Alan盼業界能團結一致,成立工會。「無理由因為個行業生態係咁,怕得罪人就唔去成立工會,我會覺得依件事有啲唔合理。同埋我始終覺得對舞者有合理的對待係好基本,我哋唔係有好過分嘅訴求,只係可能我哋人工三十年無加價,你加返價比我哋,服裝要符合安全等。」
然而,要成立工會也需面臨重重困難。他指,根據勞工處對成立工會的要求,會員需經常在香港居住,及正從事或受僱於與工會有直接關係的行業。而行內有不同的舞蹈種類的舞者,因此,發起人要先定義何謂專業舞者。其次是,即使Alan有意成立工會,但他認為若沒有足夠的成員和有權威的人士(在業界有影響力的編舞或舞蹈總監)參與,工會的作用仍然有限。Alan指,「我可以帶頭令成立工會依件事發生,再交由公平嘅選舉制度產生,但以我一個人嘅力量係有限。最後都要back to有權力嘅人。我唔算係有好多show接嘅編舞,變相大家聽我講嘢嘅機會就會細,但如果有啲權威人士加入,佢哋一個出聲已經可以令件事行得快咗同有說服力。」他盼在成立工會後,能長遠凝聚更多舞者的力量,改變舞蹈行業的生態。他特別希望,以工會力量施壓予演出製作方,在演出前先與舞者簽訂合約,為舞者爭取應有的權益。
對於日後工會的成立,Franco盼工會能列明舞者的加班津貼和安排,如為舞者提供通宵工作後的交通津貼或交通接駁。其次,他希望工會促請製作因應通脹、舞者的年資和能力等因素,上調舞者的薪酬。最後,曾經歷工傷的他,亦期望工會能為舞者爭取工傷後的保障。工傷或會對舞者造成長期影響,單次性的補償或不足以舞者傷後的生活。因此,他希望即使舞者因工受傷而無法參與演出,仍能獲取部份的表演收入以維持生計。他盼日後工會的成立,能長遠改善行業生態。
其他持分者應如何保障舞者權益?
蕭倩文指,不少舞者認為以自僱人士身分參與舞台表演就一定不受《僱員補償條例》保障,故他們因工受傷也不會向公司追討賠償。然而,若舞者對其工作沒有充分話語權或自主性,有可能會被界定為「假自僱」,舞者可爭取在《僱員補償條例》下得到工傷賠償。她呼籲舞者應在工傷後向勞工處呈報事故;同時,主動向僱主追討賠償,才能讓業界有先例可循,長遠保障同行的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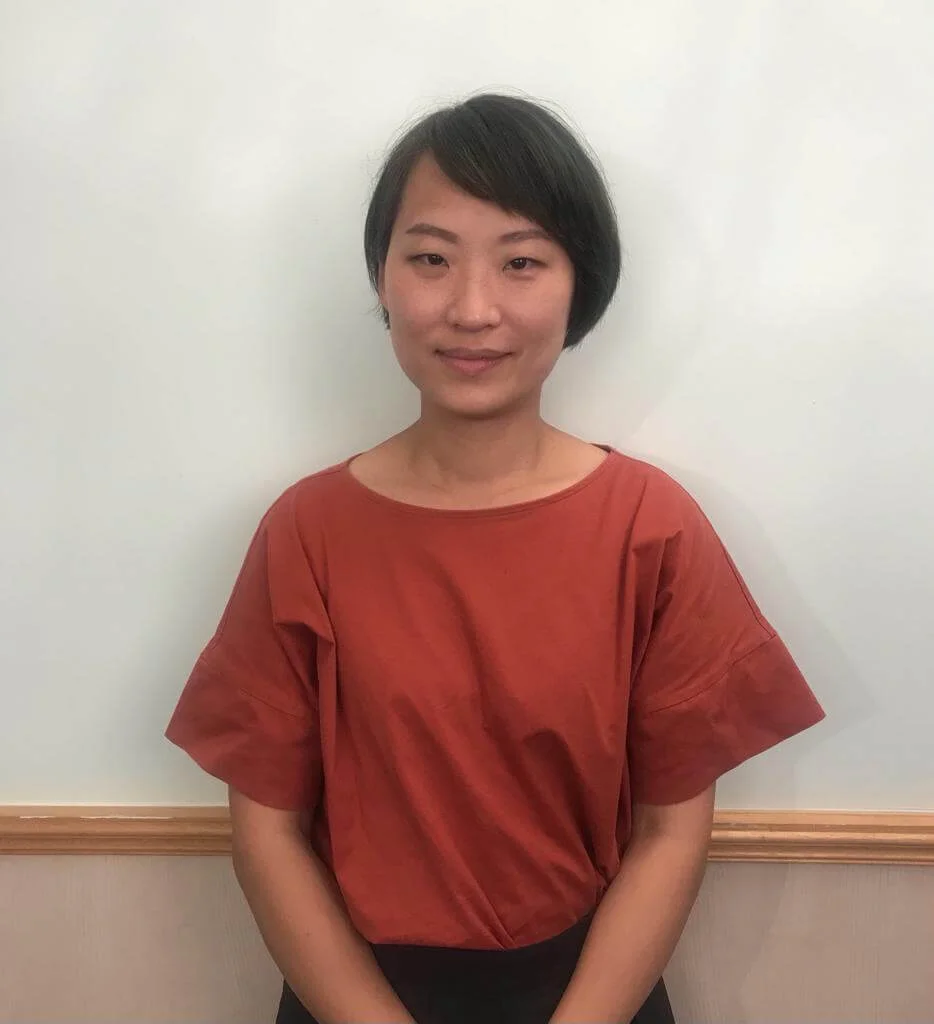
除鼓勵舞者發聲外,蕭倩文認為僱主及政府需負上保障舞者責任,「始終dancer可能係受壓迫一方,僱主同政府係好應該,而且有責任保障返佢哋。」。然而,她指普遍僱主所提供的保險只涵蓋短期或一次性的賠償。惟蕭倩文認為工傷的影響或以年計算,保額及賠償或不足以彌補工傷帶來的影響。她建議日後僱主應為僱員加大保額,保障舞者因工傷令工作能力損失的情況,及在合約清楚列明工傷賠償。
另外,她認為政府可強制規管僱主對僱員的最低保額,保障舞者工傷後的權益。而現時舞台工程亦會涉及不少重型機械及高空吊運等程序,卻仍未被界定為工業場所,只能以《職安條例》進行規管,但條例對違例情況的判罰相對較輕、阻嚇性低,僱主或因而罔顧僱員權益。她促請政府將舞台工程納入《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迫使業界更嚴謹對待舞台安全。
近日勞工處正循《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調查男團Mirror紅館演唱會事故,惟當局一般不會公開調查報告,公眾無從得知涉事成因。蕭倩文呼籲當局改變做法,一致公開所有工業意外調查報告,詳細披露意外原因,讓公眾有監察和知情權,使業界警惕,避免意外再次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