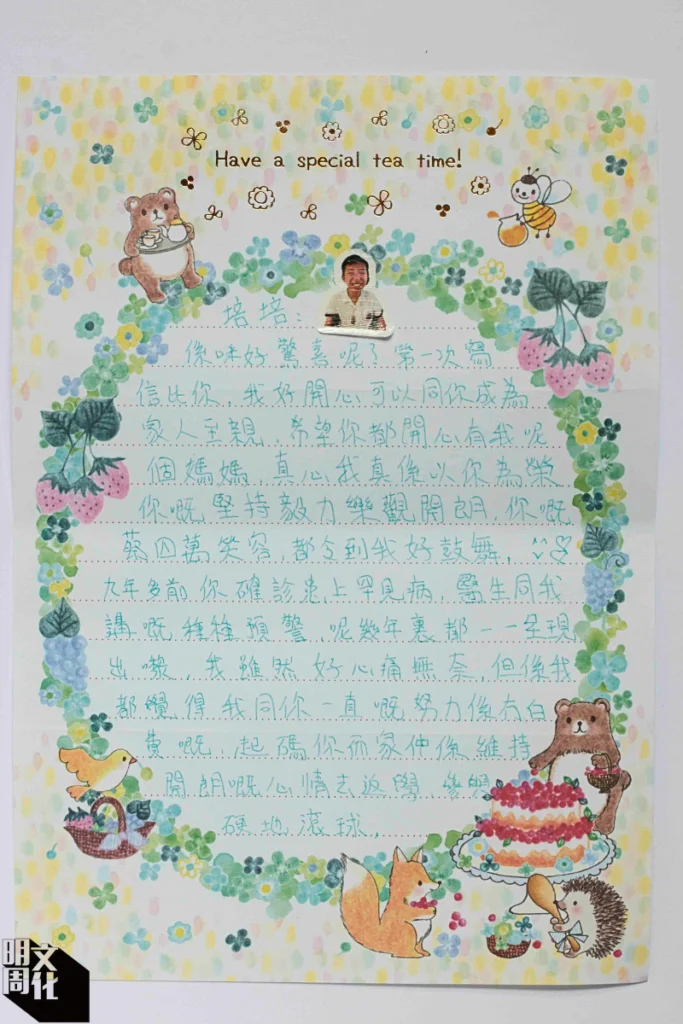嗶嗶嗶,七時正,今天梓培媽媽不是被骨刺刺痛醒來,而是被鬧鐘叫醒。她的手還是帶點麻痺感。她悄悄地起牀,走往洗手間,小心翼翼,生怕弄醒還在睡夢中的兒子、女兒和丈夫。匆匆梳洗,把握時間,先到廚房烚一隻蛋給自己,再打一隻蛋加入煉奶,在滾水上加個蒸架,蒸給兒子吃。她以前總是烚兩隻蛋的,不過近一年,梓培吞嚥愈發艱難,她換成了蒸蛋。
她又舀了一碗「長壽粥」,裏面有搗碎了的黃芪、綠豆和薏米。這碗「長壽粥」是梓培爸爸在網上發現的「秘方」,據說對於「補氣」尤有奇效。梓培媽媽說,梓培的病,總是讓他「無氣無力」,所以每天早上,這一碗「補氣粥」必不可少。
晨光乍現,轉眼,分針已走了半個圈。梓培媽媽趕緊回到睡房,先替梓培摘下夾指血氧儀和呼吸機,然後為兒子滴眼藥水、噴鼻、抹面。做完了,才輕輕拍醒兒子,開啟拍痰機和抽痰機。媽媽再將兒子平放在牀褥上,更換尿袋之後,還要翻側身體,處理兒子背後的褥瘡。「起牀儀式」完成,梓培媽媽幫兒子穿好衣服,準備下牀梳洗。
分針不由分說,又走了四分三個圈。他們得在半小時內吃完早餐,以便趕及乘搭復康巴士回校上課。
九時正,司機叔叔替梓培的電動輪椅扣好安全扣後,梓培媽媽將電動輪椅調整至接近平躺狀態,又細心地調整好頸枕的位置。
梓培讀中六,新學年獲准稍遲上學,因為梓培近來身體每況愈下,精神和力氣都大不如前。上學的話,一周也只能上三天,因為其餘時間,要休息和進行物理治療。梓培媽媽盯着眼前的電動輪椅,說如果這輛電動輪椅早點到,梓培的狀況可能不會那麼差……
可是,梓培媽媽心裏明白,現實中沒有這麼多「如果」。

⚡ 文章目錄
總是惦記着 陽光燦爛的日子
復康巴士走過東區走廊往西行,朝陽灑落在梓培的臉上。
梓培媽媽說,梓培以前十分精靈活潑。媽媽對孩子的回憶,總是那樣細緻。她說,梓培喜歡跆拳道,考至藍紅腰帶,又喜歡跳爵士舞,八歲時奪得全港公開獨舞大賽爵士舞團體組亞軍。在巴士上閉目養神的梓培,聽到這裏,忽然睜開了眼睛,眼珠滾滾地看着媽媽,嘁嘁叫了兩聲。梓培媽媽應答着說:「知道了,乖,閉上眼,多休息一會。」
「他試過很多東西,但現在只能看着他慢慢轉差。」梓培媽媽對記者說。
梓培一家四口本來與一般家庭無異。二十多年前,夫婦二人欣喜地迎接女兒出生,後來又有小兒子加入,一家甜甜蜜蜜,梓培媽媽最愛帶着兩姊弟到處拍照。不過在梓培升小一的時候,梓培媽媽已經察覺到一些異常。她發現梓培經常跌倒,在學校玩大風吹也站不穩,而且比同齡孩子瘦削,放心不下,尋求醫生意見。那時醫生說,梓培只是內八扁平足及營養不良,梓培媽媽心想,好吧,便買了矯形鞋給梓培穿,又多煮一些營養食物給梓培吃。一直看似如常,直到梓培升上小四,梓培身體出現強烈警號,每次躺在牀上,梓培就會感到頭暈,但頭部左右扭動一會,頭暈徵狀又會消失。梓培媽媽知道事不尋常,帶梓培到東區醫院急症室救醫。結果留院兩星期,經過各種化驗包括基因測試後,確認梓培患上一種名為「亞歷山大症」的罕見病,由基因病變引起,是一種惡化緩慢但致命的神經退行性疾病。

晴天霹靂 為期十年的「計時炸彈」
醫生對夫婦二人說,梓培會好像老人家般,身體機能慢慢退化,到最後,走不到路、看不見東西、認不了人。相關文獻指出,青年病發的話,很可能活不過十年。夫婦得悉噩耗,恍如晴天霹靂。他們心中默默計算,梓培那年只有九歲。
「我覺得他很殘忍,你跟我說十年,比我出街突然被東西砸死更慘。你給了我一個計時炸彈,但我知道醫生一定要這樣告訴我。」梓培媽媽說,她一直告訴自己,一定有例外的,所以她「不應該」相信這件事,只有這樣想,才能讓自己可以一直堅持走下去。
梓培媽媽神不守舍出了醫院,回家上網搜尋,才第一次大哭起來。她根本不知道,以後的日子可以怎樣過。她問上天:「為甚麼是我的兒子?為甚麼發生在我身上?」

針在兒身 痛在母身 他還一臉笑容
二◯一五年四月確診到今年年初,梓培媽媽一直有帶梓培做針灸。只要有多一點希望,她都不想放棄。最初,梓培媽媽找過一名針灸舌頭的醫師,因為聽說連明星想美容也找他針灸。每次落針數下,每針幾秒,做完,盛惠四百元。醫師還想他們每天去兩次,不過他們實在負擔不起。堅持了兩個多月,終於沒有辦法,改去別處繼續針灸。梓培父母覺得,針灸可以延緩兒子退化,至少可以減輕他頭痛和作嘔等不適症狀。
梓培經常作嘔,梓培會第一時間安撫媽媽,忙不迭對她說:「沒事沒事。」每次針灸,梓培媽媽不忍多看,只見梓培從頭到腳,被扎上六七十支針,偶爾問他痛不痛,他總是搖頭。為了感受兒子被針灸的感受,她讓醫師在她身上扎六七支針,她覺得很不舒服,然後她回頭看看兒子,不由得萬般滋味湧上心頭。梓培姓蔡,有一個花名,叫做「蔡四萬」。這時,「蔡四萬」再一次咧嘴而笑,露出他的招牌「四萬咁口」。
「他的堅持、忍耐,還有體諒我的感受,都很打動我。就算插了氧氣,他都笑,經常都笑,我很佩服他。」梓培媽媽說。
今年初,梓培情況轉差,梓培媽媽有感每次外出針灸,兒子疲態畢現,梓培媽媽終於決定暫停針灸。

梓培媽媽 也是靜琳媽媽

梓培媽媽,還有一個女兒,所以梓培媽媽,也是靜琳媽媽。
梓培確診的時候,家姐靜琳念中一。靜琳默默地目睹一切,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她看見父母四處奔波,像抓了狂一樣找救治方法。她很記得,有一次家族飯局,族中長輩因為唯一男丁梓培的病而爭執。她突然在內心升起一個問題:「為何有事的不是自己?」她心想,如果是她出事,因為她不是男丁,這次爭執就不會出現。
梓培確診的頭兩年,那時還有一份會計正職的梓培媽媽,一邊廂要上班,一邊廂要打點兒子的一切事務,身心俱疲,很多時候都顧不上大女靜琳。靜琳也不想父母操心,一放學後便趕回家裏待着,很少相約朋友出外吃飯逛街。靜琳曾經對媽媽說:「如果我學壞了,你怎麼辦?弟弟已經這樣了。」
有次兒子進了醫院數星期,夫婦二人忙得頭昏腦脹,壓根兒把女兒的事忘了。後來,梓培媽媽才醒覺,那段時間,女兒在學校也過得不愉快。女兒總是不想增加媽媽的心理負擔,學校的事,報喜不報憂,掩飾自己的不快情緒。後知後覺的母親知道女兒委屈,忍不住對着女兒哭了起來。「我一定是虧欠了她的……」
靜琳對記者說的是,是她自己選擇被miss out(遺漏掉)的。
梓培媽媽是一個「通天媽媽」,許多時候趁兒子入睡,跟女兒聊天,了解她的最新動向,她還慎防自己忘記女兒的上學時間表、實習及其他活動,每項細節都一一記在日程表裏。有些時候丈夫還未下班回家,那段少女心事時段,有時候又會變成母親的「少女心事時段」。兩母女還會一起通宵煲劇,有時在夜深人靜時,兩母女又會各自在自己被窩裏大哭一場。
靜琳修讀護理系,現在成了母親照顧弟弟的好幫手。一直與弟弟感情要好的靜琳笑説,照顧弟弟的情況,與她的課程幾乎可以同步進行,例如插尿喉、使用吊機等。這一刻,她成了主角,擔任一個照顧者的角色;其實,一家裏面,每一個人,從來,每一刻都是主角。


接納 需要時間和堅強
二◯一九年,梓培十四歲,他在五年前已確診,但一家人一直沒有認真討論過面對死亡這類話題。用了數年才能消化兒子病況的梓培媽媽說,其實她從沒親口對梓培說過他的情況,但相信梓培在家人出席不同場合的言談間已得知,也應上網尋找過相關資料。她和丈夫始終不懂得應如何開口對梓培說。
那時,梓培一家經主診醫生介紹,接觸了兒童紓緩治療。兒童紓緩服務基金的社工及護士上門,先跟梓培與梓培媽媽解釋何謂兒童紓緩治療,護士曾姑娘記得那時母子對此都不抗拒,她還特別記得當天「蔡四萬」的笑容。
報喜不報憂,可能卻是蔡氏一家的共同基因,不止梓培姊姊,還有梓培。曾姑娘多年來都想跟梓培談生命有限期這回事,畢竟這一天終究都會來臨,然而梓培很會轉移話題,連梓培媽媽也束手無策。
不過,因為兒童紓緩治療,梓培媽媽與社工及護士開設了一個名為「開心呻壓力」的通訊羣組,她學會在羣組內分享日常生活,有喜,也有憂。有一次兒子血氧含量急跌,梓培媽媽馬上在羣組留言,護士火速聯絡上主診醫生,醫生二話不說,寫紙收梓培入院。梓培媽媽十分慶幸,這次終於不用好像以前那樣,要在急症室等上六七個小時才能上病房,可說大大紓緩了她的緊張和焦慮。
不過,服務最幫助到梓培一家的,反而是她和丈夫的關係。
自從兒子確診,梓培爸爸比起妻子,更不能接受這個可怕事實。他可能相信,只要多做一點,就可以改變兒子病情。有一段時間,擔任電工的梓培爸爸通宵下班之後,還會不辭勞苦,立刻回家煮飯給兒子,再立刻帶飯盒到兒子學校,為求讓兒子多進食一點營養食物,放學後又馬不停蹄,陪伴兒子接受各項治療。梓培爸爸想兒子多鍛鍊身體,改善健康,但是,兒子情況仍然一步一步退化,梓培爸爸語氣不自覺變得嚴厲,覺得兒子不夠努力。愛之深,責之切,結果不僅影響父子關係,還影響到與梓培媽媽的關係。
兒童紓緩服務基金的社工花了不少時間與梓培家人溝通,梓培爸爸態度開始改變,慢慢學會接納梓培的各種狀況。因為這種接納,家庭關係大有改善。

病情惡化 再也沒法提筆

二◯一九年,梓培一家四口除了接觸到兒童紓緩治療,還一起飛到美國費城。那不是旅行,而是一次探求試藥之旅。他們知道,美國費城的兒童醫院舉行有關此病的會議。大費周章,只是想美國的教授看一下兒子的報告,看看能否獲批准進入首批試藥名單。可惜,梓培不能走路,不符合首批試藥名單的標準。
梓培爸爸和媽媽一直不輕言放棄,但歲月的磨練,讓他們懷抱希望之餘,同時學會擁抱現在的每一個時刻。曾姑娘說,美國之行,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捩點,因為他們可能認知到,前沿的研究亦未必可以幫助他們。
一直不想放下的,還有梓培。二◯二一年,曾姑娘陪伴梓培到骨科覆診,十六歲的梓培知道自己體內有一個鐵支架,問醫生這個支架是否可以拿出來。醫生有點訝異:「你為甚麼想拿出來?」梓培說,覺得自己會好起來,以後再也不需要那支架了。曾姑娘在一旁聽見,心裏難受,因為她知道,這幾乎沒有可能。
到了去年秋冬,梓培感染新冠肺炎,留院,出院,又再留院。梓培媽媽說,從前愛笑、愛說話的兒子,情況急轉直下,再也說不了話。他們一家害怕極了。兒子再也沒法提筆,他的DSE文憑試夢,恐怕要擱置。
梓培媽媽對他說,先休養一段時間,待明年文憑試再報名。可是,自此之後,兒子笑臉減少,她再也沒有再聽到兒子問,自己能否轉回常規學校上課。

如果要離別 最捨不得誰
今年年中,梓培的主診醫生終於還是要找機會,與他們一家商量「預設醫療指示」,因為梓培退化情況明顯,有機會隨時因為一次肺炎便引致生命危險。
那天,醫生與他們一家人見面,首先了解梓培父母和姊姊的想法。醫生當然還要知道梓培本人的想法,不過,當時梓培說話已不太清楚,梓培同意讓媽媽充當「翻譯」。
梓培對醫生說:「個天要我走,我都沒有辦法。」在旁的媽媽馬上哭成淚人。梓培繼續說:「我不想痛,而且想完完整整地離開。」醫生聽到,終於明白梓培之前為何一直堅持不想安裝胃造口。紓緩服務的姑娘又問梓培,如果真的那麼不幸要離開,他最不捨得誰,梓培說最不捨得姊姊。梓培媽媽聽了,更是哭得一發不可收拾。
醫生交帶說,把握好時間,看看梓培還有甚麼想做的就去做。梓培媽媽後來對記者說,她照顧得兒子這麼好,應該不會那麼快的。
他們安排了好些旅行,過去幾個月,去了大阪,去了北海道,又去了廣州。

又是一個有朝陽的早上
復康巴士走過東區走廊往西行,朝陽灑落在梓培的臉上。
回到學校,秋意盎然。梓培媽媽從復康巴士走下來,推着梓培進入校園。她適時拉下梓培的口罩,替他抹了抹口鼻。兒子露出了招牌的四萬笑容,她的眼睛也彎成了月亮。
這天是星期三。早上兩節課都是「科技與生活」,當梓培跟媽媽進入課室,一眾同學已經把紙杯蛋糕焗好。林老師給梓培安排了一項任務,負責看管同學量度淡奶油的分量,當分量足夠時,便要點頭通知同學。
梓培媽媽握着梓培的手,一下一下,把不同顏色的奶油擠在蛋糕上。
小息,放尿,中午餵飯,帶梓培到護士室小眠一會,又再上課。
下午二時,梓培媽媽終於可以自己一個人到圖書館休息。
她只能休息四十分鐘,但這已經是她整天為數不多的「me time(獨處時間)」。因為之後她回到家,趁兒子午睡,還要開始弄飯。


夜幕低垂,洗澡,讓梓培十時睡着。
第二天,一覺醒來,全屋寂靜。她重複一次日復一日的「梓培媽媽起牀儀式」。
這樣的日子,梓培媽媽過了七年。
她說,這是辛苦的,但她享受每天與梓培相處的時光,珍惜每一個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