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作家薯伯伯】少時遭遇車禍接受人生無常 旅遊足跡遍布歐、亞多國 屢陷險境仍看作「善經歷」 也能豁達應對社會沉鬱 薯伯伯:面對無常才更加珍惜當下


薯伯伯(Pazu)有多個身分,與他沾上邊的事物,包括旅遊、西藏、網絡安全、時政評論,甚至兒歌。
他曾在拉薩經營咖啡館,於喜馬拉雅山麓居住多年,亦是足跡遍布歐、亞多國的旅遊作家。他常在網上分享網絡安全資訊,評論時政話題;更曾於九十年代創辦著名的「Pazu兒歌網」,收集大量香港經典兒歌。
遊歷四方,人生經歷豐富的他,自有一套穩定的人生哲學:無論順境、逆境,皆視之為生活;逆境之中,也能尋覓對自己有意義的經歷。這聽上去好像是萬能的心靈雞湯,但每隻字都是從血肉經歷中淬煉而來。無論面對旅途危機、人生險境,還是當下困局,都以逆風翱翔的心態應對。
⚡ 文章目錄
生活就是旅行 疫情困身不困心
很多人視旅行為一場日常的出走,逃離平日的壓力、繁忙的工作、千篇一律的生活,在陌生國度尋求新奇和刺激。但對於遊歷四方、足跡幾乎踏遍全世界的薯伯伯(Pazu)而言,旅遊與生活的界線並不分明。
訪問當天,他身穿粉紅T恤、黑色長褲,背着一個大背囊前來,這身打扮跟他今年出發前往尼泊爾長途旅行的裝束無異。不必特意添置新裝,也無需搜羅打卡之地、繁複計劃,隨時可以啟程,他多年來的遠遊方式也是如此。「旅行對我來說很重要,但不是說一定要做到旅遊這件事,而是生活好像跟旅遊沒有甚麼分別。」薯伯伯說。

於他而言,旅行是轉換地方享受未知,在異地取得不同經驗,但其本質跟生活同樣,都是為了追求心靈的遊歷,讓路上所遇的一切人和事豐富感官,擴闊視野。也正因如此,疫情三年困身本地,很多朋友以為薯伯伯會百般難受,但他仍能處之泰然。
無法外遊的那幾年,他報讀一直以來想研修的港大佛學碩士課程。閒時,他喜歡發掘本地事物,也尤其愛逛獨立書店,遊走在書架之間。最教他驚喜的是隨機撞上聞所未聞的書,無需周遊列國也能跳出舒適圈。「這樣的想法有一個好處,你沒有那麼容易將世界變得太大,也沒那麼容易將一個狹小的空間看得太細。」薯伯伯說。


上山下海多年 惜身不冒險
提到薯伯伯,很多人會想起他在西藏拉薩經營十二載的「風轉咖啡館」,這幾乎成為所有入藏港人的必去之地。除在高海拔的拉薩居住多年,他也曾遊歷阿富汗、突尼西亞、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亞、伊朗、朝鮮等等,大多是讓旁人聽了也直呼危險的名字。
薯伯伯卻搖頭,他很少「覺得哪裏危險」,因為「危險」印象,可能帶着僅以數則新聞定論世界的偏見,當中混雜了很多與實際不符的資訊和認知。新書《逍遙行稿:逆風翱翔》出版後,他跟「旅行公民」創辦人、大學講師王劍凡舉辦講座對談,「王劍凡提過,二〇一九年的時候,有位外國朋友發訊息跟他說,香港很危險。而這個朋友是阿富汗人。」薯伯伯笑說。
他又舉例,他曾於九一一事件後一年多遊歷阿富汗,很多人以為正值阿富汗戰爭,阿國全境都是炮火連天,但他打探過後得知,當年交戰激烈的地區集中於南部坎大哈,而他前往的首都喀布爾、中部旅遊城市巴米揚則安全。
很多旅人愛冒險,喜歡挑戰人生極限,但薯伯伯多年來上山下海,仍然很是「錫身」。他怕蚊,背包永遠放着一支蚊怕水;討厭嘈雜,對聲音敏感的他,出街隨身攜帶降噪耳機;那些沒有街燈、一片漆黑的道路,他絕對不會走。雖然曾在冰天雪地淋凍水浴,或是斷食十天,但這些均是他查閱眾多研究資料、認為對自己身體有好處才去做的事。「我好錫自己,不是用挑戰的形式去看自己做的事情。」薯伯伯說。



身陷險境 轉化為善經歷
不過,即使不是故意以身犯險,但到了陌生的地方,總有意外發生時。二〇〇二年,薯伯伯到巴基斯坦北部獨遊,徒步路上失足滾下十米山崖,迎面撞上一塊大石,眼鏡玻璃碎掉,全臉是血。
他幾經掙扎後爬上山徑,沿路離開途中,遇到開電單車經過的當地村民,問他是否需要幫助。當時薯伯伯仍想堅持原本的徒步計劃,步行一日一夜抵達目的地城市Gilgit,便信口胡謅說自己沒有錢,婉拒對方。「雖然聽上去不合理,但我當時就是想繼續走下去。我也不太明白年輕時為何會有這種想法。」薯伯伯笑說。

然而,就算聽到他沒有錢,熱心的村民仍然堅持載他走,還主動提議給錢他用。到醫院檢查後,薯伯伯因腳趾骨折需要打石膏,他選擇到另一城鎮Karimabad療養,沒想到重遇幾名此前在旅館認識的日本旅客。他們經常探望薯伯伯,還一起買食材、煮東西吃,彼此交情至今依然。
薯伯伯最愛的動畫是《天空之城》,百看不厭,他的英文名Pazu更取自動畫男主角之名。養傷時,他驚喜地發現巴國小孩穿著的傳統服裝shalwar kameez,跟動畫男女主角的某身打扮類似,都是長版上衣、寬鬆燈籠褲。雖然宮崎駿從未承認這是靈感來源,但薯伯伯彷彿解開隱藏彩蛋。
雖然當年的愉快外遊驚變意外受傷,但薯伯伯想起的更多是這些心頭一暖的時刻。於他而言,人生無論順逆,皆視之為生活,逆境也能看成「善經歷」。他在新書中寫道:「所謂『善』,非謂過程無瑕,是於苦中尋其意義,得一即善。」「善經歷不代表它本質是好的,而是過了很多年,當我回想這件事的時候,仍然發自內心地覺得它們是有意義的。」薯伯伯說。

少時遭遇嚴重車禍 接受死亡與無常
薯伯伯如此豁達,不是生性樂天,不愁不憂,反而是因為他曾走出過更大的苦難。初中時,他遭遇嚴重車禍,雙腳折斷,頭骨爆裂,與死亡擦身而過。臥床一個多月,身體稍微恢復又迎來另一沉重打擊,當時與他同行的中學摯友被捲入車底,重傷喪生。
那是他人生的至暗時刻,亦產生了很多悲觀負面想法。他仍記得第一次在佛學書中看見「思惟死亡無常」時,那種強烈的切身感。「思惟死亡無常」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修行法門,意為接受世事無常,對死亡做好隨時的準備。「我不需要費力,就能理解這件事,因為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了。」薯伯伯說。
「小時候覺得這段經歷不好,很難過,也經常在想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事?但當慢慢長大的時候,開始看見自己的人生軌跡跟其他人有些不同,就會在想,如果我的人生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我今天可能未必用這種心態對待事物。」薯伯伯說。
或因少時經歷過無常,薯伯伯也一早放下對身外物的執着。身邊不少同儕畢業後高薪厚祿,早早置業,過着穩定的生活,但薯伯伯二〇〇〇年於浸會大學生物系畢業後,便喜歡周圍旅遊,除在風轉咖啡館當店長外,未試過長時間從事全職工作,他至今也沒有買樓。雖然他喜歡研究科技設備,但生活仍然樸素簡單,穿着打扮來來去去也是那幾套衣服,鮮少受外物束縛。
「要經歷了很多年之後,再回望,才慢慢有這種沉澱。而這個過程很漫長,可能有二十年,可能我現在還一直經歷這個過程。」薯伯伯說,將逆境轉變為「善經歷」的過程不僅漫長微妙,也需發自本心。如果強求所有人在苦難中仍然保持樂觀積極,實則冷血無情,忽略了對方的痛苦。

放下過往執着 不改價值與公義堅持
無論是旅行險境,還是人生低潮,薯伯伯均以豁達之心應對,他看待當下困局的態度也如是。比起過去,現今多了很多限制;談起未來,社會一直瀰漫着一種無力感。在社會沉鬱之中,薯伯伯如何找到「善經歷」呢?
「我也覺得距離從前的目標很遠很遠,但是明白了這一點之後,我也會更加清楚要怎樣對待現在。正正就是因為你不會再追求永久長存,面對無常時,反而會更加珍惜當下。」薯伯伯說。這幾年來,他堅持寫書、買書,幫襯獨立書店和小店;他繼續訂閱網媒和Patreon,支持獨立不受干預的團體和寫作人;他仍然在網上活躍分享網絡安全資訊,評論時政話題,保持求真態度,用不同的方式支持仍然留在香港的人。
「你做這些事情有甚麼用呢?又能改變甚麼呢?」然而,無力的說話仍不絕於耳。「有咩用?你現在不做就更加沒用。譬如我買了一本書,書店、出版社和作者都有得益。我用一杯咖啡的價錢,就可以支持一位記者去西九排隊聽審。有很多事情仍然可以做到。」薯伯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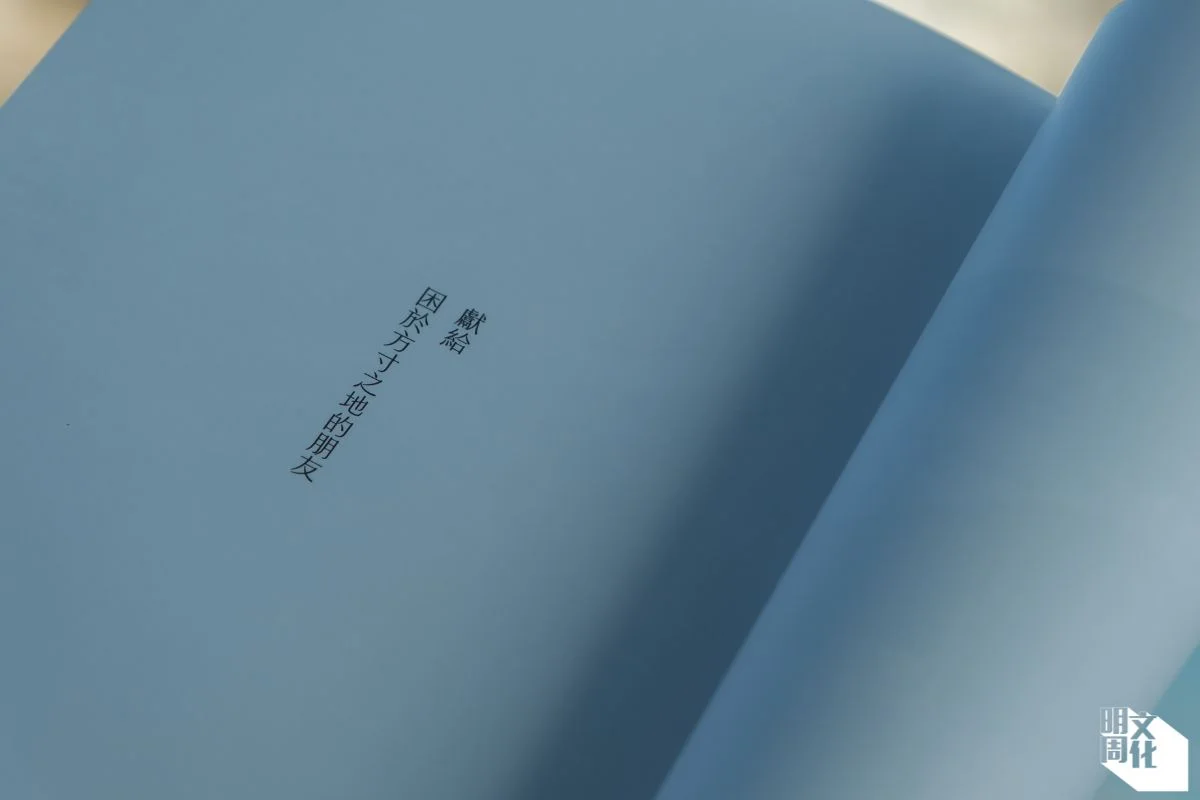
他將新書「獻給困於方寸之地的朋友」。「方寸之地,表面解作『很小的地方』,在古文裏也比喻人的內心。」薯伯伯解釋。各人現今面對不同的限制,有人困於斗室,有人礙於傷患,有人或因沒有足夠旅費、工作太忙碌而難以開啟新旅程。但他認為,限制有客觀,也有主觀。受限於狹小空間的人,可能從書海裏日益精進,心境反而比他更開闊;而那些行動自由的人,也可能找到百般理由限制自己。他寄望眾人在困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出路,逆風翱翔。新書出版一個多月,他連辦九場分享會,也想藉着這個機會跟更多人見面、打氣。
不過十一月十五日,他在留下書舍的講座開始前,遭到至少五名戴口罩人士闖入騷擾,對方還手持標語、大聲攻擊他「荼毒年青人」。活動完結後,薯伯伯立即到警署報案,即使警員告訴他提告耗時費錢,他亦堅持提起民事訴訟:「我想讓全世界看見,這種荒謬的事情怎麼可以在香港發生?我的講座只是分享旅遊和人生經歷,以此跟大家打氣。如果連這麼溫和的分享都不被允許的話,那麼在香港還可以做什麼?」
「無論付出多少時間、精力、金錢,我都已經有心理準備。因為我很不接受這件事,我很不願意看見不公平的事情發生。或許有人覺得我對這件事很執着,但這不是執不執着的問題,而一個最基本的公義。」薯伯伯說。比別人更能放下執着的薯伯伯,並非妥協或歸於虛無,他心中自有一套原則與堅持。他相信,即使行動微小,也有微小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