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兩點,工廈暗室裏,節拍無間斷融入煙霧的矇矓迷離。正想打開大門逃離一會,迎面碰上約好Charlie (DJ Charlieowo),說她對即將進行的訪問感到緊張,想跟我談談大概方向。當時的我,認真談論工作的腦容量有限;但記得這個二十五歲女生的話,平和地穿透鐵門未能隔絕的煙霧與重拍:「你問我為甚麼想當DJ,其實是因為我想帶給人快樂。」
電子音樂圈的dress code大致分成兩類:全黑的柏林工業Techno風,及迷幻繽紛的psycedelic嬉皮風。Charlie屬於後者。她蓄及肩短髮,喜歡把紮染色彩、炫目圖案穿上身。「我有段時間是很沉迷看hippies的東西。」Charlie說。她大學時曾選修美國研究,對一九六七年,那個人人髮上插着花朵,結合音樂、反越戰、和平主義與政治行動的「愛之夏」(Summer of Love)非常深刻。
錯過了那個年代,Charlie發現她在派對中,找到同樣屬於那個烏托邦的愛與連結。「人們常說rave就是第二次的『愛之夏』,我覺得它好像真的可以relive那種hippies的community,或是那種精神。」她說。

⚡ 文章目錄
愈壓抑愈學會放飛
Charlie的DJ簡介中,她說她相信“the more repressed the harder you stomp”(愈受壓抑,腳踏得愈用力)。她自己也是從現實的擠壓下,學習找尋自由空氣。她出身自傳統女校,家裏管得也嚴,「十點幾還沒回家,媽媽就打來問你去哪。」可是從小到大,她就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及愛好等,也不是父母所能理解或認同的。他們只希望女兒長大後能老實長進,低頭賺錢養家。
「我是不會主動挑戰家人的底線,可能我會自己設定那條線給自己,咁做佢應該會很嬲或者很煩,我會自己框住自己。」Charlie苦笑說,長大後認識一些敢於反叛的人,愈覺得自己奴性太重。所以,她入住大學宿舍後,簡直「放飛自我」;即使在家裏,她還是慣了窩藏自己,像一頭冬天蜷眠的獺。

也不是未試過反叛。大學畢業後,未學音樂的她曾短暫當上咖啡師。家人們的反應理所當然是「我供你讀大學你竟然去沖咖啡」。但喜歡煮食的她想,或許食物也可是傳遞能量的媒介,也許她也能為人帶來快樂。有一次,她病倒了,迷糊地打開電腦找MV看,看到了Queen在Live Aid籌款音樂會的Live,「那一刻我很感受到他的音樂力量,隔了這麼多年,我隔着個mon都可以感覺注入了全身的正能量。那一刻我就覺得,原來音樂或者做一個artist的力量可以這麼大」。漸漸地,她的跑道就從沖調咖啡,變成mix電子音樂。她跟許多決定DIY製作音樂的電子音樂人一樣,她選擇電子音樂,是因為所須技術門檻較低,不需要音樂知識背景。
從個人到集體的逃逸

Charlie認為音樂的魔力,在於創造一個彷彿從現實脫離的異質時空,「比如,當你在地鐵很多人,但是你聽到一首好『中』的歌,你都可以離開了那個空間。那個就是可能令你獲得的幾分鐘的自由」。
Charlie起先只在跟朋友租下的Airbnb搞的聚會中打碟。音樂體驗,自此從戴上耳筒的個人逃逸,變成集體共享的當下。一室的人,在她的選播的音樂下,整個房間裏的動作變得統一,好像都在聽着她的指揮。她認為DJ帶給人快樂有兩種,一是天然的身體愉悅,「你看BB聽到歌會好自然地chok吓chok吓,我覺得跟隨音樂去舞動,是種與生俱來的快樂。」二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在舞池裏,即使你跟身邊的人互不認識,但因為喜歡DJ放出來的音樂,跳得特別用力的時候,是有一種無形的connection在裏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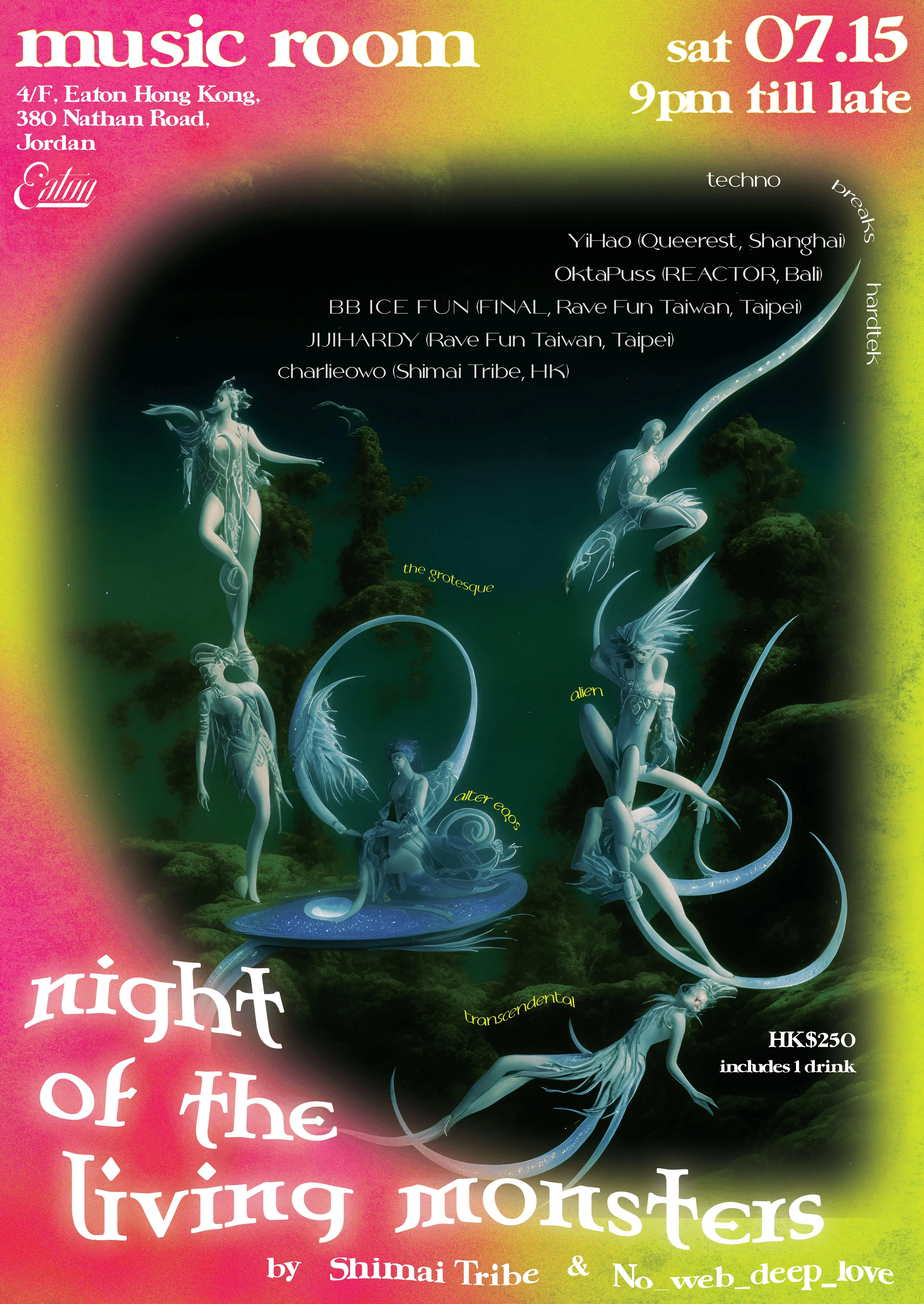
Charlie在家裏習慣收起自己,在外面也比較內斂慢熱。但在一場又一場的地下派對,她被充滿愛與溫度的氣氛打動,「很多人都很主動地去同你傾偈,或者關心你。而我覺得都給那個connection我,或者會令到我慢慢學習到,其實我不需要咁驚去踏出第一步。」因此,比起大型派對,她更珍惜圈子緊密的地下派對:「因為party其實就是人和音樂,有人聚集在一起、再有音樂其實就是一個party。你所喜歡的音樂,好多地方都可以提供;但是人是要『夾』的,要做到熟悉信任尊重,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電子舞曲世界,從七十年代Disco萌芽起,就鼓吹平等與多元。不過,有時隨着圈子擴大,也有新來者未必明白這種地下精神。Charlie指有些人去派對明顯只為了放縱,以消費心態參與,等搞手幫他「執手尾」。她也發現,當有人穿得誇張一點、或男生化妝打扮出席派對時,有時會受側目。她希望更多人能包容以不同模樣展示自我的人。「其實這個都是rave的根本吧,始終這個文化的根本是由一班LGBT黑人建立,或者就係大家喺呢個地方搵到一個地方可以好好地express自己,大家係接受自己嘅模樣,我係想去到呢一刻係可以把這個精神延續落去。」
回望才看懂一個時代
才打碟兩年,Charlie已是本地各大電子音樂派對的常客,更被邀請到台灣的音樂節打碟。她謙虛的說,承蒙前輩及朋友們關照及支持。不過,她近來搬回老家住,面臨「宵禁」政策,也惟有減少外出DJ。但這不等如她不能繼續在音樂中,跟其他隨同一節拍舞動的個體,尋找自由。
Charlie認為派對雖是一種享樂與釋放,但它不可恥。「其實很多活躍香港地下文化的人,都是曾經活躍政治的。當大環境不再容許時,他們轉去搞音樂、藝術,用另一種形式把人聚在一起。」而且當人解放了,自由了,誰知道它有一天會不會變成一個浪潮。一個個頭上插鮮花的嬉皮,積聚成眾,歌頌愛與和平,隔了一個時空回望,才發現那時的斑瀾幻彩已成時代的底色。

最近她跟朋友討論嬉皮文化,談到當時的嬉皮士也未必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只是在做他們認為正確的事。
「你不會知幾十年後,人們望回這個時代,發現原來這是一個很強的movement,你改變了好多好多。我覺得到現在這一刻,我們也是,不會知自己這一刻做甚麼,會做成甚麼改變。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理想,覺得你想做或者應該做的就去做,可能不知道那一刻改變就會發生,就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