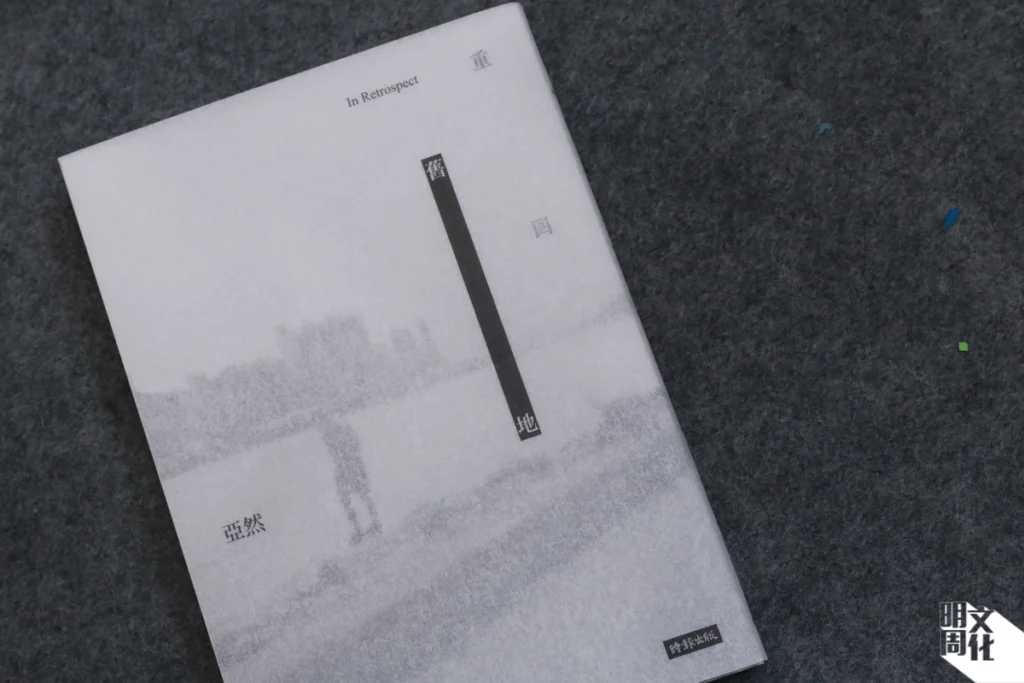台北書展有新生代香港作家的身影。移台生活數年的沐羽去年在台出版首部小說《煙街》,奪下今屆書展小說組首獎。亞然今年交出香港政治文化評論的「三部曲」最後一部《重回舊地》,同樣由台灣出版,記下讀書旅程歸來的思緒。兩位九十後寫作人以不同文體,無獨有偶都是寫離開後無法回頭、卡在中間的狀態。為何這一代香港青年作家都回不去?
⚡ 文章目錄
《煙街》與《重回舊地》:能否回去 能寫不能寫
二人是同代人,年歲僅相差一年,讀書研究,曾留學台灣,在媒體寫稿,也在台出版著作,過去卻從沒接觸交流,直至今屆書展。沐羽是今屆書展小說組首獎得主之一,除了得獎分享會,也有其餘對談講座,其中一位是亞然。那是亞然特地匆匆從香港來台灣數天,出席書展的《重回舊地》新書座談。他們表示,是講座前一周才交換社交媒體,笑言這是網友見面會。

「我們兩本書,都是寫離開了香港,回去但卡在中間的狀態。唔太返到轉頭,又唔係好去到新嘅地方。」沐羽如此概括他的小說《煙街》和亞然的專欄結集《重回舊地》的相似點。
亞然的首作《孤獨課》是外國留學遊歷,接着的《醒來的世界》也是寫於旅居德國時,對政治及世界的反思,他形容主調還是開心。惟新作《重回舊地》,都是二○二○年後,一直在香港寫成,「整個世界是一百八十度轉變過來。而且也是我個人成長的一個過程。」他說,當改變愈來愈快,就真的是回不去的那種感覺。
而逃逸是沐羽前年寫《煙街》時思考的狀態。那是關於香港與台灣的小說,筆下不少都是流亡台灣的港人。他自知其特色是中間的人,來台多年,對香港陌生,「但成為台灣人是沒可能的。移民是永遠的過程,不會真正成為到當地人。」
各自寫作的地方、距離,文體完全不同,但同樣感覺回不去。
「你有沒有考慮能否回去(香港)的問題?」亞然問沐羽,因為他認為這一點會影響寫作,「基本上寫作不會踩着剎車掣地行走?」沐羽說,去年經常被問起同一條問題,「但沒有人問我想不想回去。我不太想回去。因為整件事都不一樣了。與其回去,見到地方完全不同,不如保留那些在我的記憶裏。」這也是他選擇寫小說而非散文的原因。「因為我想的是當下的情況。我和這麼多香港人在台灣都卡在中間,這對我來說是比較切身的議題。如果我和那些我書寫的對象同在一起時,我關注的是那些回不去的人,而不是我能否回去。」
這點卻是近幾年對留港寫作的亞然影響最大,或如他所問道,踩着剎車掣般的下筆。「要思考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和所有威權政治一樣,都是自己估計。如果有張清單說有什麼能寫不能寫,當然好容易,但並沒有。」他研究專業是港、台兩地政治,多次來台觀察選舉,「特別是寫政治,如果沒有踩界的,便不用寫啦。或多或少都危險,但盡量做,盡量小心。我是很小心的人,也不是什麼厲害主張、激進的,不在政治光譜的任何一邊。我沒有刻意改變自己,不是違背了什麼,只不過所有事都要很小心。」
對於類似在港寫作者的處境,身居異地的沐羽坦言不曾自覺置身事外,亦無高低之分。「我都認識不同留在香港的寫作者,像韓麗珠每天都出文,她的寫作習慣沒有因為政治影響而忽然轉變。又會見到周冠威、任俠、陳梓桓,都在做原本他們想做的事情。當然是佩服他們的勇氣。我不會說是置身事外,因為我本來就寫一些和他們很不同的東西,在小說、美學上的bonding是非常低。如果問會不會置身事外,就已假設我是局外人,去『看他們』。」
小說與評論散文 通過故事或評論來說話
談到文學寫法、美學的觀念,也是二人的不同。沐羽成為新進小說作家,兼寫散文。而亞然無論在講座或訪問中,卻多番表示自己寫的評論文章不會被歸入文學。
亞然自大學時代始於報章撰寫評論,同期修讀政治的同學張秀賢刊在觀點版,自己則屬副刊,版面有別,不是那種很即時、觀點鮮明的文章,「由小到大寫作都會找一本書來談,不過是借他人的口,去講自己想講的。我是通過評論或書評的形式去講,而沐羽是通過故事。」譬如亞然讀錢理群談魯迅,記下的是強者如魯迅置身壞時代只能抄書避禍的命運。
他坦言自己的文章未必很耐讀,倒會羨慕可以寫得出小說的人,「但在這個社會環境下,那狀態很尷尬,又寫又驚多人睇,有這種猶豫。沒人看,自己繼續做。或者到了時候,會有人認為關仲然(亞然)這個人做了些東西。」
在創作小說之前,沐羽都是寫散文的,書評也好,理論或現象評論也好,都與亞然相似。「亞然說自己不是文學這回事,有點被傳統、由純文學把持的系統影響。因為最基本你創作了一本書,無論什麼都是文學。」
以前沐羽接觸過一類主流講法,指寫作是為了自己,但他不認同,「寫作基於語言,是有溝通性。那時我開始想,什麼人會喜歡我的文章。這不會被區域限制,我最後揀的是純文學讀者,或者比較modern的文學讀者。可能因此我才會得獎(書展大獎)。他們喜歡我作品的原因,是它在講一個故事,而剛好是寫香港。」
他指,報紙,小說或散文,時效性都有不同展現。「我和亞然有個地方好似,都是寫評論起家的。我寫評論,因為無論《明報》或文學媒體,評論是穩定的收入。這直接影響我的散文。亞然說,好多書通過他來說話。我最近得知自己有作品被選入今年《九歌》的散文選,那篇是我評論兩本書,而兩本書是通過了我的工作經歷見聞去包裝。我們的common ground是一樣,讀完一本書,消化了它。」
在亞然看來,《煙街》作為小說,直接而微觀,「沐羽寫的對話都很直接,寫一個人發生了什麼事,其生活最微小的層面。說unit of analysis是個人的話,他真的在寫一個人。我的評論不會微小到這樣,最多我見到什麼,篇幅也不會有很大的聚焦。」他表示,這是性質和處理方式不一樣,「我都想講好細微的東西。譬如講民主化,不想每次都是談最大最出眾那個,可以講其他小人物如何自處,或者都是我想知道的,作為一個普通人,在這個環境下如何自處。」
去年沐羽從新竹遷居台北,看到很多港、台兩地人的磨擦。過往他曾在小說以在台港人成立「香港村」的討論諷刺港人天性,如今他卻看到香港人的確互相扶持,「是很新型的香港社羣,很值得探討的。但這是現在進行式,我未消化到,一來是太忙了沒時間,二來我的藝術或思考未深入到去。」
憤世嫉俗 寫作的趣味
自言喜歡「睇人打交」的沐羽,在亞然的三部曲中,最喜歡的是第二部《醒來的世界》,讀得出字裏行間的憤怒,他說,有點獠牙,有嘢想鬧,「用理論去X一個世界」。
憤世嫉俗、事事看不過眼,可能是他們的共同主題,但如何表達憤怒,也在不同位置。
亞然在《重回舊地》出版前,重寫過書稿,因為在記錄城市隕落時,流露太多情緒。沐羽好奇的是,究竟寫散文能如何克制自己的感情?「那時就是沒有(克制)。」亞然續說:「所以當時我的取態是講其他。當然都是政治,明知和香港有關係,但我完全不講香港。我有點怕直接面對,甚至乎現在那麼多紀錄片,我好怕去看,可能是不太懂得面對。」
是否創傷?沐羽問。亞然表示,不算,只是個人本身比較有距離,站的位置「又後又斜」。沐羽則說自己也差不多,「不過我是在直後面X佢。不會是指桑罵槐。通常我應用理論,都是串連真實事件去講。我這本書(《煙街》)同樣是連繫故事去講理論。」對沐羽來說,最喜歡《醒來的世界》的趣味,正是因為書中有一種拿捏理論和對世界看法的游刃有餘。
「第三本有點太沉穩,沒有一種危險、向前行。第二本是想捉住一些東西來挖,是真的有東西想鬧才寫㗎嘛!」聽到沐羽如此評析,亞然也承認此中的轉變:「會愈來愈小心呀,然後驚好多事。這是絕對真實的事。」欲語還休之難,是環境,也是個人性格使然。亞然說,很多事都看不過眼,但不會刻意去講,並非偽善,而是保持距離,乜都吞落肚。他都知道,這點在寫作上有矛盾。「由第二本到現在,這幾年的狀態都好模糊,分不出哪一年,工作、疫情,好混沌。但我寫這三本書,應該是第三本最成熟,篇幅上寫長些、連貫些,闡述更多。」

回顧近年的寫作出版,「香港創作」成為一個議題,隨之而來的是出版自由、禁書、下架的字眼等等。對他們來說,有什麼不想聽到的說話?
沐羽指,自己得獎後,有朋友說恭喜,還加上一句「為港爭光」。「我不是為了香港寫這本書。我是挑戰自己,作為小說初學者,練習技藝。當中有香港,是我關注的議題。為何無端端代表香港?」他的發問或對答,不時都強調寫作手法、美學、文學理論,沐羽追求創作上的技藝超越,是對寫作的純粹想法,「這一點我還是覺得自己很天真的。」
亞然則覺得,對於被形容「好勇」感到奇怪。「首先知道自己一點也不勇,是否在諷刺我?而且由始至終我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認同這情況在今時今日無可避免,「他朝有日,很多現時在做的事,都未必做得到。」
這兩位寫作人無論性格或創作狀態,着實南轅北轍。但依然繼續寫作,可能某個相似點,除了憤世嫉俗,也是他們仍找到一點樂趣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