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出版人顏擇雅是個認真讀書的人,在出版上獨具慧眼,一人成立雅言文化,發行《世界是平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和《西方憑什麼》等暢銷書,屢屢激起華文文化中不同議題的討論。
對於張愛玲,她一樣讀得獨特,其為作品寫過的評論文章大都不是張愛玲廣受歡迎的早期作品,而是後來常被批評、被認為寫得過於冗長而繁瑣的晚期作品。
其他人都覺得文學價值不重的作品,她用心去讀,旁人覺得不值一提的,她更是一頭栽進去研究,最後總讓她讀出了書中曖曖的光,看出了別人看不到的故事。
顏擇雅說,自己年輕時很早便到美國唸書,看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流言》和《短篇小說集》都是在十五歲之前。那段時間台灣正值戒嚴,中國名家如魯迅、沈從文、老舍與錢鍾書的作品都被列為官方禁書,只有張愛玲是那時台灣唯一能讀到的民國時期小說家,然而對於一個才十幾歲的青年人而言,那正是囫圇吞棗的閱讀期,她對這個上海女作家當時亦談不上喜歡不喜歡。
到她真正再去讀張愛玲時,已是二〇〇九年。
那年《小團圓》出版,文學界鬧哄哄的都在湊熱鬧,結果不少人看完《小團圓》後都說這部作品寫不好。她卻覺得明明寫得好,很想幫它說幾句話,就在自己的廣播時段解釋《小團圓》如何運用草蛇灰線、手揮目送、背面傅粉這些叙事技巧。
本以為廣播過後就完了心事,沒想到有聽眾將她的廣播內容打成逐字稿。稿中有些說法她後來想作出修正和補充,乾脆痛下決心認真把《小團圓》評析寫出來。
「但寫文章不比廣播,每一句都講究,所以我就把她其他作品也拿來看。這樣又看出許多東西,所以陸續又寫了〈相見歡〉、〈同學少年都不賤〉和〈浮花浪蕊〉的分析。」顏擇雅說道。
她眼中的張愛玲,去美國後就不思念中國了,卻在晚年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去保存她最珍視的中國小說命脈。
《紅樓夢》未完於她是人生一大憾事,因此她花十年時間去探究曹雪芹的改寫過程。
《海上花》乏人問津讓她憤憤不平,要譯成英語與國語其實也不需要一位張愛玲,但她還是投入了。
《小團圓》、〈相見歡〉等作品都是她親手實驗,想探究失傳的叙事技巧可否用來講現代的故事。
顏擇雅:「每解開一篇作品的謎,我都對張愛玲的強大自我感到欽佩。一位作家能不在意被廣大粉絲不解,連書評人批評她退步也不解釋,是需要強大自我的。」
她就在那堆乏人問津的張愛玲晚期作品中,找繩索線,對照書信與訪談,解讀出一道道張愛玲作品不被看見的感思與謎團。

問:明周
答:顏擇雅
問:赴美後,你認為張愛玲有沒有所謂的離散創傷?
答:張愛玲一生有過一些創傷。被父親痛打、囚禁,她抱病逃家,這經歷絕對是創傷,但是,她絕對沒什麼「離散創傷」。證據是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二日她寫給鄺文美、宋淇的信:「中國人內大概是我最不思鄉。要能旅行也要到沒去過的地方,這話也跟你們說過不止一次。」
而且,她不只自己不思鄉,還奇怪別人思鄉。
殷允芃就記錄下她在一九六八年說過的話:「我很驚奇,台灣描寫留美的學生,總覺得美國生活苦,或許他們是受家庭保護慣了的。我很早就沒了家庭,孤獨慣了,在哪兒都覺得一樣。而且在外國,更有一種孤獨的藉口。」言下之意,她不是來美國才變孤獨,她是來美國才獲得合理藉口,不必老是再費心解釋她幹嗎只想自己過日子。
問:在她的作品中,哪一篇最能傳達出她的不思鄉?
答:一九八〇年的散文〈談吃與畫餅充飢〉寫的就是自己為何「最不思鄉」,不過不是明寫,是夾縫文章。
文章開頭挑出周作人,把他寫吃的文章損了一下:「周作人寫散文喜歡談吃,為自己辯護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但是男女之事到處都是一樣,沒什麼可說的,而各地的吃食不同。這話也有理,不過他寫來寫去都是他故鄉紹興的幾樣最節儉清淡的菜,除了當地出筍,似乎也沒什麼特色。炒冷飯的次數多了,未免使人感到厭倦。」言下之意,就是你思鄉,我好煩。
不只是針對周作人,張愛玲其實是對所有中國人在味覺上對故鄉的執念都有意見:「我們中國人享慣口福,除了本土都是中國人的災區,赤地千里。」以她看來,盛筵難再還要寫它多好,就是標題所謂的「畫餅充飢」,是不懂得把握當下。
但是,童年是每個人的口味形成期,寫飲食怎能不思鄉呢?
首先,張愛玲家庭已遷入城市三代,雖然在鄉下依然有田產,飲食上卻已斷連繫。這是為何她姑姑還會思念家鄉味「黏黏轉」,張愛玲卻完全不清楚是什麼。然後,她成長的城市都相當國際化,因此她追悔該吃而沒吃到的是俄羅斯包子,尋訪未得而「皇皇如喪家之犬」的是英國司康(scone),兩種食物都跟中國無關。
許多人懷念的童年飲食皆跟父母有關。張愛玲也承認,在多倫多曾經「一時懷舊起來」買了香腸卷,是為了父親的記憶。但是,發現味道不對時,就嫌它「哪是我偶而吃我父親一隻的香腸卷」。這是張愛玲特有的點到為止,有點到父親對她的吝嗇。
而跟母親有關的回憶是最好笑的一段:「我把臉埋在飯碗裏扒飯,得意得飄飄欲仙,是有生以來最大的光榮。」這麼美好,尋常人一定思念那道菜的。張愛玲卻不可能,因為那是有怪味道的雞湯。
難道她想不出中國菜有什麼好吃的?有的,她承認西湖螃蟹麵味道很好。結果她把這碗麵連結到中共上台後她感受到的恐懼。與螃蟹麵對照的,是她在船上吃到的炒河粉。這段經驗有寫進〈浮花浪蕊〉。為何強調連吃十天也不厭?弦外之音就是慶幸離開中國。
至於與美國有關的段落,張愛玲寫的都是她在這個移民社會如何找樂趣。她去光顧丹麥人開的西點店、羅馬尼亞超市,買過波蘭小香腸、以色列苦巧克力,煮過意大利餃,還嘗過埃及辣煨黃豆。怎會思鄉?她忙着藉由買菜嘗新環遊世界呢。
當然她承認近年吃得不算好。懶,連菜都不炒了。但她認為美國如今本來就不流行美味,而流行營養健康。結尾「花素漢堡」乍看是在讚美中國,卻彷彿在諷刺中國人特有的造假小聰明,但也可能是呼應文章開頭「中國人的傑作之一」大張紫菜。張愛玲只讚賞它好看、於人體有益、吃起來又簡便,就是沒寫它好吃——這就是張愛玲的不思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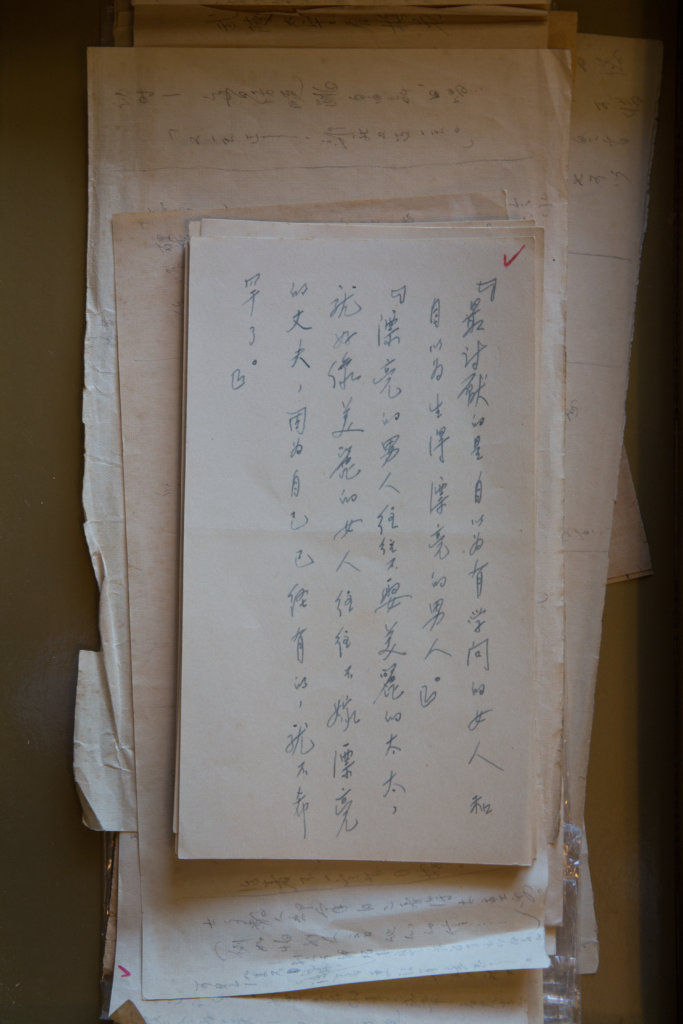
問:〈浮花浪蕊〉中洛貞為什麼要出走中國?這與現實中張愛玲的人生經歷有沒有關係?
答: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如此描述〈浮花浪蕊〉:「裏面是有好多自傳性材料,所以女主角脾氣很像我。」小說主角在香港的住所無牀無桌無椅,還自喜「簡化生活成功」,不就像是熱愛丟東西的晚年張愛玲?船上不必跟人打交道,因此「無牽無掛,舒服得飄飄然」,不就像她出了名的享受孤獨?
但是,〈浮花浪蕊〉不是自傳,更不是私小說。洛貞的家世與職業都跟張愛玲不一樣。
張愛玲在〈談吃與畫餅充飢〉寫到自己的西湖行,說她吃麵時被看一眼,就擔心會被舉報,但她沒把這經驗寫進〈浮花浪蕊〉,因為寫進去就無法讓讀者看出夾縫文章:洛貞離開中國不是擔心被迫害,而是拒絕變共犯。
《秧歌》與《赤地之戀》都有寫到社會動員,但還是有人出淤泥而不染。《赤地之戀》結尾還寫男主角決定回中國去反共,可見不想變共犯就應該離開,這是張愛玲到〈浮花浪蕊〉才寫到的。以目前證據,尚看不出她本人一九五二年離開時是因為不想變共犯。
那她離開的動機是什麼?依據《小團圓》,她十六、七歲就有離開中國的念頭,因為她小時候就看到媽媽姑姑出國,高中準備考倫敦大學,也有考上,歐戰爆發無法去,才改來香港。
《小團圓》中再度提到出國的打算是在戰爭結束後,女主角想到有沒可能夫妻一起流亡英國美國。「她自己去了也無法謀生,沒有學位,還要拖着個他?她不過因為她母親的緣故,像海員的子女總是面海,出了事就想往海上跑。但是也知道外國苦。」母親希望她留學,知道她想繼續寫作,還來信罵她「井底之蛙」。把念頭轉到美國是因為「看英國戰後十分狼狽,覺得他們現在自顧不暇」。《小團圓》寫:「只好蹲在家裏往國外投稿,也始終摸不出門路來。」這是一九四六年,「國外」應該是指美國刊物,當時香港並不在張愛玲腦裏。
一九五二年張愛玲之所以來香港,應該是不管有沒門路都想離開中國了。選擇香港是因為她能申請回港大復學,但還是想去美國,這是為何她一到香港馬上用英文寫《秧歌》。

她從沒在任何作品中寫過她從不反共變成反共的轉折點,因此〈浮花浪蕊〉很重要,《談吃》西湖那段也很重要。
從〈浮花浪蕊〉看來,張愛玲很同情那種有家累而無法離開的人(洛貞的姊姊、姊夫)。
〈重訪邊城〉英文版有寫到一位親戚,都來香港了,卻怕吃苦而回上海,後來遇到麻煩—張愛玲對這種人就不以為然,〈浮花浪蕊〉中這種人的代表是艾軍。
許多作家都是流亡後才寫出思鄉情濃的文章,張愛玲卻相反,她在努力想要離開的一九四六年寫下散文〈中國的日夜〉,大大抒發其中國情懷。到真的離開,作品中就沒流露一絲眷戀了。
在〈中國的日夜〉開頭詩裏的意象,通常比喻是落葉歸根,但是張愛玲卻把它想成一段愛戀,寫說葉子落下去是要去親吻自己的影子,影子也迎上去。最後「秋陽裏的/水門汀地上/靜靜睡在一起/它和它的愛」。這裏,張愛玲寫的是一個人在自己國家終老一生的幸福感。
再來數段,都在描述她在買菜途中看到的中國人面貌:髒衣服的小孩、叫賣的橘販、要賣肉卻被冷落的衰老娼妓。描寫道士的那段文字更是詩意驚人,把他想成「古時候傳奇故事裏那個做黃粱夢的人」,寫他跪下行乞的樣子「像一朵黑菊花徐徐開了」。
這些景象都是為了鋪陳以下的感受:「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我也喜歡覺得手與腳都是年輕有氣力的。而這一切都是連在一起的,不知為什麼。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我也都有份;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感情如此深沉,結尾卻是突兀而且不完整的「中國,到底」,然後就句點。
什麼意思呢?是確認「這裏到底是中國」?是譴責「中國正在往下沉」?是探問「中國到底會變怎樣」?還是自問「中國到底還屬不屬於我」?
也許四種意思都有,反映張愛玲此時的徬徨不安。

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雲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
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譙樓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
沉到底。……
中國,到底。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