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雅文創辧的木棉樹出版社,出版了很多有意思的童書和繪本。《木棉樹兒童文學月刊》也是本地罕有專注推廣兒童文學的兒童讀物,而且在資源及人手極度缺乏底下,竟然曾經持續運作了二十年,滋養了一代又一代兒童讀者。這件事本身就是奇蹟。若非有着過人的熱情與天真,實在無法堅持下去。長年與童書為伴,她始終保有一份「初心」,對閱讀仍抱着初看世界的眼神:打開書,就是打開一個世界,而童書的世界,也就是我們認識世界的起點。來看看她的分享。
明:《明周文化》編輯N
黃:黃雅文
明:最近看什麼書?
黃:在重看舒比格(Jurg Schubiger)的童書。很久以前看過《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非常驚豔。後來看到有新的譯本,就又買回來,當成新書那樣重讀一遍。原文是德文,現在讀的這本《當世界還不存在的時候》,嚴格來說作者有兩個,舒比格和他的朋友一人一篇,輪流講述這個世界的由來,以及它一開始的故事。

明:你看的書是否以童書為主?
黃:這幾十年的話,是的。最初是因為喜歡讀,才開始編;進了這一行,上了賊船就更加不讀不行。
明:為什麼這麼喜歡讀童書?
黃:也許因為它比較簡單,更適合傻蛋吧,哈哈。我喜歡那種簡單的書,小孩子讀了也能懂;長大以後重讀,又有更深一層感受;也許等到老了,回頭再讀還能有另一番感悟的書。好的童書是非常動人的。像安徒生的童話,小時候再喜歡,總也是囫圇吞棗,長大了再讀,感覺完全不一樣。
明:正想問,大人讀童書會不會覺得太簡單?而有一種說是給成人看的童書,你覺得如何?
黃:我不大了解那樣的書,就是看上去像是童書,其實不是寫給孩子讀的,更多只是為了迎合成年讀者的趣味而出版的書。對我來說,童書最重要的讀者一定是孩子,如果碰巧大人也愛讀的話,那是意外之喜。但這個順序不該反過來。
明:好的。說到安徒生童話,有些解讀是暗黑版的內容,你覺得這會破壞你的閱讀樂趣嗎?還是童話本來就應該有更多解讀可能?
黃:安徒生童話應該沒有暗黑版。(笑)他的童話很有美感,宗教意味也很濃,大部分都來自他個人的想像和創作。格林童話是收集民間傳說故事再改編的,所以才會挖出來暗黑版,也就是追溯到改編以前的原始版本。
其實也不用等到後來的暗黑版,小時候讀《藍鬍子》就把我嚇壞了。現在回頭看,那樣的故事有著真實歷史的印記,但那時候不懂,就不喜歡格林童話。

明:安徒生沒有暗黑版,但是有些解讀就是有比較殘酷的一面。
黃:安徒生的童話裡有很多悲劇,還有對冷漠現實的描寫。好人一定有好報、壞人一定沒好下場,那是格林童話,也是民間對善惡報應的樸素想像。安徒生的童話不是那樣的。
明:是的,像人魚公主就很慘。
黃:他筆下的真摯愛情,好像很少有不慘的。《柳樹下的夢》有點自傳色彩,寫的也是無望的愛情,就連裡面一對薑餅戀人,都只能以悲劇收場。
明:這樣看來,你對安徒生的評價是比較高?這是你會一直重讀的作品嗎?
黃:我確實比較偏愛安徒生。小時候那本葉君健翻譯的《安徒生童話集》,直到今天仍然健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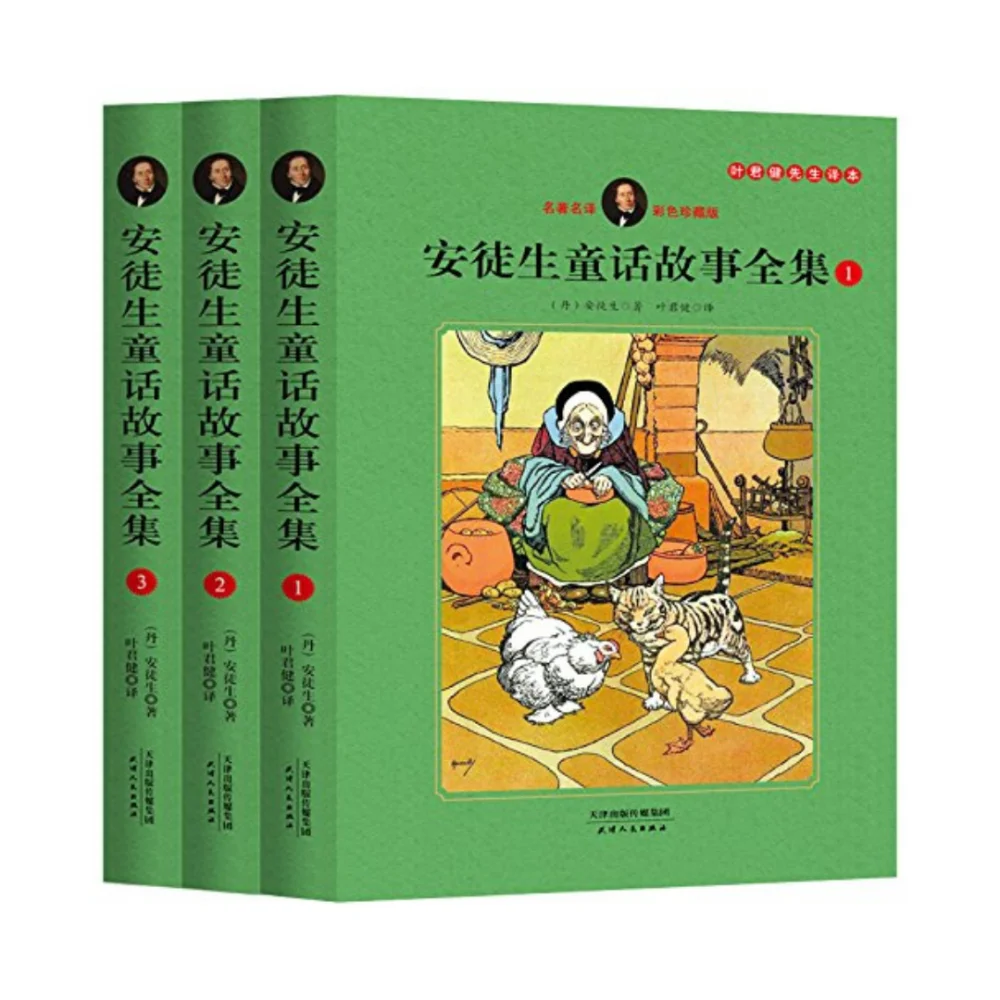
明:我小時候也是看葉君健譯本,那時候就覺得童話哪裡是美好呢?!所以說什麼「童話故事」的結局,其實是很諷刺的啊。
黃:人魚公主在海底生活的風景,還有她的姐姐們初到人間的經歷,不是很浪漫、很美好嗎?(笑)即使後來愛情失敗了,騎著玫瑰色的雲飄到天空,仍然有可能得到一個不滅的靈魂,不也很美嗎?反而白雪公主,一醒來發現被親了,就馬上高高興興地結婚了……這樣的故事是把小孩子當成笨蛋嗎?小時候看了就很氣憤。
明:好,說說舒比格,我沒讀過他的書。你是說只有簡體中文版?你會考慮出版繁體版嗎?
黃:應該不會,雖然在出版這件事情上,我們已經夠任性的了。這份工作做了二十幾年,留給大家最大的奇蹟就是:「啊!原來這家出版社還沒關門!」
明:那你選書有什麼標準?有什麼書是一定不會讀?
黃:其實我們都知道,雖然童書的對象是孩子,但購買的人群是大人,是家長。大人相比孩子,總是比較目標明確的,就像你問:閱讀有什麼用?(笑)家長也一定會問:這本書有什麼用?或者,這個故事有什麼意義?這是所有編輯都要被考問的必答題。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書,或回答得不夠好的書,命運可能也就不那麼美妙了。
所以我們與市場的鴻溝一直都在,就是賣得最好的書,往往都不是我們最愛的書。舒比格的故事為什麼令人驚嘆,因為它從頭到尾,都在一派天真又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這些故事有什麼意義?」讓大人問去吧,作者才不管呢!
明:孩子不會問有什麼用,只會說好不好看 。(笑)
黃:閱讀能力也是需要培養的,它不光光是指識字的能力。舒比格的書,我們沒有能力出版,想都不忍心去想。已經有很多繪本,愈是心愛,愈是堆在倉庫裡,看著就令人難過——一本沒有讀者的書,太寂寞了……哎,我好囉嗦啊!其實年輕的時候根本不會想那麼多,年紀大了就是不一樣。(笑)
明:明白,你對香港讀者的市場那麼悲觀?
黃:也沒有。我們有過很多超棒的小讀者,也遇見過很多開明的家長。也許更大的問題在於我自己,編輯的工作從選題開始,要把書做出來,也要把書賣出去。我沒能做好最後一步——不擅長,也不喜歡。
明:辛苦你了。說回讀書,你有什麼習慣,有沒有特定的喜歡的場所?
黃:我喜歡在過海巴士上讀書,到站的時候剛剛好。床上也是好地方。給我一張正經八百的桌子,我可能就會想,還是工作吧!別浪費了這麼好的書桌。

明:你和鄭政恆一樣,坐巴士看書不會頭暈。(笑)在床上看書很易睡着吧?又或者看到失眠?
黃:容易睡着好啊!尤其對我這種總是失眠的人來說,這也許就是閱讀對我來說最大的、功利上的用處。(笑)
明:那麼有沒有最瘋狂的讀書經歷?
黃:為了讀完一本借來的書,而整天不吃飯算不算?當時我媽媽不在家,留了錢讓我自己下樓去買,我一直想著看完這一段就去……結果一直沒去。那本書第二天要還給人家,書名我已經忘了,是我一個同學從她爸書櫃裡偷拿的。
小時候沒有書可看,借到什麼都看一通。因為書難得,好不好看、看沒看懂都堅持要看完。很多不符合年齡的書,都是這樣被我糟蹋完的。
明:其實我覺得你出版童書就夠瘋狂了。(笑)
黃:我也這麼覺得。(羞)
明:真可愛。好了,最後一條問題,為什麼還要閱讀?
黃:也許在我,閱讀只是從小延續下來的一個習慣。小時候搬家頻繁,好朋友都留不住,那時沒想過閱讀有什麼用,但很大程度上它安撫了獨自成長的寂寥。
這幾年很多同行和朋友流散各地。大家相互打氣說,要以閱讀(和寫作)來抵抗現實的醜惡。羞愧的是,其實我更多地還是把閱讀當成是最後的一個避難所。有時打開電視見到太多墮落的面孔,我會很想躲進那個充滿奇想和憧憬的童書世界,重溫我們最初的樣子。甚至今天的世界已被我們糟踐得面目全非了,重讀舒比格,也像是回到最初,當我們和萬物仍是懵懂天真的時候──
「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萬物都得學會如何生活。星星匯聚成星座。一些星星先試著排成長頸鹿的形狀,然後是棕櫚樹狀,玫瑰花狀,最後排成了大熊星座。
「太陽開始發光。它開始學習上山下山,日昇日落。
「月亮一直不知道自己該學些什麼。學發光嗎?在白天它覺得這個主意不好,在晚上它又覺得這個主意不錯。它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所以看起來有時圓有時缺。
「那時候的萬物很簡單地生活著,但它們都得弄清這種簡單到底是什麼。對火來說簡單的事,對風來說卻未必;對鳥來說簡單的事,對魚來說也未必;對樹根來說簡單的事,對樹枝也未必。」
……不好意思,我今天到底是來做什麼的?其實我就是來給舒比格打廣告的!之前以為沒有繁體中文譯本,原來有,是玉山社出的!大家快去買!(大笑)
(編按:訪問那天,黃雅文以為舒比格《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沒有繁體中譯版,後來她才發現玉山社的版本,於是補上最末一段。)

黃雅文
木棉樹出版社創辦人。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出版過一些童書和繪本,還做過一本叫《木棉樹兒童文學月刊》的雜誌──從1998年創刊到2019年停刊,是真正的從頭到尾一手包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