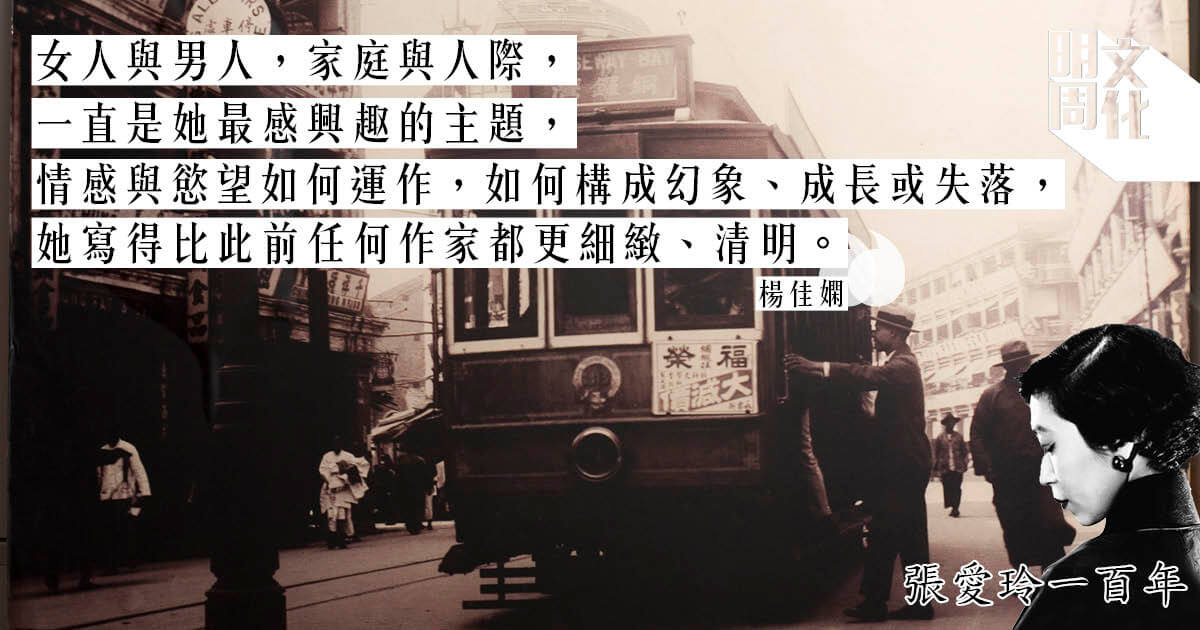
系列前言:談起張愛玲,我們會想起她一生曲折的際遇,斐然的文采才情,以及愛恨交織的戀愛韻事;也會想起她筆下形形色色的人物,還有每個萬轉千迴、緣起緣滅的故事。她看過城市的華美與悲哀,見盡時代的浮華頹唐,她以辛辣冷峻、細膩深長的筆調,道盡人世間各種蒼涼惆悵。今年是張愛玲百歲冥誕,如今我們再翻閱經典,無論愛情觀、美學品味,以及女性書寫,都是更堪細味。(黃靜美智子策劃)
二○二○年,既逢張愛玲出生百年,也是干支紀年中難得一遇的庚子年。對於後者,熟悉中國近現代史者,難免想起西風東漸的大勢,國族主義的功與過;對於前者,除了嘆惋天才,複習名篇,誦讀金句(它們被廣泛地雞湯化、張冠李戴、製成商品),還可以怎樣認識她在文學上的意義?
就從國族主義這一點講起吧。張愛玲個人形象與文學表述,總與個人主義劃上等號,一九五○年代初她離開大陸,充分顯示對集體主義的抗拒。而她在二戰期間上海成名,所寫不脫家庭婚戀生活瑣細,厭之者認定逃避現實,愛之者稱許為消解格式,貼近常民。實際上,她有能力思考國族與政治,也曾經發表意見。《小團圓》裏,九莉大考當天遇到日軍攻港,戰爭像巨大機器嘎嘎嘎駛過來,炮彈落到對街炸死了人,目睹而未死的,全都算倖存者。燼餘裏九莉想的是:
她希望這場戰事快點結束,再拖下去瓦罐不離井上破。
希望投降?希望日本兵打進來?
這又不是我們的戰爭犯得著為英殖民地送命?
當然這是遁詞。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們的戰爭。
國家主義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
九莉所謂「國家主義」,應是「民/國族主義」(Nationalism)另一譯名,而非Statism。「我們」指英殖民地上的華人,和英殖民者劃清界線?——下句就否認了。只要對手是日本,都是「我們」的戰爭。從甲午戰爭、五四運動到抗戰,「日本」就是「(現代)中國」永恆的敵人與他者,「抗日」早已被含括為「(現代)中國」成立的血肉。接着,九莉表達了個人的立場,她不將國家主義——亦即「愛國」,當作必須遵守的道德,而視為「宗教」,普遍的信仰——但她不信。換言之,她就年代與教養,雖然是五四的女兒,政治態度上,卻是五四主流價值的叛徒。
不單單是對於國族的態度,實際上,張愛玲對於五四另一個主流價值——「自由戀愛」,訴諸當事人自決的婚戀方式,同時被認為更為自然、更為人性——也抱持着高度懷疑。
當然,張愛玲並非發出質疑之聲的第一人或唯一一人。廬隱《海濱故人》(1923)、魯迅《傷逝》(1925)、丁玲《夢珂》(1927)等小說,均從不同角度展現受新式教育、追尋自由的五四現代女性,在實踐上面臨何種痛苦與窘迫。無關乎個體女性是否足夠傑出、足夠奮鬥,而與社會結構有關。
從這方面來看,張愛玲比廬隱、魯迅、丁玲,更長久且全面地以文學形式表現她的質疑。一方面,她的時代距離五四已過了二十年,或許更能有距離地審視此一口號帶來的正反面效應;另一方面,女人與男人,家庭與人際,一直是她最感興趣的主題,情感與慾望如何運作,如何構成幻象、成長或失落,她寫得比此前任何作家都更細緻、清明。
《鴻鸞禧》、《花凋》裏積極待嫁的「女結婚員」,《琉璃瓦》、《金鎖記》裏以女人美色與生殖力為商品、通過婚姻交換利益。《封鎖》、《紅玫瑰與白玫瑰》、《年青的時候》裏,無論對於男人女人,自由,包括婚戀的自由,其實都仍受制於社會主流框架,而女人可能在此過程中更缺乏選擇,更需服膺體制。張愛玲很少拿反叛性格的女性知識分子作主角,更多去寫受相當程度教育但仍無法、也未必想要衝破性別藩籬的普通都市女性,文憑屬於昂貴嫁妝,是炫耀的配件。
除此之外,我認為張愛玲在女性書寫另兩個面向上,同具開拓之功。第一,關於民國時期的女同性愛,第二,情與慾裏的屈從關係。
「同性愛」一詞來自日語,民國刊物常用,反而今日慣見的「同性戀」一詞較為稀罕。女同性愛在淩叔華、丁玲、郁達夫等人筆下都出現過。《小團圓》裏蕊秋就告誡女兒不要被另一個女孩「控制」,意即不要陷入同性戀愛。
一九五○年代寫成的《相見歡》,寫表姊妹伍太太對荀太太傾慕,荀太太也十分領受這份傾慕,伍太太的女兒旁觀者清,「荀太太並不是嘮叨,盡著說她自己從前的事。那是因為她知道她的事伍太太永遠有興趣」,而這種感情到了中年還能維繫,「上一代的人此後沒機會跟異性戀愛,所以感情深厚持久些」。這種觀點,似乎認定女性同性情誼只是少女時代的後遺。然而,最晚應在一九七○年代末之前完成的《同學少年都不賤》,張愛玲正面描寫了帶有身體慾望的女同性愛。
《同學少年都不賤》主角趙珏和恩娟,中學時代密友,後來兩人都到了美國,際遇卻判若泥雲。趙珏曾戀慕過學校風雲人物赫素容,不但偷偷貼臉磨蹭赫晾在外頭的衣服,甚至追蹤赫剛剛上過的廁所,坐上暗戀對象剛剛離開、猶有餘溫的馬桶,感受異樣親密。趙珏不滿足於精神戀愛,對赫的身體產生慾望,卻不知道該如何靠近,只能通過替代物,衣服或馬桶,遂行那難以伸張的渴求。
後來,趙珏開始與男人戀愛,自覺沖淨了過去對同性的愛慕;經過二十年情感跌跌撞撞,她認為只有「沒有目的/結果的愛」才是真愛。這樣的真愛,不見得只能在同性戀愛當中體認,然而,現實中卻只有存在於回憶中的同性戀愛,才庶幾近之,畢竟,異性戀關係難免被人審度:條件是否匹配、對象是否體面、是不是正當關係、有沒有生育。「沒有目的/結果的愛」,同時質疑了傳統包辦婚姻與五四「自由戀愛」,愛情不是為了雙方家族利益或標榜文明進步,也不是為了繁衍或救國而存在。
看來趙珏的同性愛經驗,也侷限在少女時光,延續了《相見歡》的說法。但是,小說另一主角恩娟卻非如此。趙珏中年與恩娟重逢,才發現她始終愛着中學同學芷琪,時地的阻隔、異性婚姻的成功,也沒有使愛消逝。趙珏感到駭異,並非因為發現原來恩娟是「真正的」(?)的同性戀,而是最為服膺異性戀婚姻價值、從婚姻這樁「合夥營業」得到最大好處的恩娟,事實上卻愛而不得、難以吐露,連婚姻帶來的高度社會回報都不能磨滅回憶與傷痛。趙珏所謂「沒有目的/結果的愛」,恩娟反倒無意之間實踐了。
再從情慾與屈從這一層面來看。張愛玲小說高度彰顯女性意識,但她並非教條化的女權主義者。早在《蘇青張愛玲對談記》(1945),二戰時期上海最重要的兩位女作家就談過兩性之間「被屈抑的快活」,今日看來或許不夠政治正確。從張愛玲小說觀察,她所留意並不單單只是女人如何獨立,還涉及一種明知不當為而為,壓抑但仍投入的激情。
例如,《第一爐香》葛薇龍完全清楚喬琪喬的卑劣為人,卻仍嫁給他,倚賴青春色相,替喬琪喬弄錢,替姑媽弄人。一旦年老色衰,下場可想而知。薇龍分析自我,「完全是為了他不愛她的緣故。也許喬琪喬根據過去的經驗,早已發現了這一個秘訣可以征服不可理喻的婦人心」。《小團圓》則以張愛玲小說過去從未出現的露骨性描寫,更深刻呈現屈抑與激情的雙生。這些性描寫並非為了增添賣點,而是體現愛情關係裏的恐怖——女人的身心苦痛不被正視,竟被當作情調,甚至佐證了男子氣概。即使如此,女人仍在其中掙扎求存,從身體聯繫心靈,從中確認親密。這看似愚勇的行動內存在着無悔的熱情,就算走到盡頭,還有一份悲傷與溫柔,多少年後還殘存夢裏,於意識不防備處湧現,也就是張在序言裏說的:「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迴,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
張愛玲的創作生涯很長,經歷了不同的政體與時空,顛沛中始終不放棄對創作反覆思索與實踐,新環境新讀者都是考驗。她並不滿足於只是重複操演上海時期的風格,即使最被讀者喜愛。有人說張愛玲到了美國以後才思枯竭,題材重複,也不再如少作時時拋出雋言警句。我卻以為,她後半生膠着反覆重寫類近的故事,近乎症候,正是她生命裏驅之不去的魔魅,《小團圓》說的「痛苦之浴」。更何況,《同學少年都不賤》叙事時空跨戰前戰後和中美兩地,叩問異性與同性的愛與滄桑,《小團圓》既總其大成,又在性與心理描寫上突破過往,直面不堪與陰翳——張愛玲赴美之後其實仍艱難地創造着,作為創作者,她從未懈怠。
作者:楊佳嫻,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台灣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台北詩歌節協同策展人。著有詩集《少女維特》、《金烏》等四部,散文集《瑪德蓮》、《小火山群》、《貓修羅》等五部,編有《臺灣成長小說選》、《九歌105年散文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