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藥可以結束一個人的性命;人死了,一切皆完結;酒不同,酒不會立刻結束人的性命……」,其實,文字又何嘗不是?寫故事的人逝去了,但在文字裏卻是永恆。6月8日,香港作家劉以鬯先生在東區醫院逝世,享年99歲。先生是作家亦是報人,生前佳作等身,中短篇小說、微小說、詩體小說、故事新編都寫得精妙。他亦曾為香港文學「正名」,說「香港不但有文學,而且有站在時代尖端的文學」。

⚡ 文章目錄
滬港的時空錯置
上月底,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所做《否想2046》的演講,以王家衛的經典電影《2046》作開端:梁朝偉飾演的作家周慕雲,六十年代住進東方酒店的2047號房間,面對2046房間裏進進出出的女性客人,情傷之時開始創作小說《2046》—「『2046』像是一個不可解讀的密碼、一個時間點、一個房間號碼,亦是一個未來的地方。」焦點由此被移至一個關乎香港的時間軸線,「在這個時間點,所有的記憶永存,『2046』是一個理想的、時空最後交匯的烏托邦」。
細想來,這一番時空與香港未來的交錯,背後藏着的莫不是劉以鬯和他的《酒徒》。王家衛因受《酒徒》啟發拍攝《2046》,又令梁朝偉化身劉以鬯,在電影的結尾亦不忘特別致謝。儘管作家曾在一次訪問中表示「他(王家衛)對我瞭解不是很深」,但不論《花樣年華》還是《2046》,能投射出如此林林總總的時空光影,莫不得益於劉以鬯小說中「時」與「空」的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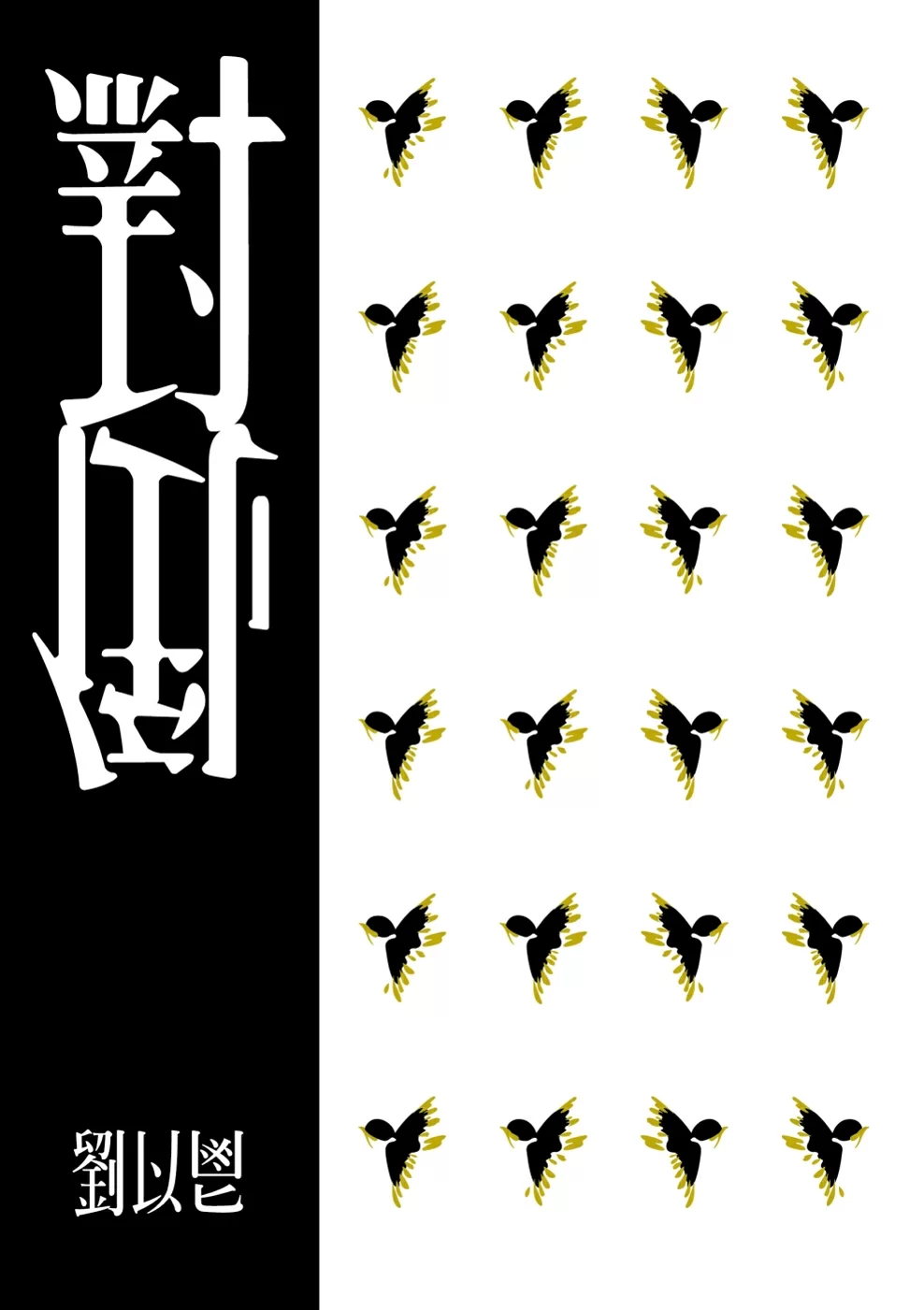
結尾大逆轉
都說劉以鬯的小說具有現代性、實驗性。在我看來,他作品中的「surprise ending」有着對時空趣味性的思量與編排。小說《打錯了》最為讀者津津樂道之一,文章上下兩部分,在空間上無絲毫改變,連文字也相差無幾,唯一通電話、幾句對白,主人公陳熙從一宗巴士事故的受害者變作目擊者。劉以鬯不止寫種種生活所呈現出的情與事,還將未呈現的、命運的殘酷與善意和盤托出:時間的一個錯置,成了一線生死的擦肩。《打錯了》作於1983年,後與其他短篇一起集結成冊;20年後,陳奕迅唱出黃偉文寫的:「遲兩秒搭上地下鐵能與你碰上麼,如提前十步入電梯誰又被錯過」,頗有20年前《打錯了》的意味在其中。
除了時間,劉以鬯對空間的結構性思索也是其小說奇妙之處。2013年,95歲的作家仍說想寫一個故事:兩輛電車對開,一輛從筲箕灣到西港城,另一輛由西港城行至筲箕灣,故事就發生於這方向完全相反又偶然交錯的電車。作家以電車路線為軌跡,將寫作的觸角延展,寫人情更是寫城市。

愛走走看看
劉以鬯小說中錯置的時與地,環境的描述是如斯的細緻入味,一切源於他的觀察力。傳媒人區家麟曾說,劉以鬯愛「看」:「他走在又一城,不望地面,他一路抬頭,目光銳利,留意五光十色的名店櫥窗。……坐在車上,他注視後退的街景,短短幾分鐘路程,他一直在看風景,說這裡沒變,那邊也沒變。香港電臺的大堂,有古董舊相片陳設,一般無人問津,過客們掂行掂過。劉以鬯二話不說,獨自走到展覽櫃前,凝神細看。」
與居港三十年卻少寫香港的徐訏不同,劉以鬯字句間都是香港。巴士在彌敦道上疾馳,新樓林立兩旁,掛著值得一看的招牌;男女相約,是去「利舞臺」,去百老匯戲院看那《亞爾瓊遜傳》,或去「皇室」看一齣《花樣年華》;吃宵夜,去九龍飯店,皇后道「鑽石」的滷味極好,適合下酒;主角噓噓的口哨不吹別的歌,但要吹那《勇敢的中國人》,唱片播放的是《愛你三百六十年》和《今天不回家》;旺角的食肆供應蝦餃、燒麥、春卷、果粉與叉燒包;人們炒金、炒樓、炒股票,抱怨著香港的治安也背負著賣子的困窘……
除了實體的都市空間,他的想像空間更加廣博。微小說《旅行》中,敘述者想著徐霞客的石灰岩地貌,想和80天環遊世界,想跟隨阿龍納斯到海底,也想看龐貝城的酒肆、捉吳哥窟的蝴蝶……空間何等無邊,卻只能在別人的書裏、思想裏獲得,結尾才猛然發現,敘述者是個失去雙腿的殘疾人。
其實,那一對相互倒置的郵票、那一雙各奔東西的飛鳥、黑與白既分明又相間的色彩……又何嘗不是對空間結構的另一層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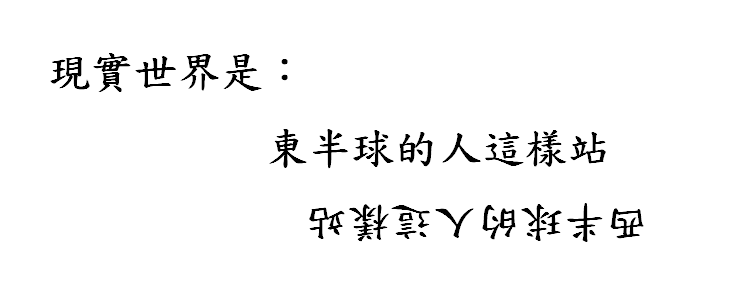
上海與香港的錘煉
從上海到香港的作家不少,但劉以鬯的人生歷程不止留在文字裏,在他身上亦混合手廿月山被兩個城市浸染、錘煉過的氣質,好似一杯「鴛鴦」—溫文爾雅、平易近人地勉勵後輩,如同奶茶的柔和與絲滑;而日寫餘萬字、奮力創新的劉以鬯又似咖啡因般不竭躍動。
作家令我想起上海的「老克勒」,那是一種風範、一種講究。在人們通常的見解中,「老克勒」指那些較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上海人,他們大多出身背景不錯,受良好的教育,彬彬有禮、有品德、有文化、有視野,講究生活的品位和情調,又還帶着點上海人的「腔調」。劉以鬯似乎全都符合,父親是英文翻譯官,哥哥是宋美齡的機要秘書,家境不錯。就讀的聖約翰大學,是美國聖公會在上海創辦的「東方哈佛」。導演黃勁輝拍攝的紀錄片《1918》裏,劉以鬯提到,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老師比較嚴格,讓學生背誦莎士比亞的英文原句。這造就了他良好的英文和文學功底,直到影片拍攝那時,他都還能背上一段。
此外,無論何時,劉以鬯同太太都以白淨面龐、俐落得體示人,在報紙副刊輝煌的年代,作家尚可以稿費維持有品位的生活——「半島下午茶、中環希爾頓酒店開幕後吃十多元一份自助餐,都是普通事情。」
如果說上海代表着一種青春年少的赤誠,那我想劉以鬯始終懷揣著他心中的「小王子」,不曾丟棄。訪問的作者同時形容,劉以鬯「喜愛跟我們分享小小藍莓雪糕鮮奶油夾餅」。訪問間歇,找不到洗手間無功而返的作家,講著帶外省口音的廣東話,在太太面前像個發脾氣的小孩。有時講座上,劉以鬯收到同學們有趣的提問,也會顧自地笑起來,引的在場觀眾也跟著他一起歡笑。
在上海流連過「孤島」,與那些南來到香港的上海人一樣,如《酒徒》所說「香港在招手。北角有霞飛路的情調。」仿若一個避世的、懷戀的空間,這個空間又永遠代表那個時空,劉的文字像時空隨意門,現代細閱又回到那個空間。但很快,他為寫稿、為文學,當然也是為一份生計撲心撲命、不竭創作的精神,又似乎與一個勤勤力力「搵一啖食」的香港人形象無異。未曾生於斯但長於斯的作家,一邊「娛人」一邊「娛己」,在報紙副刊衝鋒陷陣,「在忘掉自己的時候尋回自己」;得以如此,也正因香港這一獨特、包容的文化空間。
而他亦回應着這座城市,鼓勵新的作家,開設「我之試寫室」,不只自己力求與眾不同,也教那時的年輕作者們敢於嘗試。先生不是隻身來港,他帶著中國新文學的傳統而來,香港又令這種傳統於「在地化」的寫作中得以保存、得以延續,共同譜寫了新的「雙城記」。
先生近百仙逝,走過一世紀,但仍有太多不舍。這別離,留下創新的執著和敘事的精妙,令人們扼腕歎息一個時代的落幕,卻又好似直頭直面地上前詰問「文字的繼承者們,你們準備好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