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是幸運的,這是我要自知的事。」王樂儀不諱言,自己的詞人路,一直走得比其他同道平坦,因此她也不敢怠慢,珍惜每個機會。
現於阿姆斯特丹大學讀博士的王樂儀,暑假從荷蘭回港,迎接她為歌手黃妍包辦填詞的《九道痕跡》專輯推出,也看她有份改編的廣東話版百老匯音樂劇《攣攣成人禮》首演,同時接下許多訪問講座。這是她回港隔離完畢後首個訪問,高瘦斯文的她來到我們的影樓受訪。初時,她略顯拘謹,但很快便放心坦誠分享,流露真情。
「今年是我寫歌詞的第六、七年。」在昏暗的房間裏,王樂儀一邊說着,我們特別準備的投影,在她背後乍隱乍現,時見《慶祝無意義》、《無門》、《阿茲與海默》和《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等歌曲歌詞,盡是王樂儀近年引人共鳴的填詞作品。「我現在想做的,是透過我的作品嘗試打開多些文化和城市的景觀。雖然這樣講好似太大,但一首歌能做到少少事,少許顛覆,我就已經很開心。」
⚡ 文章目錄
遇上周耀輝 學生徒弟家人
和同代人一樣,王樂儀在廣東歌的浸淫下長大,Twins的歌是她中學時代哼唱的最愛,以前未曾留意到「詞人」在歌曲中的角色,但一直喜歡寫作小說散文。二◯一一年,她考入浸會大學,成為人文及創作系學生,遇上了詞人周耀輝,歌詞創作才走進她的生命。「耀輝剛好第一年回來香港,開了歌詞班。」王樂儀笑着說起這段回憶,「我見到這個班很多人reg(register,報讀),我就爭,其實我不太知是什麼來的,輾轉下又reg到,第一堂已經很開心,要分組講心事,從你的心事構思一首歌的idea。」
「那時候一個禮拜一首歌詞,接着一個創意練習,然後在班上把歌唱出,解釋為何會那樣寫,那個過程很赤裸的。」在歌詞班上,同儕憑歌寄意,她聽別人的故事時,也道出自己的真實情感,其間不止學到歌詞是溝通的文體,更令她發現生活上聆聽和理解的重要。

王樂儀重視歌詞班每一堂課,從不欠交功課或缺席,除了一次,因個人壓力太大而「鬼剃頭」脫髮,她才被逼請假。十年前這次告假,她至今仍舊難忘,「他(周耀輝)很嚴的,會說『你不交功課或請假,那就不如不要上課,把機會留給其他更珍惜的人』,所以我很驚,請假時就揭露給他看,他覺得我這個人很坦白,我們便開始熟絡。」
其後,王樂儀跟周耀輝傾訴心事,周耀輝也會和王樂儀講個人困擾,王樂儀當上了周耀輝的學術助手,周耀輝教導王樂儀做人處事,兩人因課堂而結緣,隨之自然地相處再交心,多次合填歌曲,最終築成了深厚的師徒友誼。他們去年合填的《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我就算全身有傷/心至少一寸未變壞」,暗地寫出對方是各自心中尚餘的一寸完美。
去年十一月,訪問周耀輝,其時《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剛剛推出,他也提到王樂儀,「我和王樂儀都對自己的血緣家庭有複雜的感情,慢慢相處,我發現我們成為了彼此的家人。」時隔大半年,像傳音筒般,把他的說話轉告王樂儀。聽後,她深受觸動,「現在有人喜歡跟我合作,其實要感謝他,因為我很多做事態度都是從他身上學習。」然後哽咽說着,「我本身是個不懂跟人溝通的人,我想普遍的年輕人也沒有大人會鼓勵你說出心事情感,但他每次都會很相信你做的事是有價值的,無論是你的憤怒,對世界的情緒,抑或愛。」
慶幸創作路上有伴扶持
一般而言,有意入行為流行廣東歌填詞者,起初需要不停填「Demo詞」,為原創樣本歌曲無酬填詞,等待唱片公司賞識,才有機會試為歌手寫詞,而這段等待總是漫長而磨人,叫人自我質疑。「而我,真的是幸運的,因為開頭第一個機會已經是詞人給我的,是耀輝很好的邀請我。我沒有Demo詞的修練,因此我很珍惜現在有的機會。」
王樂儀的出道詞作是吳雨霏二◯一五年的《想入非非》,和周耀輝合填。她記得,由初稿到定稿,一共改了十六次,但畢竟初出茅蘆,能夠保留到幾隻自己寫的字,經已心足。
後來,再經耀輝介紹,認識到唱作人王嘉儀。豈知兩個姓名相似、年紀相近的女生,一拍即合,成為了長期創作伙伴。



六年間,王樂儀包辦了王嘉儀三張專輯的填詞工作。在《Sophrology》裏探討廿歲女生城市愛情觀,在《Quarter》裏講正值廿五歲的迷失碰撞,前年的《殘》則思索城市的種種殘缺。這些年來,兩人攜手合作,一同追夢,也各自默默耕耘自己的事業,雖時有意見不合,但彼此卻藉着磨擦更加了解對方。
「我很珍惜這段友誼和合作關係。」王樂儀說,「在商業世界中有同行者很重要,特別是現在愈來愈難,捉摸不到可以做什麼,大家接受什麼時,很多東西都是新嘗試,若有同行人一起嘗試,你會較大膽,亦會事半功倍。」
「我很慶幸,在短短這幾年,已經有創作伙伴一起起步,之後的黃妍亦是。」歌手黃妍的新碟《九道痕跡》,收錄九首歌曲,全部歌詞都出自王樂儀手筆。因為專輯,王樂儀和黃妍兩人不斷見面聚會,日漸熟稔,多了公事以外的互動,反可滋養作品的內涵。「長期合作時,多了時間和藉口挖她內心的東西,可以寫到對歌唱者生命較精準的作品。」如《無聲浪》的歌詞,便是王樂儀聽過黃妍講腦退化症的外婆後所填寫,「彼此有話卻不懂人的衰老或變幻時」一句,取自真情真事,故亦至誠動人。
這種和歌手長期合作的創作模式,王樂儀認為,「可能是抗衡固有商業模式的做法,同時令音樂更加diverse的過程。」流行音樂工業追求速度和效益,每首歌何時派台、怎樣宣傳、熱門潛力,都涉及計算,但若果創作團隊之間多了人情關係,許多決定便少了計較,容許更多別具意義的事情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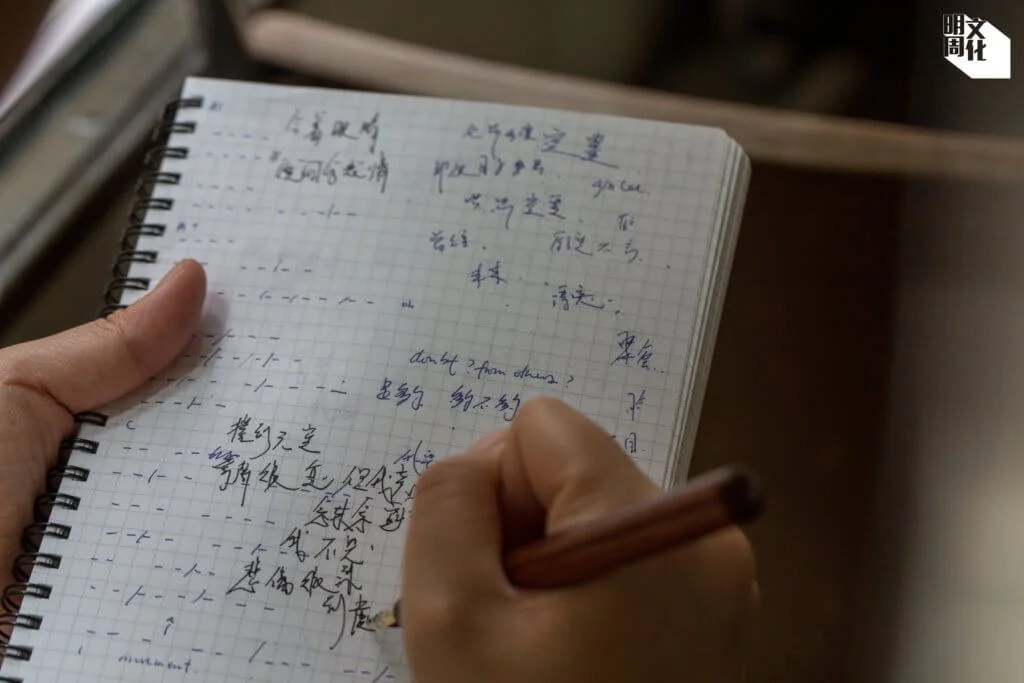
女詞人的責任和困頓
從《想入非非》起,王樂儀寫詞已有六、七年時間,累積不少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然而,「最初幾年,我質疑過自己是否可以叫作詞人,因為沒有那個mindset,純粹當是畢業後Freelance,寫些東西。」是直到後來,一位前輩鼓勵王樂儀,「香港很少女詞人,你要加油。」一句加油,讓她肯定自己是詞人,也意會到,身為「女詞人」有種責任。
如今回想,當時缺乏自信,是因為女詞人現實中罕見。「這個行業裏,有男性主導的部分,你可以數數有多少個女監製,的而且確,在香港,女生創作是否容易受到鼓勵呢?」她續道,「行業裏頭總有點不公道,我已寫過一些男歌手的歌,但到現在都有監製會猶豫,你較多寫女生的歌,寫不寫到男生的愛情?但你很少會問男士寫不寫到女生的愛情。」
「特別在創作上,性別是頗為明顯的問題。」作為香港為數不多的女詞人,王樂儀對自己許下承諾,要多寫女性情慾,開拓這城市的文化景觀。像她為樂隊Dusty Bottle填詞的《問世間情是何物》和《Break it down》,前者寫女生的戀物癖,後者則寫女性主導的性愛,可堪玩味的歌詞由型格自主的女主音唱出,得出不俗風評。

「我們的生活不止要把自己變成受難者。
我們的生活應該還可以有很多樂趣, 所以
我開始提自己, 是否可以遠離那堆情緒?
我們的生活其實可以再豐富點。」
雖然王樂儀立志要多寫情慾,困頓的時代卻讓她無法只談風月。這兩年,她無可避免把因時代而生的種種情緒和壓力,傾放在歌詞創作中。如黃妍的《九道痕跡》中許多首歌都傷痕纍纍、《阿茲與海默》漫溢對城市消逝不返的惋惜,還有《無門》裏對世界的懷疑與希望的錯落,或多或少折射了王樂儀的悲傷難過。
「但我今年開始多了自覺。我們的生活不止要把自己變成受難者。我們的生活應該還可以有很多樂趣,所以我開始提自己,是否可以遠離那堆情緒?我們的生活其實可以再豐富點。」她不願再沉溺於負面情緒,咬緊牙關走出低谷,以不同的姿態,寫出日常生活百態及想像。「我們不能長期受苦難,我們要慢慢重建自己應有的生活。」她堅定地說。
因此她寫了《輕盈》。她受黃妍的簡單從容性格啟發,再回贈《輕盈》給黃妍。歌詞寫到,「當有絕望未承受到/來讓我吹起肥皂泡」,重與輕矛盾但並存。填詞人親自解畫,「它不完全是輕盈的姿態,而是你在做沉重事情時,如何把它當作日常,由此減輕自己面對時的壓力。」

留守香港陪伴他人
讓王樂儀轉念,懂得以輕盈面對沉重的,是距離。
這兩年,王樂儀在紛紛擾擾的香港,積存過量的情緒,快要滿瀉時,總想回到荷蘭;但到她真正回到無風無浪的荷蘭,平和愜意的日常,卻讓人失卻了求進的躁動。「這個躁動,當我們在裏頭時,可能很負面,但它對於你追求自己的生活,對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你會比較對身邊的東西敏感。」從遠方抽身回望,她接受自己在香港的憤怒、悲傷甚或沉重,可能正是人們所需要的。在荷蘭和香港兩邊走,友人都關心王樂儀的去留,但她一早決心留低,就像師父周耀輝。
「他都可以在荷蘭教書,但他會想荷蘭是否需要他呢?但香港的學生可能更需要他,我也承繼了他的mindset,我覺得,我在這個地方可以做的事,可以給予的,會是更多。」

使她堅決留守香港的是人。「是我對身邊人的陪伴,有時會想,裏面的朋友出來後會見到什麼人呢?」她想起了很多人的面孔,熱淚盈眶,「現在我發現,在香港跟他人的連結,對我來說原來是最重要的,從他人身上看見自己才是最重要。」
於是,王樂儀繼續創作,藉着她筆下的歌詞,連繫人們,讓這個城市,縱使頹敗,尚有好歌,撫慰碎裂的心,讓人重拾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像她在《至少有歌》所寫,「聽著聽著發現再累也至少有歌/唱著以後我信聽朝更清朗」。
PROFILE
王樂儀(Yvett),詞人,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現為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分析學院博士候選人。師從著名詞人周耀輝,創作歌詞近七年,長期與王嘉儀和黃妍等歌手合作,最近包辦黃妍《九道痕跡》專輯所有歌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