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人類學家Gordon Mathews花不少時間在家中創作音樂,不時寫歌至凌晨,直至他的妻子Yoko細意提醒,才記起是時候上牀休息。訪問當日,我們在他的辦公室一起聽一首歌,畫面夾雜抗爭場面、小丑、科幻的城市黑夜,伴隨不斷重複的旋律,像跌進漩渦裏,往深處打轉。那首曲子叫〈Lament for a Dying City〉。
成為人類學家之前,他曾經在紐約當一年全職爵士樂手,他創作的歌曲結合爵士、古典音樂和電子音樂,「很多人都覺得我的音樂很怪。」說罷他招牌式地仰頭大笑。
也許人類學家,都得帶點「古怪」。他們總是縱身躍進陌生的文化,撇開偏見以嶄新的目光看世界。他們眼中,每個人都可以是怪人,包括自己。
⚡ 文章目錄
由外人到自己人
人類學是研究他者的學科,在Gordon看來,人類學家是專業的外人(professional outsider)。人類學家透過長時間進行田野調查,跟研究對象建立關係,浸淫在他們的生活和文化中,甚至成為他們的一分子。他經常鼓勵學生研究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由二○○六年開始研究被視為龍蛇混雜、生人勿近的重慶大廈。在他眼中,重慶大廈是世界的縮影,他稱之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他看到全球化下廉價商品如何流通,聆聽在港難民的故事,感受不同族裔的共存和角力。

常說,人類學家最大的工作是閒逛(Hang out)。他花了七年時間在不同店舖蹓躂,跟人聊天,不時在大廈的賓館過夜。他記得初到重慶大廈,有人跟他說:「由於你是鬼佬,所以我肯定你不是卧底警察。那麼你一定是……CIA!」他又曾經因為注射胰島素的副作用而暈倒,被一些巴基斯坦人以為他飲醉酒,在大廈裏花天酒地。如今說起得啖笑,但可以想像要融入他者的社羣,由外人變自己人,好不容易。
至今,他仍與非牟利機構定期跟大廈內的人開組討論時政。Gordon的非裔好友兼小組的常客Dixon說:「你無法想像這個人來了多少趟重慶大廈!」Gordon解釋:「人類學不是科學,沒有假定(hypothesis)。有些事情,只有透過跟人聊天才能知道。」正如社會學家William Bruce Cameron所說:"Not everything that counts can be counted, and not everything that can be counted counts."並非所有算數的東西都可以計算,也不是所有可以計算的東西都算數。
我們跟他到重慶大廈走一轉,他背着小背包,仍舊好奇地四處張望。每走幾步,便遇到相識的店主,高興地寒暄一番。他也會嘗試進陌生的店跟店主攀談。他從不視大廈內的人為用完即棄的研究對象,而是真心待他們為朋友。進入大廈前,他細心叮囑攝影師拍攝人臉前要先問准被拍者,以免為他們添麻煩。當他的朋友有需要,他不介意提供金錢上的幫助,「我很清楚,我從《重慶大廈》一書所獲得的比起這裏的人要多, 我因此而感到有點愧疚,畢竟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Gordon將要搬離校園,他甚至考慮過搬到重慶大廈。他回想起二○一九年抗爭期間,有一晚公共交通都關閉了,於是他須在重慶大廈過一晚,「來到的時候,Damn!一家餐廳為我準備了美味的免費晚餐!這地方令我有家的感覺。」

同學,思考吧!
Gordon大概自小就意會到自己與美國社會格格不入。他大學時曾以迷幻藥為哲學論文主題,質問人何以為人?現實是否只能建基於由A去B去C的邏輯推論?在耶魯大學修畢美國研究後,他的同學都籌謀從事金融,在大公司打工,他想的卻是離開美國,到陌生的地方,看外面的世界。
當時要離開美國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在外國教英文。他選擇了日本。在等待遲遲未確認的機票和教席的時間,他待在加州的森林中,靠着五十美元捱了兩個月,日日食蘋果和花生醬麵包度日。如是,他以這戲劇化的方式跟他的祖國說再見。
到日本時,他才廿五歲,用入門級的日語教小朋友英文,雞同鴨講,靠表情和手勢教些簡單的詞彙:clock、happy、sad……轉換的,除了是語言和文化,也是他的身份,「在美國,我感到跟社會疏離,可是在日本,人們總是叫我『外人だ』(指外國人)。大家都是『外人』(outsider),正常不過。而這狀況,對我而言似乎更加自然。」
Gordon第一次來香港,是一九八三年,當時他以背包客身份到訪,他坦言:「除了重慶大廈之外,對香港沒有太深印象。」後來,他輾轉到了中文大學任教人類學,由過客,變成公民,親歷香港的起跌。

疫症緣故,大學裏大部分課堂都轉為網上授課,Gordon位於中文大學內的辦公室顯得格外清靜。他教授關於全球化的科目,學生來自五湖四海,因時差關係,有外國學生甚至一邊駕駛貨櫃車一邊上課。有他的學生形容上他的堂「都幾chur」,因為他從不照書直說,反而九成時間在向學生發問,來回辯論,腦袋沒有停下來的空間。
馬傑偉曾向Gordon請教教學秘訣,他分享的經驗是:在課堂上向同學借一張一百元紙幣,再在全班面前撕爛,用意是探討金錢的意義。我向Gordon提起此事,他澄清道:「我現在不會這樣做了!我原本是利用這行為說明金錢只是一張紙,是人類發明,它本身沒有內在價值,而每次課堂後我都會把錢還給同學。但有一次被我借錢的同學,生氣得在我肚子打了一拳,因為他真的很需要那一百元食飯坐車。事後我們向對方鄭重地道歉。」
取而代之,他現在會在白紙上寫上$100,然後嘗試跟同學交換一張真的一百元紙幣。同樣可引發討論,而不會傷害到任何人的感情。不得不佩服他的鬼馬創意,無所不用其極,誓要刺激學生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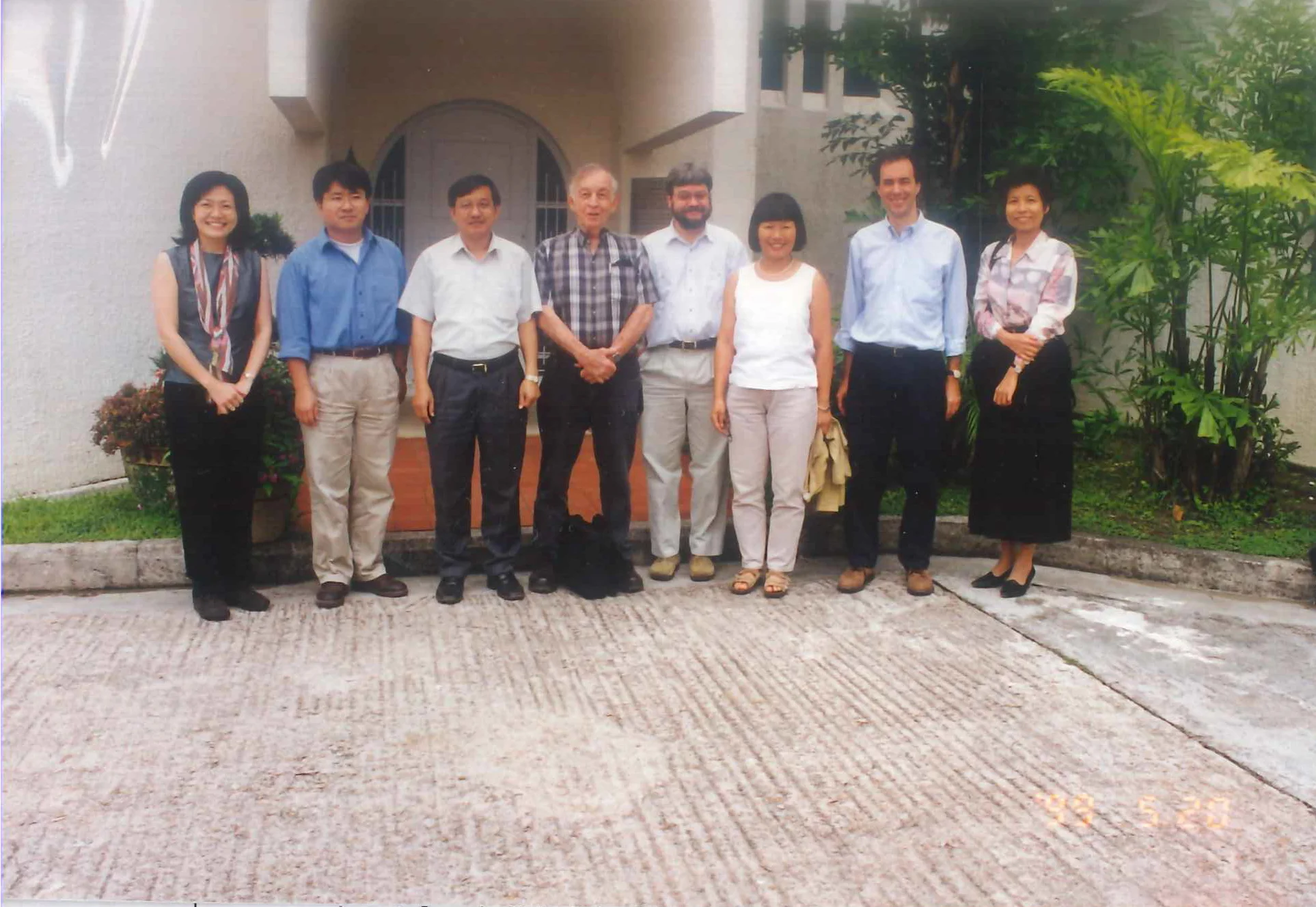
別放棄對世界好奇
今年二月,Gordon在Facebook宣布決定延遲退休,繼續留港任教,引導學生批判思考。於他,教授批判思維不只是工作,更是他的使命,以至信仰,他明言:「當我不能再教批判思維,或者會因為教授批判思維而被警告,甚至入獄,那代表香港已不再是我所認識的地方。」
在很多人心目中,這危機愈來愈大,甚至已經實現了,但他仍保持謹慎樂觀,他補充道:「但我認為以上的事不會發生,因為我相信這(學習批判思維)是人們希望得到的教育……你要知道,我的學生常笑我太樂觀。」

但再樂觀,講到香港的未來,他不免凝重起來。多年來研究香港人身份的他,留意到香港開始接受「愛國訓練」,他指:「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被教育要對國家有歸屬感,但他們被教導的是不加批判地愛國。」他記得在美國自小就要宣誓,他把手放在胸口,唸出誓詞:”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他緊接道:「很明顯美國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平等和自由,看看警察對待黑人和白人示威者的分別就知道。」
理性上,他很清楚這是政治宣傳,但感性上,他坦承:「無可避免地,我仍然有丁點兒的自豪感。這就是愛國思想植根(instill)在我們身上的方法。」
他始終相信愛國也可以具批判式性:「你可以愛你的國家,但可時可以批評她。」但他最希望的,是有一日我們可以打破國界,創造一種新的忠誠(loyalty),「我希望有一天,我們都可以成為純粹的人類,忠於地球,這會是很美好的事。」
他最近上載了一首新歌,名稱是〈Kafka Comes to Hong Kong〉,卡夫卡式的荒謬,已無處不在。然而世界再無稽,年屆六十五的他,也不放棄對世界的好奇和熱情,「它(人類學)使我無止境地好奇……我想再過幾年十年,甚至幾年後,我就會死,我不知道,但我希望無論我去到哪裏,都可以上網看新聞,世界發生的不同事情太有趣了!」
現時,他還在進行不同的研究,例如最近開始研究老去,「我的媽媽有認知障礙症,她什麼都記不起了,但她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現時社會常說production ageing,為什麼老了還要productive呢?」
世界再壞,他仍會繼續以人類學之眼,看這奇怪的世界。

Profile:
Gordon Mathews(麥高登),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主要研究題目包括人生的意義、全球化、身份認同等等。曾出版書籍包括《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2013)、《南中國的世界城:廣州的非洲人與低端全球化》(2019)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