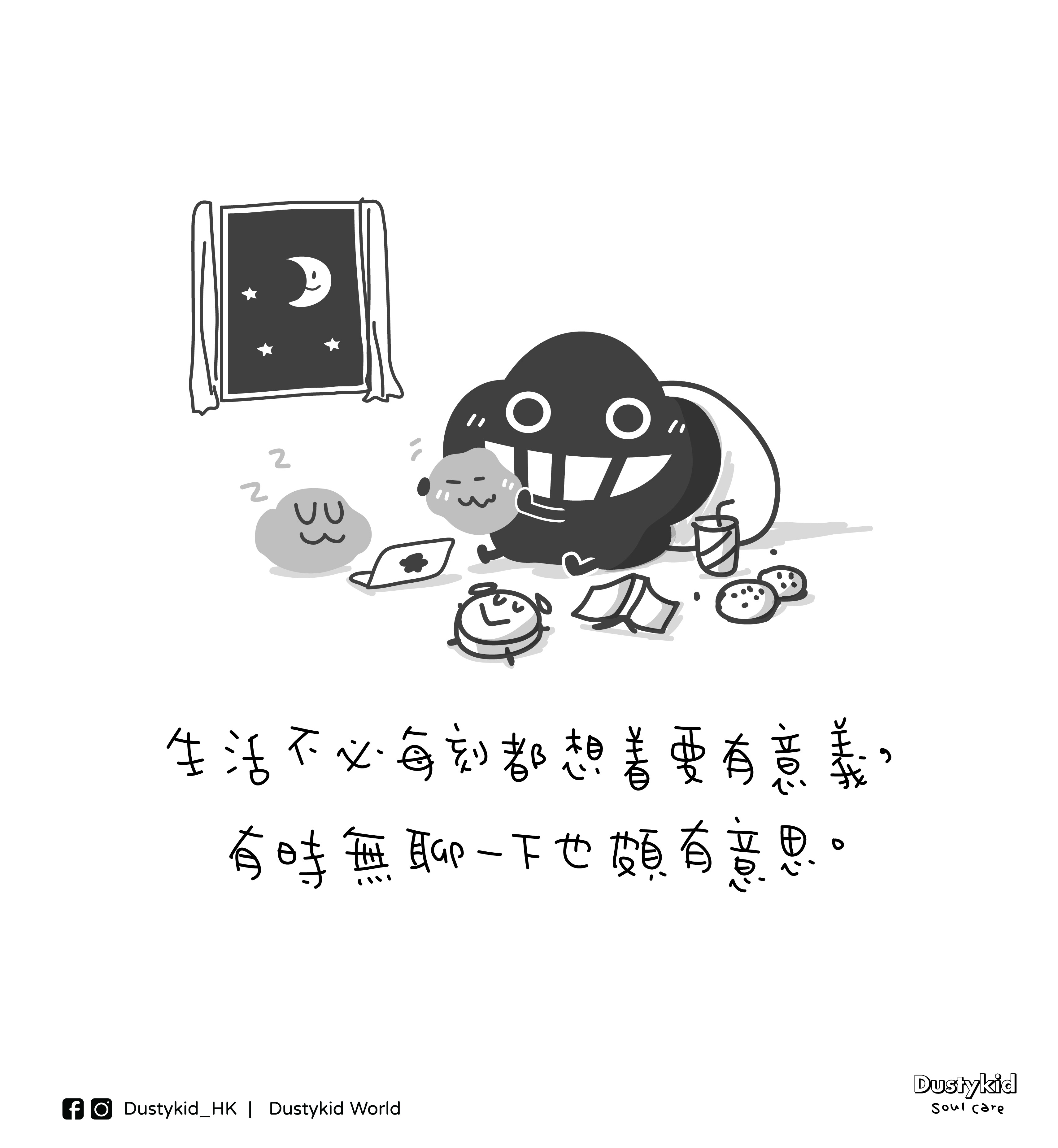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編導的《我想結束這一切》無疑是今年最令人期待的新作之一。這位傳奇編劇一向珍惜羽毛,產量甚少,但自九十年代末起編寫的《玩謝麥高維治》、《何必偏偏玩謝我》、《無痛失戀》,一直都是備受影迷追捧的偏鋒經典。考夫曼之後自己執導過令人如入大觀園的《腦作大業》和停格動畫片《不正常麗莎》,事隔五年,他終於在Netflix平台的支持下完成新一部長片作品。考夫曼的電影一向以複雜、出人意表的架構見稱,內容往往能別開生面地打破現實與虛構/想像的界限;電影正式推出以前,大家都很好奇在Netflix比較自由的框架和製作條件之下,考夫曼會如何再發揮他的想像力。

電影改編加拿大作家Iain Reid的同名小說,表面上,那是關於女主角「Lucy」與她(不太喜歡的)男朋友Jake初次回家見家長的旅程。在這個看似沒有戲劇衝突的背景底下,女主角、Jake、與及Jake的父母,在故事發展的途中,都會有令人措手不及的行徑與脫離常理的發展。在Jake那個略帶陰沉、布置間隔又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異感的老家,他的父母會神經兮兮地與Jake有的沒的不着邊際地聊天,那種餐桌上的別扭怪異氣氛,會一直蔓延,到全屋,以至全齣電影的每一個角落。
《我想》後三分之二的段落,明顯不合理的事情愈來愈多,例如女主角會沒來由地被喚作不同的名字(Lucia、Louisa、Ames)、Jake的父母會突然變老或變年輕並換上不同裝扮、女主角在地庫發現本來應該是她創作的畫、女主角自己創作的詩句竟變成Jake睡房中另一個作者的詩集作品等等。電影的後半段,女主角與Jake冒風雪回家,故事在這裏變得更為抽象:Jake與女主角在車廂中展開關於電影、媒體與人生的冗長辯論,更脫線地到公路旁的雪糕店買雪糕 ,最後—恍似完全忘記了現實的—Jake帶女主角回到他上學的高中學校,迎來超現實式的高潮結局。

電影在Netflix上公開不久後,影評網站IndieWire就刊載了一篇題為〈考夫曼的《我想結束這一切》導讀:導演拆解謎團〉的訪問文章,它旋即成為了影迷們競相傳閱的指南;大家在看完電影後,好像都渴求着某一種(權威的)解讀與說法。這篇文章,我看到一半就放下了(雖然之後也盡責地將它讀完)。
考夫曼有一個說法無疑是很動聽的:他說《我想》出現的三個主要角色(女主角、Jake、還有在片中間歇閃現的老頭校工)都是同一個人的腦海幻想,一切都是子虛烏有,他特別想透過《我想》試驗「幻想」能否完全脫離它的現實依據,單獨地存在。正是這個原因,正是考夫曼與《我想》強烈抱持一種「所有都不實在、所有都是幻象」的虛無態度,所以電影最終理所當然地沒有描寫出什麼着實、可以被認同、可以被感受與討論的內容與情感(一切都給電影最後混淆虛實真假的尾聲推翻了)。考夫曼的題解導讀,在這個思路之下,都變成了一種機智刁鑽的猜謎/解謎遊戲—的確是巧妙奪目,但那也不過是無關痛癢的腦袋練習。


考夫曼對身外的現實世界的偏狹理解和觀察,在《我想》終於難以避免地發展成把整部電影都拖垮的致命傷。《腦作大業》中從主觀角度出發對大千世界百種人物的描寫,與及箇中調劑的自嘲與幽默感,在《我想》幾乎蕩然無存。在《不正常麗莎》中,男主角發覺他與四周的人事逐漸脫軌,無法與他人正常溝通;在他眼中看來,所有除他以外的人,都慢慢長成同一個模樣、發着同一把聲音。這一種拒絕整個外在世界的傾向,去到《我想》,就令全片發展成關於一個人(也就是考夫曼)沒有節制、自我封閉的內在思路,但可惜的是那個人徹底否定了他自己的所思所想有任何實質的意義。《我想》大量引經據典,借鑑以往的劇場文學作品等等,遠眺猶如七寶樓臺,令人目迷,但拆碎下來細看端詳,卻感不成文章,自說自話。
作者簡介
安娜,現職大館當代美術館助理策展人、溝電影節策劃之一。天秤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