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沒想到我會以這樣的方式遭遇中港矛盾。
父親從深圳回到廣州,去諮詢那位他所信服的介入科主任。主任給他出主意:管它是個什麼東西,直接消融掉就好了。當即安排十天後做射頻消融術。
聽到這個消息我急壞了,顧不上正在上班,連打好幾個電話回家:「做穿刺也好,手術也好,都是為了取組織做活檢來判斷肺部的問題。醫生也說現在不知道那裏是原發、轉移,還是炎症,如果做消融就取不出組織做活檢,那我們如何判斷下一步治療應該怎麼做?這時候不搞清楚,將來只能糊裏糊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亂治。我上網查了,就算是原發肺癌都分好幾種,肺腺癌、鱗狀細胞癌、大細胞癌的用藥都不一樣,何況盧醫生都說早期肺癌最好是做手術,而且他覺得原發肺癌的機率比較大,如果消融了就沒辦法判斷了呀。」
但無論如何,父親油煙不進,他反問我:「為什麼要弄清楚呢?反正要除掉。」
於是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橫亙在我和父親之間的,是一道「認識論」的鴻溝,是「為什麼」和「為什麼不」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思路。在我看來理所當然先找出問題,分析問題,然後解決問題的邏輯順序,在父親眼中是「教條、迂腐、書呆子」。他認為內地的醫生講理論雖然講不過香港的醫生,可他們的實際經驗擺在那裏,直覺擺在那裏──你折騰一番把問題搞清楚了又怎麼樣?到最後解決不了還不是白搭。倒不如跟着感覺走,說不定「歪打正着」呢?
我氣急敗壞地叫:「這還沒到要靠『歪打正着』的地步啊!」
退一萬步說,我們是自從生病起才接觸癌症,而專科醫生已經在這領域工作一輩子,我們怎麼可能知道得比醫生還多呢?當然是力所能及找最好的醫生做代理人,聽從代理人的建議行事。我說香港的醫療知識與國際接軌,父親說內地的病人數量最多,於是又回到「外國的月亮是否比中國圓」的老調。
吵到最後我們彼此無法說服對方,父親一句「你又不是我,你又不是醫生」,再也不肯接我的電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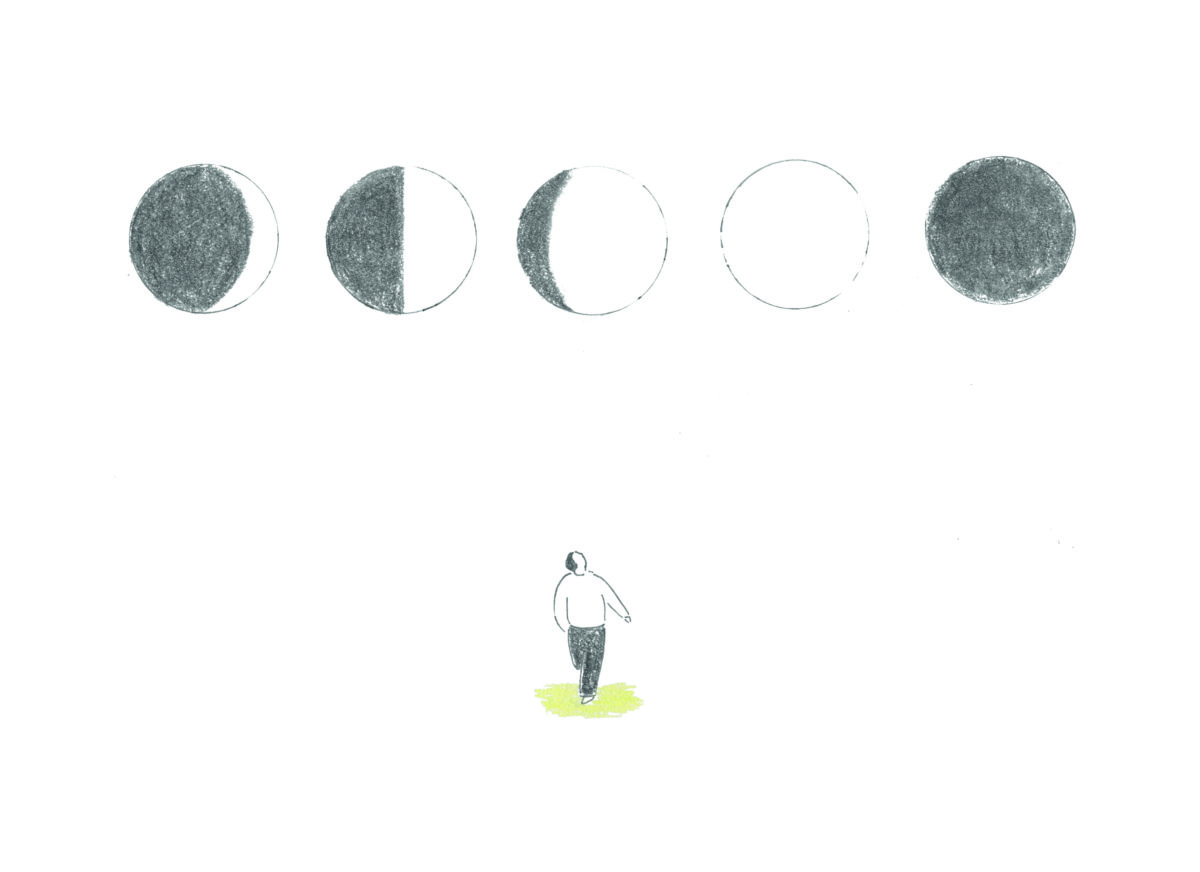
* * *
更沒想到的事還在後面。
冷靜了一天,眼看沒法講道理,我給父親發信息,深情回顧我們父女情誼,懇求他積極面對疾病,不要逃避。結果父親以同樣深情回信,語氣宛如與我隔空相對而跪,說他一定將生命堅持到底,而立即接受消融治療就是他的行動:「你就相信老爸一次,讓老爸自己做主吧」。過一陣,他在我們一家三口的微信羣裏轉發熱門文章《癌症不是病──它是一種身體的求生機制》。
我氣昏過去:「爸爸,即使你不信香港的醫生,至少別發這種東西來刺激我吧。」可他顯然是信了,直到第二天那篇文章被微信官方闢謠,蓋上「謠言」戳印,他才不再說話。
我又拜託親戚幫我勸說父親。我家有位有錢親戚,已經投資移民到香港,為人最是珍惜生命,平常連洗牙都要去養和醫院。我想如果這位親戚現身說法,總有辦法勸得動父親吧。
沒想到親戚專程上廣州,在我家坐了一晚,與父親一番推心置腹、促膝長談之後,回來不僅反過來勸說我尊重父親的意願,還熱心地給父親推薦了一位西藏活佛。
至此我情緒徹底崩潰。那幾天,我每天以淚洗面,上班躲在自己格子裏哭,晚上下班不是去朋友家裏喝酒,就是哭着和朋友打電話。身邊所有知心朋友都被我找了一遍。
我像祥林嫂一樣向每一位朋友哭訴:「為什麼我爸爸,一個西醫,在得了癌症、信仰受到終極考驗的時刻,寧可相信活佛、氣功和《癌症不是病》?我覺得我好像不認識我爸爸了。」
* * *
朋友們聽說我的遭遇,反應各不一樣。
有一晚三人在小林家喝酒,我們都是從內地來香港上學,繼而留下工作生活十幾年的朋友。小林說,她一直是家族微信羣的闢謠專家,孜孜不倦地將長輩們轉發的每一篇《測測你的體質是酸性還是鹼性》、《米飯你吃對了嗎》、《快看!這些收費即將上調》逐一求證破解,引用權威信息來源在羣裏以正視聽。經年累月地做下來,起到的效果是父母至少不再一見到排版文章就盲目相信,真有什麼事情好奇,會想到先問她一下。她還帶父母來香港打流感針,做身體檢查,潛移默化地讓父母感受香港的先進醫療水平。
這些事情我從來沒有做過。我在我家大羣裏從不說話,連拜年都懶得,更沒眼看那些長輩們分享的微信文章。一起喝酒的另一個朋友是男生,他和我一樣冷淡孤僻,但他對待父母的方式比較簡單粗暴:「我媽不敢不聽我的。」他已經成長為當家之主。
有一晚我給一個已經做了母親的朋友打電話。她丈夫知道我家出事,體貼地負責照顧孩子,讓她專心和我煲電話粥。她聽我哭着講完,自己也哭了,她說:「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你不能替你父親的生命負責。就像我媽媽得了糖尿病,可是她精神有點問題,總不記得吃藥,有時候又以為吃藥是有人想害她。難道我把她從老家接到自己家裏來,每天守着她吃藥嗎?這幾年看着她牙齒差不多掉光了,腳也總是爛着,只是因為糖尿病不吃藥,我心裏怎過得去?可是我能怎樣呢?我有自己的家要顧,我的孩子才兩歲,現在肚裏又有一個,我還要上班,但這些只不過是轉移注意力。每當我想起媽媽,我就內疚得喘不過氣。」
有個朋友是精神科醫生,她聽我說完,不禁感慨:「你對你爸爸的感情真深啊。我對我爸從來沒有這樣的感情,他如果死去,我不會難過。」我知道她的童年不幸福,她用那黑暗年代的幼小掙扎,換來成年後的無痛分離。我如今雖然哭得像個孩子,但我確已是大人。
她坦誠地說:「平時遇到這樣的心理輔導,我的專業訓練是對病人家屬說『你不是他,你不能替他決定,那是他自己的生命』,就像孩子吸毒,母親想不通。可是說到底,終極那條底線,是個體生命的邊界。」
只有一個朋友羨慕我的痛苦。她的父親在得知自己生病之後,誰也沒有告訴,自殺了。
* * *
踉踉蹌蹌地捱到父親去做消融術前一天,父親高興地安慰我說:「你放心吧,主任答應在消融之前順便取一些組織留作化驗,這下就可以一箭雙雕了。」
我的香港醫生朋友知道後說:「那樣做跟穿刺或者做手術取組織還是不一樣。姑且不論內地醫院的病理報告水平,我很擔心這樣做取不到足夠的組織樣本做病理分析材料。」
果然,病理報告出來,肺部沒有發現癌細胞。
父親在消融術後恢復了幾天,經由朋友介紹,和母親去參加為期半個月的封閉式氣功訓練營。他們在氣功營裏每天吃得好睡得香,彷彿中了邪一樣,身邊都是疑難雜症奇蹟康復的營友,大家天天練功團契,父親還接受師父單獨發功,據說真有氣感。他們只偶然和我打電話,還說氣功營正好缺保健醫生,邀請他們考慮常駐機構為營友保健。
父親從氣功營出來,每天清晨和下午繼續定時練功,傍晚還有熱心的師父隔空送氣,他就在家打坐接氣。練氣功的人不主張吃西藥或者接觸任何輻射,誓將唯心主義發揮到極致。
他感覺自己身體恢復得很好,不想去檢查。我說,距離上次住院過去一個多月了,驗個血總不算什麼大事。結果驗血報告出來,AFP升得厲害。氣功界對此現象的解釋是:這是肝臟鬱結被氣打散了,一個必經過程,再堅持些時日就會大病化小。不要去驗,免得動搖意志。
我跟父親說,既然這個氣功營這麼好,我也想去看一看。在一個初冬的周末,父親開車帶我去氣功營。那天不是營期,地方極安靜。我們沒有預約,竟意外遇到了和父母也只有一面之緣的總舵主。他熱情地將我們迎進屋喝茶。
我不是一個完全排斥另類療法的人,自己也曾研究辟穀。總舵主年過半百,頭髮烏黑,中氣十足,顯得頗有道行。然而當他嘗試說服我,用一本自己編纂的論文集,我就去魅了。那是一本典型的內地風格學術論文集,一時在中文系,一時在社科院,一時在歷史系,沒有統一字體和格式。
回家路上我對父親說:「氣功這門學問太深奧,需要國學底蘊和悟性,沒有二三十年童子功,臨時抱佛腳可能有點困難。」(六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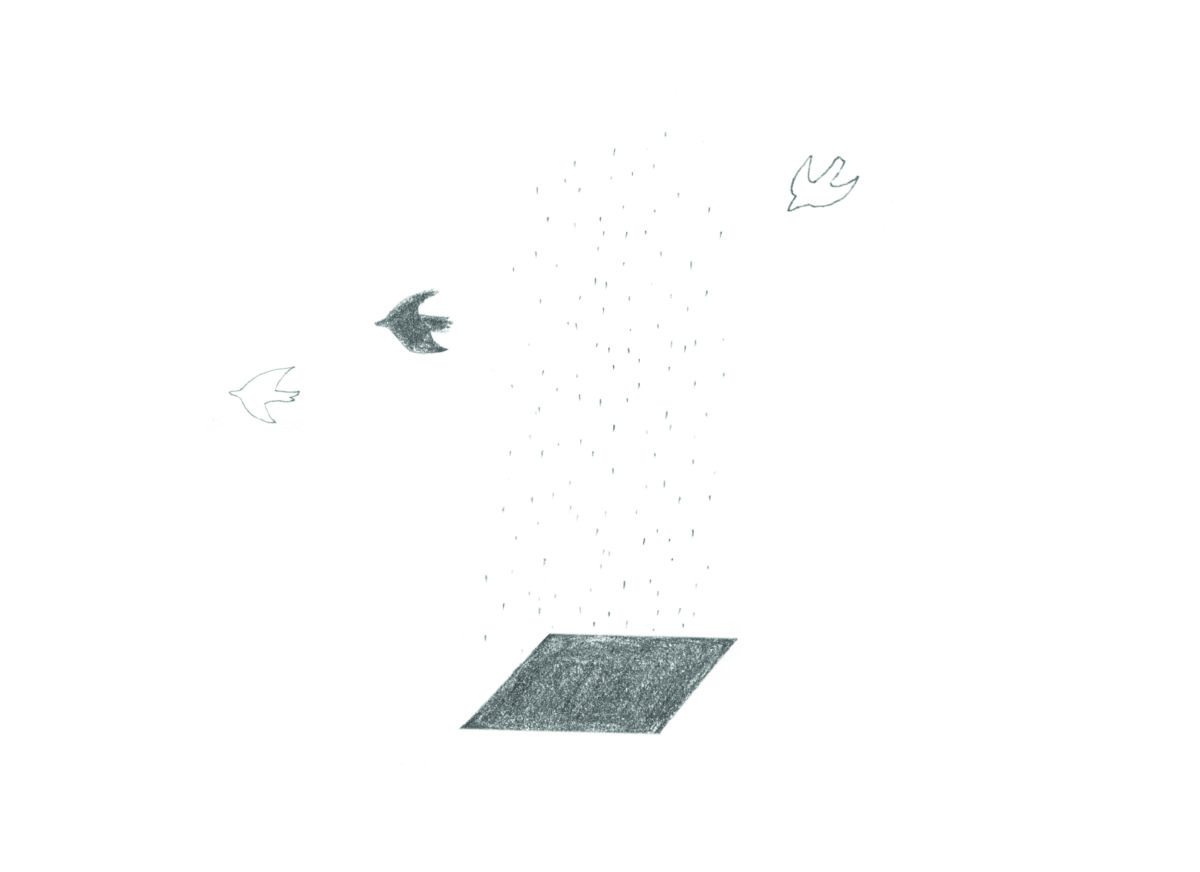
作者簡介
王雅雋,80後廣州人, 在香港工作和生活十二年,離家日久。因為父親一場病,連月來和家人奔波於廣州、深圳、香港的醫院求醫問藥。本系列記錄這段五味雜陳的看病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