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四年的諾貝爾文學奬由南韓作家韓江摘下桂冠,成為首位奪得該獎的南韓作家及亞洲女性作家。韓江的作品聚焦韓國社會狀況,譬如《素食者》呈現受父權壓迫的女子,《少年來了》及《永不告別》分別以光州事件及濟州四三事件的血腥歷史為藍本書寫世代創傷。瑞典學院讚揚她「以熾熱且詩意的文體直面歷史創傷,同時揭露人類生命的脆弱」。
韓江在瑞典學院致辭時提到,自己的創作核心都是兩個問題:為甚麼這個世界如此暴力和痛苦?然而,怎麼這個世界竟能如此美麗?我們找來本地文學研究學者楊彩杰及劇場編導黃呈欣,一起探討韓江文學中呈現的暴力與美麗。

⚡ 文章目錄
《素食者》 人是否完全無辜?
要談論韓江的文學,就不能不談代表作之一《素食者》。韓江早年已活躍韓國文壇,在國內奪得多個文學獎,直至二○一六年憑着第三本長篇小說《素食者》(二○○七年)奪下國際曼布克獎(後改名為布克國際獎),成為亞洲獲得該項殊榮的第一人,聲名大噪。
故事圍繞素食者英惠由忽然戒肉到斷絕食物的經歷,先後由她的丈夫、姐夫和姐姐三人的視角作敘述,逐步挖掘出父權文化壓迫的暴力和痛苦。去年十二月七日,韓江在瑞典學院致辭,提到自己寫作此書時苦苦思索幾道問題:「人是否完全無辜?」「人在何等程度上能拒絕暴力?」「當人拒絕成為人類這物種時會發生甚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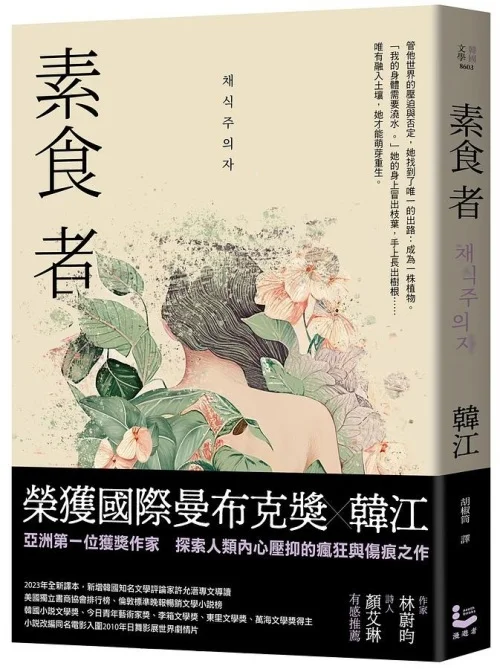
以精巧敘事呈現壓迫者羣象
巴黎索邦學院法國文學及比較文學博士楊彩杰熟讀韓江所有中譯文本,她指,《素食者》三位敘事者分別象徵形而下者、形而上者,以及父權的紅利參與者,「在三個章節會看到時間的推移,從三方的角度去回看素食者英惠由不吃肉一直到被送往精神病院,這些人是怎樣將他們的意志施加在她身上。最初源於英惠受父親虐待的原生家庭問題,但現在是加上其他人一同在整個制度之上去剝奪這位素食者。所以最後英惠想像自己是一棵樹,想逃離制度,逃離人類社會的關係網。」
她認為這個敘事結構相當精巧:「韓江不是用一種很直接的方式去呈現時間推移,而且從來都不是透過英惠去講自己的經歷,而是透過三個部分去講整個制度如何壓迫她。這種精巧在於每一個部分集中在一個人的焦點,但合起來能看到社會整體的羣象,主角身邊的人代表社會不同面向如何剝奪一個女性作為人的不同特性。」
去年本地劇團「藝君子劇團」大受好評的劇目《植物人》,靈感意念之一正正是這部《素食者》。身兼編導的藝術總監黃呈欣表示,除了出於劇團「植物思人」系列的概念,也因為《素食者》的可演性甚高。「《素食者》根據韓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創作一個虛構的小說,但是文字的掌握讓我感到一個抽身的視角,以冷調的狀態慢慢進入一些很強烈的情感,例如性慾,或者是男性沙文主義怎樣蠶食女性。」

她指,書中的角色不是一般為推進情節而做些大龍鳳,而是真正由不同敘事和觀點去閱讀個體和事件,也以素食者去代表弱勢,不只是一些人與人之間的事,是批判韓國根深蒂固的父權思想。在《植物人》中,黃呈欣同樣保留了三章結構,敘事者則設定為女人的丈夫、姨甥和姐姐,分別指向大眾、小眾以及沉默的大多數;並且設計由女演員飾演所有壓迫者,女主角則由唯一男演員擔演。她說:「小說文字是2D的藝術的想像,搬到舞台就成為3D或4D的表現。我是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其實令到英惠最失望或最痛苦的,並不是男性的壓迫,而是作為同性的壓迫和沉默。在這個層面上,女性在沙文主義的社會裏面亦是威逼者。當通過劇場上的性別調轉,會衍生一種抽離的感覺,令不論男性和女性都會反思。我希望這樣可以更立體呈現到《素食者》文本背後蘊含的意義。」
《少年來了》 生者能拯救死者嗎?
韓江所刻劃的暴力,除了來自父權社會,還有一段段韓國歷史上血腥的國家暴力,包括一九八○年席捲全國、撼動當代韓國政治的重要民主化運動「光州事件」。
光州其實是韓江的出生地。她於一九七○年生於光州,九歲時隨家人搬到首爾,那時是光州發生大規模屠殺前大約四個月。其後,韓江讀到一本由倖存者和死者家屬秘密出版的攝影集,看到光州居民和學生被軍事勢力屠殺的殘酷畫面,同時又見到醫院外人們大排長龍等待捐血的圖像,當時她試着理解這兩者的不相容,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行為如何各走極端。
直至二○一二年,韓江開始構思書寫光州事件。那年冬天,她到了埋葬光州事件遇難者遺體的望月洞墓,那時她告訴自己,不但要直面光州事件,甚至是更多反覆出現的國家暴力歷史。於是,她寫下了另一部探索人類黑暗與暴力的代表作《少年來了》(二○一四年)。


直面歷史創傷 探索人類暴力
浩和朋友正戴參加了反抗全斗煥政權的示威遊行,他在這一場暴力鎮壓中,目睹正戴被軍人當街射殺,然後前往道廳的尚武館尋找他的屍體。與《素食者》類似,《少年來了》全書分七個章節,由不同敘事者展開陳述,包括正戴、負責處理遺體入殮的女學生、曾在拘留所遭受非人對待的大學生,東浩的母親等等。
對於這種敘事,楊彩杰認為,常見的寫法是透過個別人物的經歷反映出他怎樣經歷大時代,折射出一個面向,「但是韓江這種多角度敘事,會看到時代不是純粹單一佈景板。時代是化歸為當中的人物。像《素食者》,時代化歸於丈夫、藝術家、姐姐這些人的身上。壓迫其實在個體、人與人之間施加的權力,構成了時代。《少年來了》借敘事者的個人經歷,例如有人參加過女性運動,有的是勞工保障運動等等,從光州事件出發,前前後後牽連其他社會事件。這一種多角度的敘事,是將社會和時代化為在一個人身上,不只是指向單一事件(光州事件),本身自帶一些情節背景而進入歷史。這是拓闊了光州事件的書寫,帶出韓國民主化歷程上一脈相承或引伸出來的事件,例如轉型正義、女權運動、勞工運動,囚權問題諸如此類,是會拉闊了整個暴力的邏輯。」
在《少年來了》中,韓江仔細描繪各種血腥殘酷、屍橫遍野的殺戮場景,如用紀錄鏡頭放大每一寸血肉模糊的屍體。楊彩杰曾辦過《少年來了》讀書會,有不少讀者都表示書中的描述使人不忍直睹。黃呈欣形容是「有一種鋒利冷酷的感覺,但同時有血有肉」,她說:「《少年來了》用既冷酷又有感性的情緒去描述如此殘酷的重大歷史事件。因為它的冷酷,令到讀者不是以客觀的第三者視角去閱讀一個歷史紀錄,而是進入了事件。」
黃呈欣依然記得最初讀到《少年來了》開首仔細描繪屍橫遍野的慘狀,「如果只量化了事件,像有幾多萬條屍體,有一具沒了右手的屍體等等,這樣會令到人的感性和同理心慢慢減少。我們劇場有個字眼,In-yer-face,即把事情毫無隱藏,活生生呈現人前的時候,你才會面對到究竟政治衍生出來的一些戰爭、暴力事件,以及遺禍是怎麼樣。」
韓江在瑞典學院致辭中提及,寫作《少年來了》時,最初腦海反覆浮現兩個提問:「現在能幫助過去嗎?生者能拯救死者嗎?」後來她發現,問題或許應該倒過來:「過去能幫助現在嗎?死者能拯救生者嗎?」
她用熾熱而詩意的書寫探索人類極端的暴力,其實為了從中提問理解他人的可能。

《永不告別》 能與所有痕跡輕易告別嗎?
同樣書寫韓國歷史創傷,小說《永不告別》(二○二一年)聚焦在一九四七年的「濟州四三事件」歷史悲劇,但同一時間,也是寫與歷史相連的現在——無法與痛苦痕迹告別的現在。
故事主角是小說家慶荷及攝影師朋友仁善。開首花大量篇幅描述慶荷因撰寫屠殺主題的書而飽受失眠噩夢的痛苦,及後才娓娓道出仁善家族經歷濟州無差別平民大屠殺的苦難。楊彩杰形容,在現有的四本中譯本中(上述三本,連同《白》),《永不告別》是較難閱讀,也是最有野心的創作。「《少年來了》和《素食者》從文學角度來看技巧很好,但會看到「炫技」感覺,《永不告別》就放棄了這種寫法。沒有很快就直達事件的核心,直到接近二百頁後才取出歷史素材,如報章紀錄、倖存者家屬的資料搜查,開始寫大歷史。之所以說野心,是韓江沒有用過去那種很快吸引讀者進入事件的寫法,而是更多地面對後人怎麼面對他們僅有的那些資料和回憶。」
不只韓國,當一個地方經歷集體創傷,不少作者都會想以作品記下時代,凝視無法言說的痛。楊彩杰認為,作者對於怎麼獲得及運用那些「材料」的覺悟,作為讀者是能看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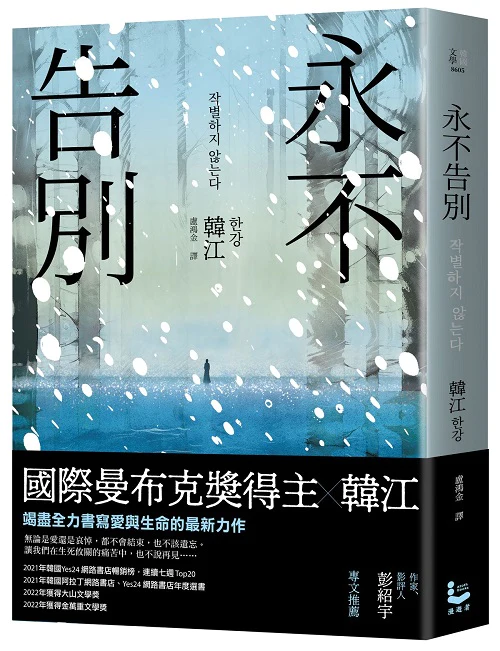
寫作者的意識
「我既然下定決心要寫屠殺和拷問的內容,怎麼能盼望總有一天能擺脫痛苦,能與所有的痕跡輕易告別?」這是一段慶荷關於寫作歷史創傷的自述,類似的思考反覆出現在《永不告別》中。作為家族苦難的記憶傳承,韓江也藉仁善的傷勢作出隱喻:「他們說縫合部位不能結痂,要繼續出血,我必須感受到疼痛,否則被切除的神經上方就會徹底死掉。」無處不見她對於後人面對歷史傷痕的責任與痛苦的思考。
楊彩杰坦言,從這幾本小說中都能看到韓江對於怎樣書寫歷史創傷,是有一個重要的寫作者意識。「韓江用長篇小說講暴力,但其實這個暴力的邏輯是沒有改變,民主化的歷程有沒有進步呢?韓江是將那些單一的故事,放在整個歷史的長河上面去看。當時韓江寫《少年來了》是轉型正義民主化,完全沒有心理包袱、政治壓力。但一個創作者對於自己用一個再現的方式去呈現創傷,呈現世界,是需要很大的反思。作為文藝創作,怎樣有一個meta-narrative(宏大敘事)的位置,是要真誠地面對的。」
痛苦和愛存在的原因
「為甚麼這個世界如此暴力和痛苦?然而,怎麼這個世界竟能如此美麗?」這就是韓江直面自己創作核心的問題。
韓江解釋,這兩句問題之間的張力和內心掙扎是寫作動力,而且從第一本小說起,在她心中這兩個問題至今依然保持不變。例如《永不告別》中,仁善的母親是濟州大屠殺倖存者,一直苦尋親人遺骨,舉辦正式葬禮,終此一生承受漫長痛苦,只為拒絕遺忘。韓江想問的是:人可以愛到甚麼程度?極限在哪裏?愛到甚麼程度依然能保持人性?
楊彩杰認為《永不告別》中,不論兩位主角,抑或倖存者,這些人物都是很有堅持。「那個時代歷史變遷,當中有一些人與人之間的扶持,或者後人堅持不懈地對於死難者爭取或紀念,我都看到一種堅毅,牢記歷史,持續下去,而當中不是沒有反思,這裏面就是有一種愛。」而對於痛苦和美麗之間,黃呈欣表示:「那種露骨和極致的書寫,我會覺得韓江是一個極度坦白、極度純粹的人。她只是在描述真實生命的美麗。像《素食者》用了很多文字篇幅去形容那種扭曲、沉溺的狀態,當中一定是有美學,如在英惠胎記那一段描述,或者用花作比喻,描述扭曲的性愛的魅力。如果你能達到一個同理心,才會思考衍生出來的禍害有多少。」
十二月十日,韓江一身素淨全黑衣裳,走到瑞典諾貝爾獎典禮上致辭,末段如此說:「我自小就想知道我們誕生的原因。痛苦和愛存在的原因。這些問題,文學數千年來已一直提問,至今依然不休。……閱讀與文學創作,是站在一切破壞生命的行為之對立面。我希望和大家分享這個文學獎的意義——一同於此對抗暴力。」她聲線輕柔,吐出來的句子卻何等具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