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自古以來一直是人類存活的最大敵人,因此也成了文學的常見題材。在文學作品中,疫病常寄寓為一種莫名奇妙的不可抗力,引發無窮想像;作家多藉此探求在疫病流行社會中,努力求生人類的境況,以及他們應對境況展現的人性。
⚡ 文章目錄
《十日談》

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留傳後世的最出色作品,必為《十日談》(Decameron)。《十日談》為一冊短篇小說集,寫於1348年,叫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爆發後。
見證家鄉佛羅倫斯因瘟疫死了十多萬人,整個歐洲生靈塗炭後,薄伽丘便執筆寫了此書,講述了三男七女總共十人,因瘟疫而到郊外別墅避世玩樂,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渡日,最終合計講了一百個故事的經過。 小說集開首非常寫實地描繪了人們患上瘟疫的慘況:「在我主降生後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麗的城市——就是那繁華的佛羅倫薩,發生了一場可怖的瘟疫。」
「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間或是在胳肢窩下隆然腫起一個瘤來,到後來愈長愈大……這以後,病徵又變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體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現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時候是稀稀疏疏的幾大塊,有時候又細又密;不過反正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樣,是死亡的預兆。」
受瘟疫可怕景象震撼,薄伽丘寫到,大難當前,人們對自己的人生,都有了「活在當下」的態度,但以不同方式實踐。有的清心寡欲,對外間不聞不問,但求時光飛逝;有的則不為明天而籌謀,只為今日而盡歡,縱情暢飲,為所欲為。而對自身生命有自覺性的書中人物則是第三種人,雖一走了之,但卻不只沉歡作樂,仍要保守規矩,好好過活。
從書中可窺探到中世紀歷經「黑死病」時的社會情況,從而想像到身處該時代的生活和心態,思考疫症當前的人生路。
《瘟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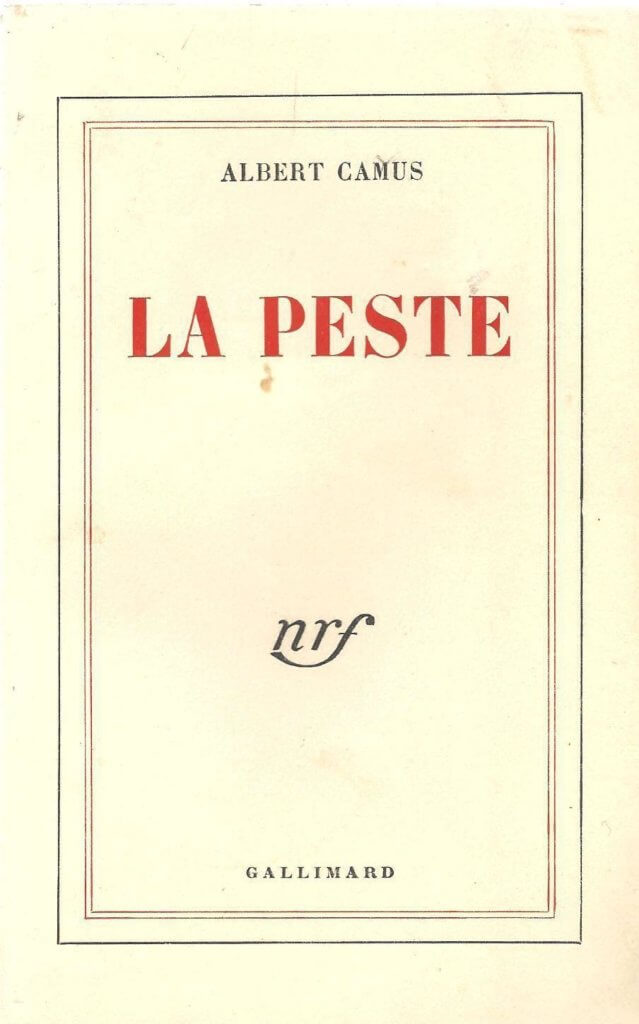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存在主義作家卡繆(Albert Camus)1947年寫成的《瘟疫》(La Peste,又譯名《鼠疫》),為其代表作之一。《瘟疫》為虛構小說,敘述法屬阿爾及利亞城市奧蘭(Oran)於1940年代再度爆發「黑死病」的故事。
最初,奧蘭街頭無端出現大量死老鼠,人們不以為然;後來,人們逐漸因病死去,醫生診斷為「黑死病」。然而,政府卻以「為免引起公眾恐慌」為由,遲遲不願做防疫準備措施,結果,要到疫情不可收拾,政府才下令封城。
卡繆主要描寫的,便是封城之後,奧蘭城內人們的存在態度,希望與絕望,隔離和孤獨,恐懼與不安。借小說內人物的經歷,卡繆以冷漠的筆觸,延續過去的觀點,寫出了人類面對極大荒謬的反應和狀態。也有評論指,小說可以為政治寓言,探討法國在二戰時如何反抗納粹的歷史。
《瘟疫》前期有一段意味深長,尤其警世:「天災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認為它不是現實,而是一場即將消失的噩夢。然而噩夢並不一定消失,在噩夢接連的過程裡,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義者,因為他們未曾採取必要的措施。這裡的市民所犯的過錯,並不比別處的人更多些,只不過是他們忘了應該虛心一些罷了,他們以為自己對付任何事情都有辦法,這就意味著他們以為天災不可能發生。他們依然幹自己的行當,做出門的準備和發表議論。他們怎麼會想到那使前途毀滅、往來斷絕和議論停止的鼠疫呢?他們滿以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禍從天降,那就誰也不得自由了。」

《盲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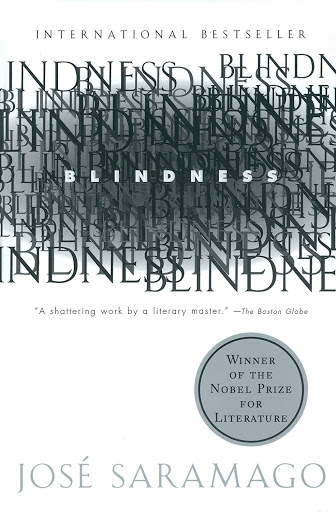
晚卡繆數十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萄牙小說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代表作《盲目》(Blindness,又譯《失明症漫記》)亦是一本關於「傳染病」的小說,但這次的疫症,是小說家所憑空虛構的。
《盲目》天馬行空,描述了某西方現代都市中,一種名為「白色眼疾」,令人無緣無故失去視力的惡疾正在肆虐。換句話說,失明,成為了一種傳染病。隨着失明症在城內蔓延,羣眾陷入恐慌,害怕自己也會相繼失明。拒絕積極應對事態發展的政府,以為將失明病人鎖進「瘋人院」便可了事,然而,一些未被政府囚禁的失明惡徒,卻趁火打劫,乘人們看不見之危,壞事做盡,奴役並虐待他人。在沒有人看見底下,社會的文明秩序迅速分崩離析。
小說中,唯能夠保持健全視力的,是「眼科醫生的妻子」,可是她卻承擔了觀看的痛苦。她的眼晴──讀者也透過她的雙眼──見證了人們在突如其來的大疫災前,比起高尚自制,更多沉淪墮落,比起善良互助,更見醜惡自私。也許薩拉馬戈對人性過於悲觀?但至少他提出了一個我們不願樂見但又可能的世界,警惕今人,「如果我們不能完全像人一樣生活,那至少應盡一切努力不完全淪為禽獸。」
薩拉馬戈把他的角色人物置放於極端的境遇中,逼使他們必須直面道德倫理的各種判斷,挑戰自己的信仰價值;而目睹書中人們掙扎抉擇的讀者,不禁也反問自身若然陷入類近情形,又會如何自處。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見;如果你能看見,就要仔細觀察。」
薩拉馬戈選了《箴言書》此一句,放在《盲目》卷頭開首,是為引子。

《末世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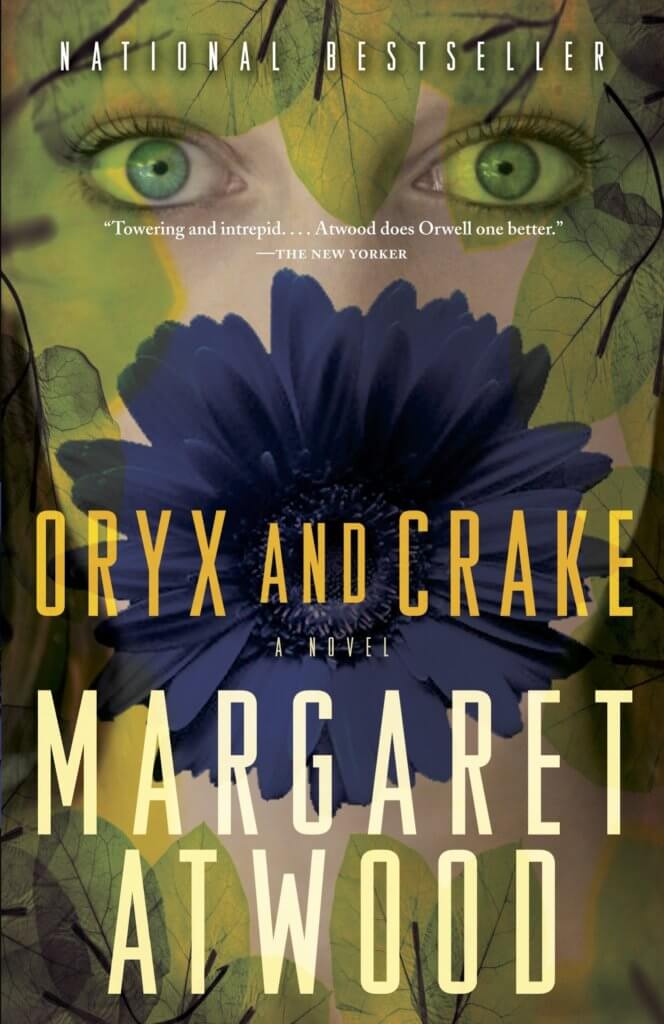
在2003年SARS從中國傳播全球,侵襲各國之際,以《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聞名的加拿大小說家瑪嘉烈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推出了新作《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
《末》的故事開首,已引入了一個後末日時空:史無前例的大瘟疫滅絕了人類,只剩下自稱「雪人」的主角、一羣像似人非人的「克雷科人」(Craker),以及許多叫他們避之則吉的基因改造猛獸,在荒涼的世界中共處。
慢慢讀下去,才發現,原來「雪人」在文明崩壞前,本名為吉米(Jimmy),而他的老友叫作克雷科(Crake)。克雷科是個天才,專精生物科技,大學畢業後也進入生物科技企業工作。他在企業中的秘密任務,就是透過基因工程,製造改造人「克雷科人」──有超人的生活機能、不需破壞自然就能生存的新人種。改造過人後,克雷科又遇上了自小就被迫當雛妓的奧麗克絲(Oryx),聽了她受盡壓迫的故事,克雷科在公司發售的「抗老藥」中,加入了自製的基因改造病毒,計劃淘汰舊人類,讓完美善良的「克雷科人」接管地球。
最終,克雷科的計謀成功,他與奧麗克絲相繼死亡,而他製作的瘟疫也瞬間蔓延世界,人類以極短的時間滅亡,遺下吉米和「克雷科人」面對這蒼白的新世界。在這新世界中,吉米也許不時會憶起自己以往曾對舊世界作過的反思和批判?
「人類社會,屍體,還有瓦礫。人類永遠不會學習,總是一次又一次犯下同樣的嚴重錯失,以短期利益換取長期痛苦。就像一隻巨大的蛞蝓,永無休止地吞食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形式,輾碎地球上的生命,然後從屁股中拉出一片片大量製造但又即將廢棄的塑膠垃圾。」
《末世男女》明顯是部「反烏托邦」小說,呈現了生物科學和基因工程有機會引致的悲劇世界。然而,帶來毀滅的,其實不是科技,而是人心。本來表面科技進步、物質豐裕的社會,其實早就千瘡百孔,貧富懸殊,極多醜惡不道德的勾當進行卻不得解決。那麼,在克雷科散播病毒前,世界這齣大悲劇,不是早就有自我毀滅的傾向嗎?

從《十日談》,到《瘟疫》、《盲目》,再到《末世男女》,都見疫症在人類歷史又或未來命途上都佔一不可忽視的位置。但這些文學作品的作者,以「疫症」作為大題寫作的動機,卻是總關於當下的。他們藉作品提醒人們注視個人和集體當前的世界現實,進而思考生命的抉擇,人作為人的缺憾,官僚體制的迂腐僵化,科技的致命力量,還有人類未來的可能性等大哉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