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月來,香港人度過不少無眠夜,其中包括7月21日這一夜。
當晚,元朗西鐵站大堂充斥着叫囂聲,不少元朗人在歸家路上,遭遇大批白衣人無差別襲擊,有人被藤條打至背部傷痕纍纍,或被拳打腳踢至頭破血流及暈倒,約四十多人受傷,期間更未有警方到場執法,有短片拍到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和白衣人握手道謝。
兩天後,何君堯稱在屯門的家墳遭到破壞,並指事件屬立法會議員朱凱廸的追隨者所為,要求朱凱廸選擇「生路」及「不生路」。 隨後朱凱廸公開表示,何君堯不是一個人,是一個現象,背後是有人想在香港發展「義和團暴民政治」的陰謀。
其後,在北角、荃灣、將軍澳等區,接連有不明來歷的人以棍、鐵通甚至刀襲擊途人。「五年前,佔旺現場有黑勢力入侵,已預示親建制的激進派試圖訴諸暴力,到今天,規模變得更大,恐懼瀰漫得更普遍。」朱凱廸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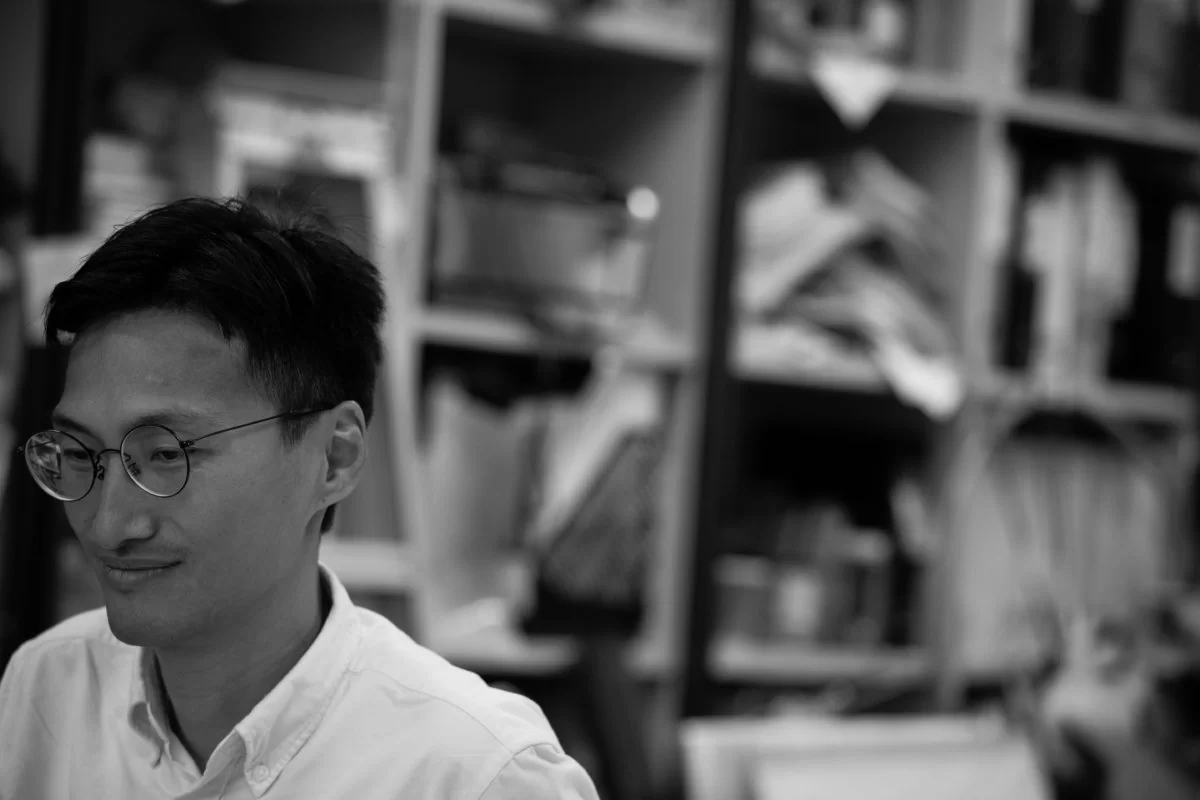
7.21後,朱凱廸收到多個死亡威脅信息,包括江湖上已發出「暗花」,要捉拿朱凱廸的助手;此外,也有相熟的鄉事人士和政府人士告誡他,有暗花尋找一個身患絕症的人暗殺他。由於感到自己及團隊的人身安全受威脅,他曾到警署報案,要求警方徹查事件。
事態發展之今,情況如何?「(警方)沒有說具體捉到一個人是跟蹤我。」朱凱廸說。
⚡ 文章目錄
兩次遭受死亡威脅
這是他第二次感受到嚴峻的死亡威脅,上一次是2016年。
當時傘後的民主運動經歷一輪低潮期,隨着立法會選舉而出現轉捩點,扎根元朗八鄉的朱凱廸以獨立身份參選,將他長期關注的土地議題如「反官商鄉黑」、「城鄉共生」、「復興農耕」等帶入主流視野,並以「票王」之姿當選新界西議員。當選的一刻,他禁不住在鏡頭前流下男兒淚,坦言參選以來,知道因為提出「官商鄉黑」勾結的議題惹怒了不少人,令自己和家人受到人身安全威脅,經歷好幾個禮拜無以為家的日子。
他後來公開表示,在選舉過程中多次被人跟蹤和恐嚇。兩星期後,警察在八鄉、荃灣等地以涉嫌恐嚇罪名拘捕六名男子。他當時表示樂見警方執法,但「背後操控恐嚇者、包庇『官商鄉黑』勾結的權力仍然控制着香港政治發展及港人生活」。
「那一次,起碼查到車牌的牌主,知道是怎樣跟蹤。今次,警方沒有調查出什麼,似乎變成『無頭公案』。」至於元朗襲擊一案,截至8月21日,警方以涉嫌非法集結拘捕廿八人,其中兩人在事發一個月後被控參與暴動;9月3日,元朗區議會曾合併討論事件,其中有議員動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惟遭過半數議員反對。
「7.21之後,很少一個人在街上走,每次吃飯都去特定的地方,吃飯的選擇少了很多。」他說,8月某一天,他的地區辦事處曾有一羣來意不善的人想強行闖進,幸而辦事處位處唐二樓,下面隔着一道鐵閘,職員下樓「頂住」要衝進來的人。
「這件事,我已告訴了調查案件的警員,提供了照片,但我估計最後都是不了了之。其實,好些議員辦事處都被人淋過紅漆、遭到破壞,或被抹上糞便……在香港,即使有人擅闖一個地方,拿棍砸壞了所有東西,無法辨認他的樣貌的話,(警方)都不會有什麼行動。」
他說,不少泛民議員都受到類似恐嚇,例如被起底,家人的背景、電話被上載到網站,隨後會不斷收到騷擾電話,有些向你說粗口,有一些以程式撥打你的電話以致電話無法正常運作。此外,亦有不明來歷的臉書帳戶,會突然傳來你的車輛照片和車牌號碼,暗示他們知道你的行蹤。
近期好幾名立法會議員已經遭受襲擊或被捕,朱凱廸暫時「無事」。「因為這樣,許多人還說我是『鬼』,我在這位置,其實做了被捕準備,(政權)不拘捕你或DQ你,沒有人知道原因。其實也不用擔心,現在被捕,很正常,結果不過是坐監,香港監獄未至於有酷刑,懲教署會保護你,不會讓黑社會在監獄裏殺掉你。相對來說,在巴西坐監可能會被殺,在大陸坐完監出來,可能整個人都已崩潰了。」
「香港和大陸唯一差別是監獄」
「被黑社會襲擊,或者被一些不明人士無差別襲擊,其實更糟糕;假如真的在警署被酷刑,可能也沒有追究的方法。」朱凱廸對現狀悲觀,對他來說,政權很容易可以摧毀一支警隊,「現在香港和大陸的唯一差別,就是監獄裏的處境。」他認為懲教署維持不腐敗十分重要。
7.21之後,他提高了警戒,因不能確定迎面而來的人是善意或惡意。「香港目前出現比較對立的情況,作為一個容易被辨認的人,我不知道怎樣自處。」他甚至在困惑,應該正視面前的人,還是索性不看別人,他也不知道應該給陌生人一個怎樣的表情。

他遭遇的情形大概如下:街頭有人要求跟他合照,街尾有人用粗言穢語罵他。以前溝通無礙的選民,突然有一天在他的通訊羣組留言:「我覺得你是一個好人,但是,不知道你原來是一個大漢奸!」
反修例運動之前,他與泛民議員於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委員會會議上發動議會抗爭,及後在運動的警民衝突現場出現,希望能擔當緩衝的角色,隨後與黃之鋒到台灣分享香港的情況。「有些人覺得我變了,他們本來同意我對環境運動的看法,同意我對於新界鄉事和黑社會糾纏不清的批判,甚至同意香港民主化、民主自決,但看到我和黃之鋒去台灣,就會觸動了他們另一根神經線,發現我原來跟黃之鋒『連結了』,他們的迷茫,類似一個在美國的共和黨人,反墮胎,支持槍械合法,但有一天他突然反對石油企業,突然關注全球暖化,那些共和黨世界裏面的人就會覺得這個共和黨人很奇怪。」
新的民主運動 無人能預期
他說自己沒有辦法選擇,因為香港處在危急關頭,如果這些人不理解,他也想盡量和他們溝通,正在革命中,可是,「我也很疲累了。」
雖然有不支持反修例運動的人,但朱凱廸認為大部分市民其實有着一定共識,例如8月中大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十五的市民認為五大訴求應該落實。「餘下百分之二十幾的人,會覺得很委屈,好像被邊緣化,不過就算『谷住道氣』,他們也不敢大聲地罵,因為擔心可能會被十多人圍着。」
五年前的雨傘運動,朱凱廸早在罷課時期曾連同一些學生領袖籌劃運動,他的組織土地正義聯盟亦有到過佔旺現場。他認為,當年的運動是基於人大8.31決定,在一開始已是個死局,到最後亦釀成了巨大的消耗,政治運動出現長期的低潮。「我記得17及18年,整個氣氛都是『挨打』的,即使是我這些死硬派頂住,但部分議員已被DQ了,去到後來一段時間,有些人逃避看新聞,有年輕人北上深圳消費,喜茶有很多人排隊,抖音開始流行,小學生又說普通話,整個情況給人的感覺就是,香港玩完了,不過你『頂多一陣啦』。戴耀廷說,民主運動已變成反威權運動,進入”Defensive Mode”。」

今年6月發生的事,改變了一切。一連串運動,事前沒有人能預期,雖然有人一早言明,2014年是香港民主運動第一波,將來必然有續集,但是,過去三個月,無論是運動的方式,以至牽連的事件,都不是事先能預料得到的。朱凱廸認為,2014年之後,大家都覺得民主需要深化,需要去處理地區或區議會,可是慢慢有些項目半途而廢,只餘下「維修香港」和「土家」等;到今次,動員方式,用了Telegram和social media等新的連結方法,那已經超出了傘後大家想像的模式。
「相對如雨傘的定點運動,今次變相是十八個地區由頭到尾都在『捲』,除了離島之外,大家對運動都有更貼身的經歷,將來會引發一些什麼更深化的政治能量或模式,會激發什麼地區參政人士,值得我們期待。」
「朱凱廸」成了假新聞關鍵詞
朱凱廸認為,反修例運動之後,值得關注市民如何重新審視一些體制,包括是否覺得需要參加區議會選舉和投票,「因為不能夠只是在街頭上打贏,如果贏了區議會過半數,可能會有特首選舉一百一十七席,那下次特首選舉,影響也可能會大一點,譬如2018年很多人都不太想投票的,兩次九龍西的普選投票率都很低,因此就輸了。」
他亦同時思考自己在體制內的角色,他一直做的,是建立一些政治運動的基礎條件,換言之,除了當下,他更多的是考慮未來。「當在前線都沒有你的工作,大家就得找能夠做的事情,或者提早預備未來的工作,譬如區議會選舉,有些新人去選,就去幫一幫忙。」

關於地區選舉,去年年底朱凱廸參與過一次,但那次報名參選村代表選舉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儘管坊間有說法,朱凱廸再參選,可能會被取消資格,但年底前的區議會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他亦在考慮之中。「他們可能都會按照那次的說法來DQ我,但我還是想參選的。」他估計未來變化可能很大,相對他八年前參選區議會時只有一兩個泛民參選鄉郊地區,他相信這次可能會出現數十人參選的情形。
他說,就算自己最終無法參選,他都能透過支援其他人參選,去做表述,那是關於地方自主的,也是關於環境問題的,同時是關於香港鄉村未來的思考。「當處身於一個翻天覆地的時候,所有事情都袒露了出來的時候,其實什麼意識都可以成為主流,因為那是在運動過程之中塑造出來的。」實踐的人多了,思考的人多了,對他來說,是比他一個人奮鬥更有意思的事。
他說自己不會花時間擔心再次被DQ。「對我來說,更大的麻煩在於,我沒有辦法回到一個比較輕鬆的狀況下,去創造這些可能性。」利用「朱凱廸」三個字去創造假新聞,他這個月見識了不少。他說,譬如元朗襲擊事件中,社團領袖就以假消息通傳社團成員,他和鄺俊宇會在7月21日帶幾百人去元朗搞事,又譬如近期又有傳聞,說他會在某個日子走去南丫島、坪洲和長洲「搞搞震」。
「我估計是有些鄉事的人或親北京的人,覺得我是一個可以使用的符號,結果我出現在某一個地方,就會產生一種對立。譬如說,本來我在這鄉村問題方面,算是比較了解新界原居民想法的,但現在用了『朱凱廸星期六來南丫島搞事』這句話,就把我標籤成代表激進的人,導致我本來可以發揮的作用不再存在。」
他說,他的團隊向來喜歡到各區作長時間的溝通,或舉行一些輕鬆的討論會,但始自7.21元朗襲擊案後,就困難重重,「大家叫我不要來。」
世界可能只剩下十年
他說,他本來有很多地區工作正在進行中,但感到自己的政治主張,在某些場合被人放大了,就是所謂「符號化」了。「你去台灣,就被誤讀為『獨立』,你入村就是要拆祠堂,這些都是『符號化』,我想,不同人可能在不同範疇都面對這些『扯開』自己的問題。我還有一年任期,我可以怎樣做呢?由農業、鄉村發展到減廢永續能源的問題,怎樣去帶起這些議題呢?這是我現在的苦惱,我是很悲觀的,我覺得世界在十年之後處境很嚴峻,可能會玩完,即是環境玩完,所以那首《願榮光歸香港》,說自由民主是萬世的,但我說,其實是沒有萬世的,可能只剩下十年。」
在他心目中,每件事都迫在眉睫。說回黑勢力襲擊問題,他說是自上屆特首上任後,香港情況出現了變化,9.28時佔旺現場有黑社會滋擾,只是小規模,今天問題彰顯得很大,形成一個大家都意識和感受得到的白色恐怖。「那個難解的地方,就是它(黑勢力)不是公權力,所以如果香港好像哥倫比亞一樣被毒販控制了,連總統都要感到害怕,總統候選人都要和毒販談判,之後才可以選總統,那你是一個很被動的處境。你不能說,我們現在很勇武,然後弄什麼民兵就不害怕他們。」他認為黑勢力襲擊這個問題要有公權力去制衡,需要有警察,如果警察不理會,反而助長黑勢力,局面就會難以收拾。

他認為,無論是國泰裁員事件、元朗7.21事件,又或是人臉辨識監控系統,其實都預告着香港未來踏進極權式管治的手法。「所以,無法『收科』,即不單是五大訴求這麼簡單,如果你不能勝過我,你就用這些手段來整我,我沒有辦法,我打不過那些職業上負責打人的人。如果周圍都是燈柱,周圍都是那些監控鏡頭,每個人都告發每個人,沒有人受得了。」
他表示,這些現象發展下去十分恐怖,香港人現在能做的,是用運動的力量去制止這些發生,所以香港人已經沒有退路。雖然飽受假新聞困擾,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覺得整個世界都危在旦夕,但在這場運動中,他不贊成「回去做實事」的說法,因為這場運動的成敗,決定了所有人的命運,輸了,不是他一個人輸了,而是所有人都面臨極權管治的威脅,所有人都會輸得徹徹底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