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日本現代文學的開山祖師,森鷗外和夏目漱石常常被相提並論,除了因為兩人先後留學西洋,也因為他們都熟悉而且深愛漢文學。同時精於東西洋文學,令他們不約而同對萌芽中的日本現代文學的抱有批判和懷疑的態度。不過,鷗外和漱石的根本差異,卻可以從他們的留學經驗中看出。兩人的眼中的西方,是兩個西方。
生於一八六二年的鷗外比漱石年長五歲,未夠二十歲便自東京大學醫學部畢業,隨即加入陸軍成為軍醫。一八八四年赴德國留學,專修衞生學,四年後回國,並發表處女作〈舞姬〉等以留歐經驗為背景的浪漫主義小說。鷗外成名之時,漱石才剛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系就讀。漱石畢業後曾到南部鄉下當中學教師,一九○○年奉派公費赴英留學。留英兩年因精神問題被召回國,在帝國大學教授英國文學,到了一九○五年發表《我是貓》聲名大噪。距離鷗外初試啼聲,已經是十五年之後。表面看漱石好像是鷗外的後輩,只是因為前者的起步點落後很多。
漱石在大學修讀英國文學之初,便發現它和自幼喜愛的漢文學差異極大,有「被英國文學所欺騙」的感覺,認為兩者所指的「文學」是不同的事情。他不情願地奉派來到英國之後,對當地生活習慣感到格格不入,在大學裏聽課也無甚所得,大部分時間閉門在家,埋頭苦讀。他在《文學論》的序言裏談及自己留英兩年的經驗,直接以「不愉快」來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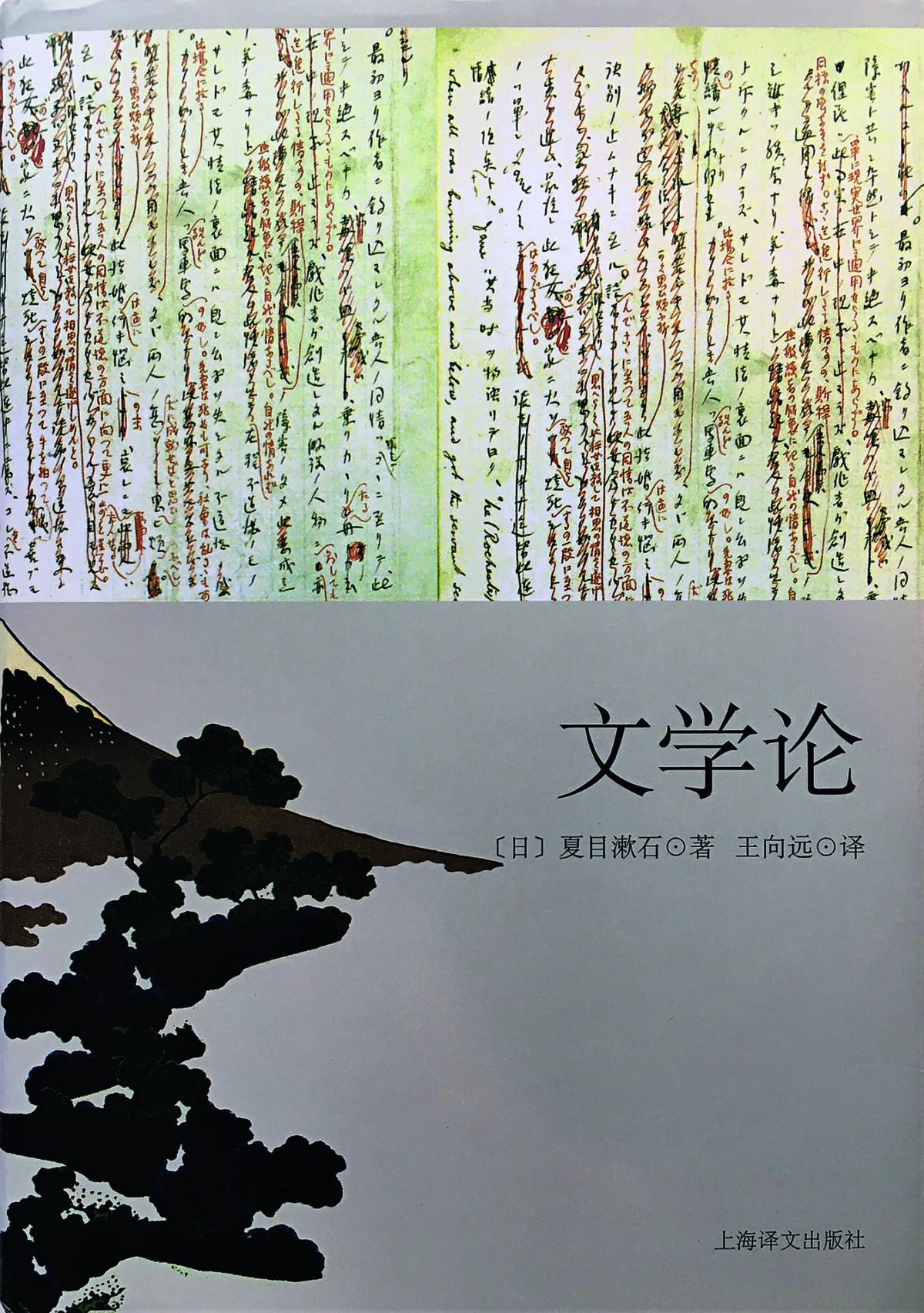
「我在英國紳士之間,猶如一匹與狼羣為伍的尨犬,終日鬱鬱寡歡。據說倫敦人口有五百多萬,自己當時的狀態猶如摻和進五百萬滴油珠中的一滴水,勉勉強強苟且維繫着朝不保夕的生命。假若一滴墨汁掉落在洗得十分乾淨的白襯衫上面,襯衫主人的心情定然不會愉快。我就如同那滴招人厭煩的墨汁,猶如乞丐一般徘徊在倫敦的西斯敏斯特大街上,兩年間吐了這個大都會幾千立方尺人工造成的充滿煤煙污染的渾濁空氣,為此而感到深深愧欠於英國的紳士們。若依我自己的主觀意志而言,我當終生一步也不踏上英國的土地。」
漱石對英國的厭惡,可謂溢於言表,但這並不表示他很「愛國」,以為回到日本便可以尋回快樂和幸福。他表示回國之後,又是不愉快的三年,但身為日本的臣民,他不能因不愉快而離去。「在我意志之上的意志命令我,為支持作為日本臣民的榮耀和權利,必須避免一切不愉快。」國家意志對臣民自由意志的壓抑,不言而喻。如此比較,甚至比置身異國更無反抗的餘地,也即是連「不愉快」的權利也沒有。似是罵了英國,實則批評了日本。漱石的深層諷刺之力,在此可見一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漱石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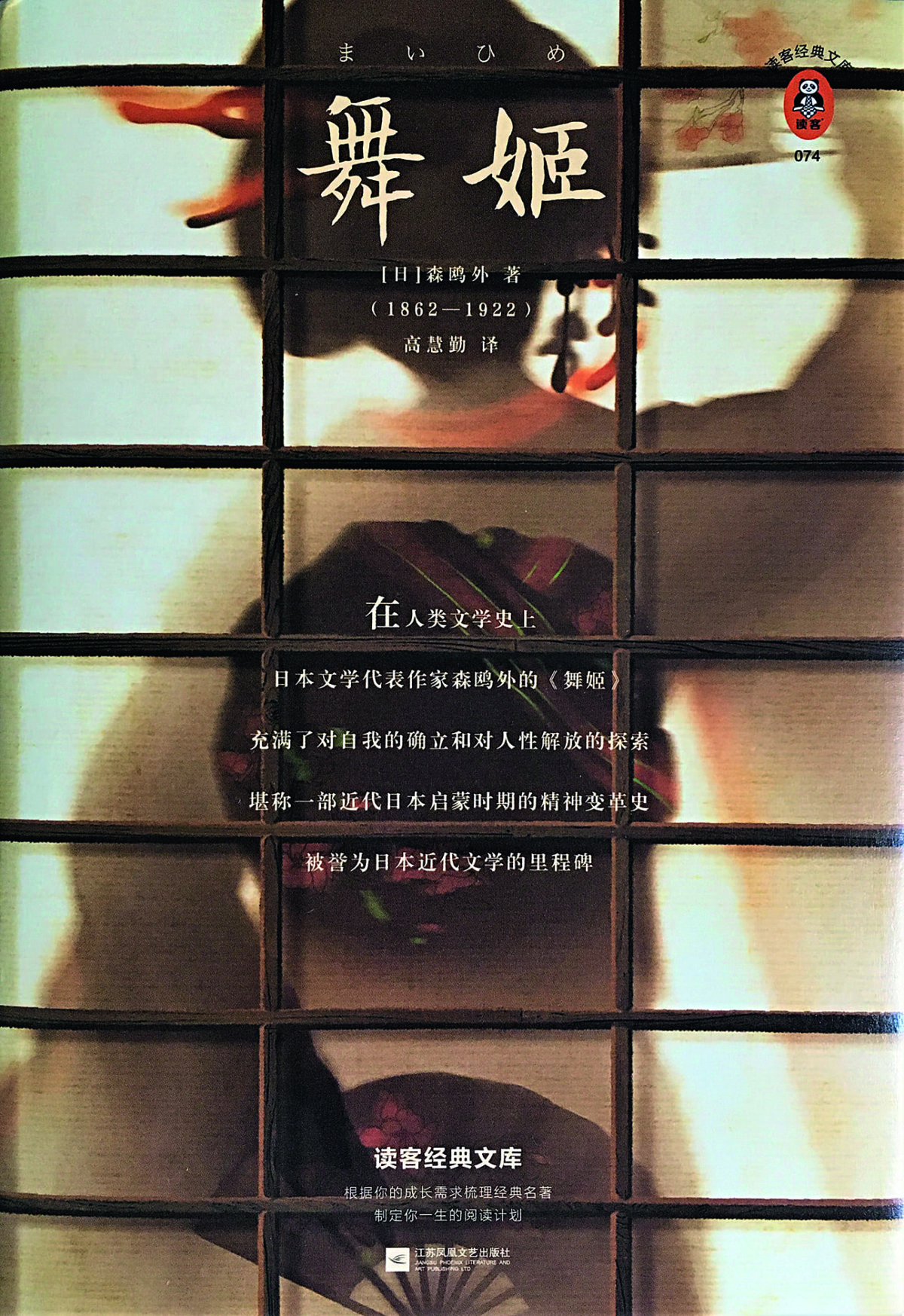
和漱石的引發了神經衰弱和癲狂症的留學生涯相比,鷗外的德國經驗可說是相當愉快。從他的成名作「留德三部曲」,也即是〈舞姬〉、〈泡沫記〉和〈信使〉三個短篇,可以看出他對於歐洲生活適應無間,遊刃有餘。三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是留學德國的日本青年,分別是法學生、畫家和軍人,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令人驚訝的是,當中完全不見任何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衝擊的痕跡。小說中的日本人不但外語流利,與西方人完全無礙地交流,在態度上也非常自信,就算與當地貴族交往也沒有自愧不如。歐洲人對待日本人也看不出任何隔膜,不但沒有歧視,甚至還好像對待本國人一樣友好。不是說鷗外表現了世界大同、種族平等的思想,而是說,在這批少作中,文化分歧和國族差異完全沒有成為焦點,好像根本不存在這回事一樣。
對明治中期剛接觸西方文學的讀者來說,鷗外小說的最大震撼不只是當中的西方背景和異國情調,而是日本男性輕易地贏得西方女性的愛情與信任。在〈舞姬〉中,留學生豐太郎拯救了貧困的舞女愛麗絲,兩人墮入愛河,最終男方卻因為事業前途而決定歸國,忍痛拋棄了為他懷有身孕的愛人。據說鷗外回國之後,曾有稱為愛麗絲的德國女子隻身坐船來到東京求見,但卻遭到鷗外拒絕,由家人出面打發離開。無論是否作者親身經歷,這個故事的意義在於日本人竟然一下子便跳過了東西文化的鴻溝,獲取了主動性和主體性,扮演上西方浪漫主義小說的主角。在〈泡沫記〉中,日本畫家巨勢幫助了賣花女孩瑪麗,幾年後成為模特兒的瑪麗與巨勢重逢,雙方互相吸引,把臂同遊,最後卻遭到意外的悲劇結局。在〈信使〉中,年輕日本軍官和德國貴族女子伊達之間雖然沒有發生戀愛,但後者卻深深信任前者,並藉着他的幫助尋求自己人生的解放。在三個故事中,日本男性都是西方女性的幫助者。雖然在〈舞姬〉中他同時也是辜負者,但也只有強者才能辜負,而被辜負的則是弱者。這跟東西方在現實中的強弱關係,完全是一種倒置。
縱使虛構小說未必代表日本留學生的實況,浪漫主義的形式亦左右了小說的表現方法,但留學生活對鷗外的正面作用是明顯不過的。歸國後鷗外的仕途一帆風順,逐步晉升至陸軍軍醫總監、陸軍省醫務局長。自陸軍退役後,又歷任宮內省帝室博物館總長和帝國美術院院長等文職。與之相反,夏目漱石終身和權力保持距離。他決定加入《朝日新聞》成為專業作家之後,辭去大學教職,後來又拒絕國家頒發的博士頭銜。同樣的榮譽,鷗外卻欣然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