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字發作】一個接受過極嚴格中國武術訓練、周遊列國和外太空、經歷了許多怪事、很多次險死還生、改變了香港很多人腦電波的人,六十年前第一次為人認識。
如果日曆上沒有這個日子——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衛斯理先生就不會出現在我們的太陽系。六十年前,衛斯理先生大名首次出現,當時《明報》的頭版闢了個宣傳欄,這樣寫道:「衛斯理先生是一個足跡踏遍全球的旅行家,又是一個深諳武術的名家。」
許多年後,衛斯理離開了地球,到了宇宙其他地方探險。
留下的是他離奇古怪的經歷,化成了衛斯理小說。
許多情節可能都忘了。衛斯理失蹤六年(無名髮)、因全身燒傷而毀容(藍血人)、頭顱被切下來(換頭記)、成了瘋子(沉船)、變了白骨(透明光)……這些奇特至極的怪事,是外星人作祟也好,是某個地球人胡思亂想也罷,已經不再重要。
我們只是記得,有一個講故事的衛先生,言必「受過極嚴格中國武術訓練」,經常「大跳起來」、「聳了聳肩」、「冷冷地說」、「揮了揮手」和「倒抽一口涼氣」,遇到的東西,常常「不是地球上的東西」,遇到的人類表情,不是「瞪大了眼睛」就是「詭異絕倫」。
六十年,回看衛斯理,赫然發現,第一篇,一個人告別了鑽石,丟落大海,最後一篇,另一個人連同他的家人,離開了地球,走向宇宙。勾起的記憶,不是埃及的黃銅箱子,不是西藏的神秘金球,不是在四處走動的人體殘肢,不是藍色血液的外星生物,不是恍如ChatGPT談戀愛的痴情電腦筆友,而是只限老友的音容宛在,而是冥冥中自有主宰的「陡然」和「毀滅」。


以下附上衛斯理小說連載的第一篇全文和當年的《明報》版面:
一:將鑽石拋入海的人
(鑽石花 衛斯理著 雲君插圖)
這是一個隆冬的天氣,香港雖然不會冷到滴水成冰,但是在海面上,西北風吹了上來,卻也不怎麼好受,所以,在一艘港澳輪的甲板上,顯得十分冷清。那天晚上,又是一點月光也沒有,黑沉沉的天上,只有幾顆亮晶晶的星星。
我因為生性喜靜,這天晚上,我又穿着一件厚厚的大衣,可以不畏凜烈的西北風,我在甲板上踽踽地踱着,倒感到這樣的境界另有一番況味。
正當我以為是獨自一個人在甲板上的時候,忽然聽得「嗤」地一聲,我立即循聲望去,只覺在欄杆上,另有一個人倚着,望着海面,那「嗤」的一聲,正是從他那裏所發出來的。
我心中感到十分奇怪,因為剛才那一聲,曾經學過中國武術的人,都可以聽得出,那是以極強的指力,彈出一件東西的聲音,也就是如今一般武俠小說中所說的「暗器嘶空」之聲。
因此我停住了腳步,點着了一支烟,在點火的時候,我偷偷地抬起頭來仔細打量那個人。
只見他左手一隻布袋,右手伸入布袋之中,拈出一粒小小東西來,向海中一揚,「嗤」地一聲,那粒東西,便跌入了海中,濺起的水花並不高,那東西已然跌進了海水中。
在那粒東西劃空而過的時候,我看到那粒東西,發出一絲亮晶晶的閃光。
那一定是無聊的人,在將玻璃珠子拋向海中,以消遣時間,我想。
與其一個人在甲板上閒踱,何不走過去和他搭訕幾句?我又想。因為每一個人,如果你能夠設法打開他心扉的話,你就一定可以聽得到一個極其動人的故事,不論那人是行動之間太過揉的貴族,還是過着原始生活的土人。這是我的經驗,所以,我輕輕地來到了他的身邊。
那一個人,像是全然未曾發覺我在向他走近去一樣,仍然是望着黑漆漆的海面,機械地將那袋中的東西,一粒一粒地拋入海中。直到我來到了他身邊,只有四五尺遠近處,他才猛地回過頭來。
我和他打了一個照面,天色雖然黑暗,但是就着遠處射過來的燈光,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得清他的臉面,他是一個三十歲不到的年輕人,面上雖然有着一種憂傷得過份的神氣,但是卻仍然可以看出,他本來是一個極其英武剛毅的人,大約因為他所受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所以臉上才會現出這樣的神氣來。
他冷冷地望了我一眼,眼色是如此之冷峻,然後,簡單地道:「走開。」我並沒有聽從他命令式的吩咐,只是停住了腳步,不再前進。
「走開!」他第二次冷冷地叱着。我向他作了一個不明所以的神情,他忽然冷笑了幾聲,轉過身去,又重複那機械的動作。
我在他身旁站了好一會。他一直沒有變化他的動作,繼續地將那些小粒東西,拋入海中,我也不斷注視着他目不稍瞬。在附近的一個船艙的窗中,突然亮起了那燈光,當燈光映了出來之際,我已經陡地看清,他拈在手中的,竟是一粒足有十五克拉大小的鑽石!(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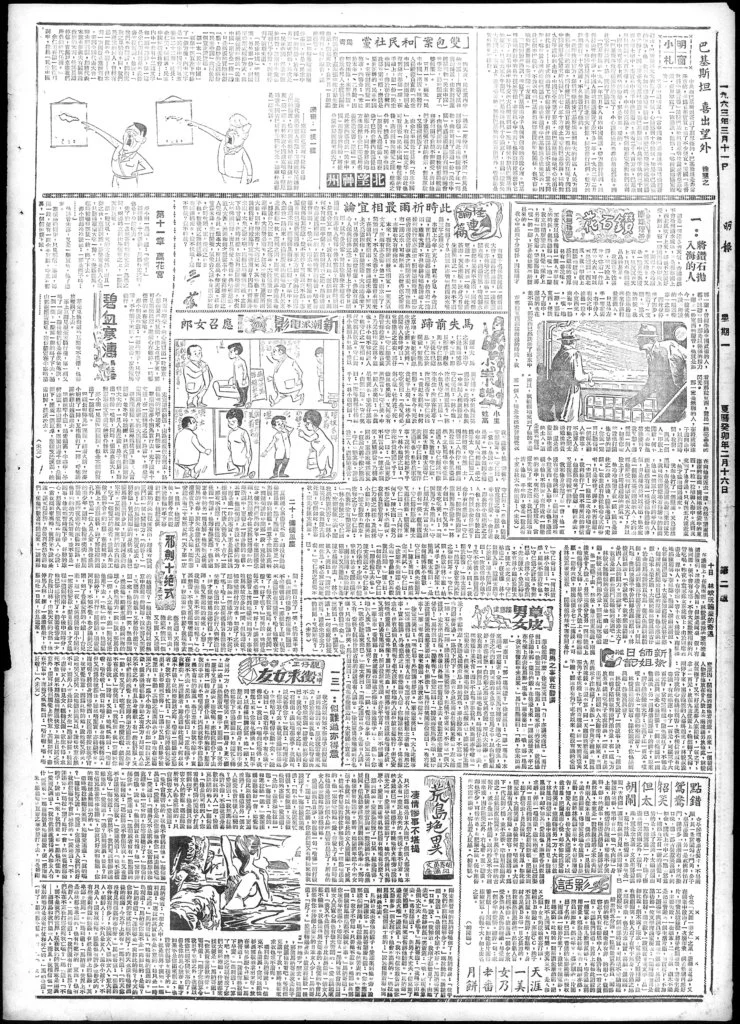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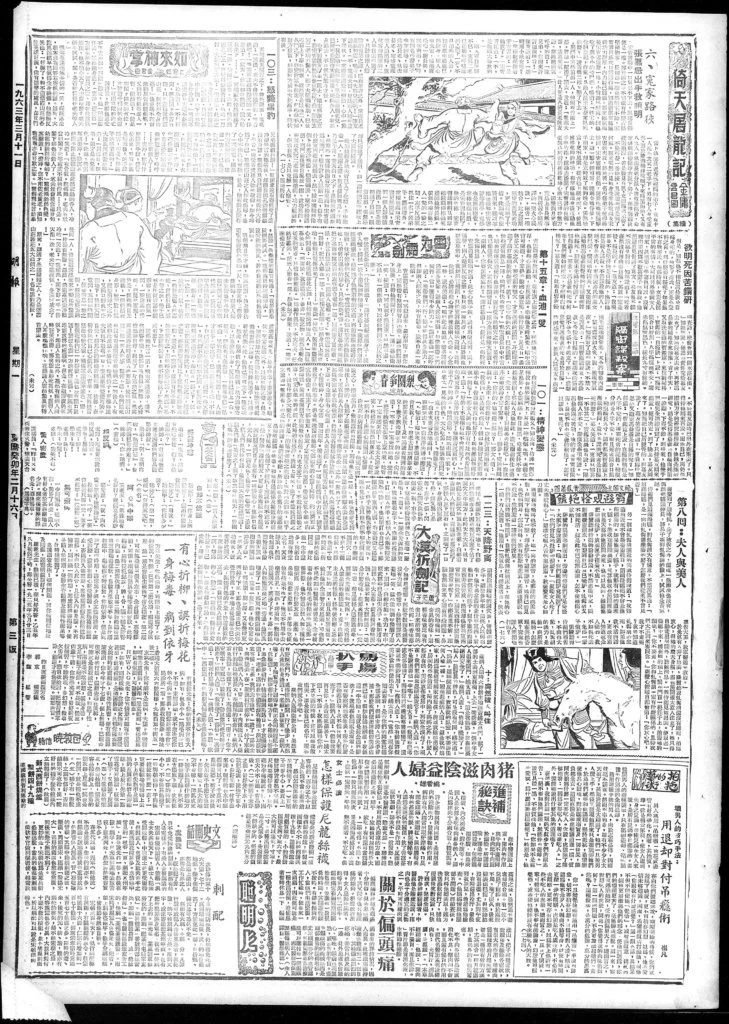

(按:《鑽石花》的單行本,進行了若干改動,包括一些詞語改動,例如凜烈改為凜冽,況味改為滋味,吩咐改為說話,又刪去一些冗字,如第六段刪去「,那東西已然跌進了海水中」,第十段第一句改成「那人像是全然未曾發覺我在向他走近」,最後一段第二句改為「他一直將那些小粒東西拋入海中,我也不斷注視着他」等等。除了文句改動,最明顯的改動,是把文中的香港改成亞熱帶,又把港澳輪改成遠程渡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