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旁分鬈曲棕色短髮,一身闊衫寬褲,配上丸山正宏的雙橋圓框眼鏡,鏡框保留着不規則線條,鼻托扭曲成黑白兩色。要在中大芸芸頹T和樸實衞衣中認出余俊良,着實不難。
中大心理學系麥穎思教授也有相同品牌的眼鏡,平頭的她未患癌症時,喜歡以大波浪短曲髮示人。
有人說過你們兩師徒很像嗎?她蹙眉:「他認識我後才換眼鏡和電髮,誰知道他有沒有抄我?」余俊良立刻放下夾着叉燒的筷子,瞪眼反駁:「點抄呀!難道把你的相片交給髮型師,說要電成這樣嗎?」故作沒好氣狀,卻一秒破功:「不過,是的,我們真的很相似,她對我的影響簡直是由外到內。」二人八眼相視,指着對方後仰大笑。
平日兩師生聚頭,若不是談論研究論文,就是這般你一言我一語,不着邊際。這次難得圍坐小圓枱,與學士畢業論文導師、碩士教授、研究室戰友兼時裝顧問互吐心事,余俊良感覺到,自己許多細微處都被欣賞,又發現自己像眼鏡一樣沒被磨去稜角,卻在不知不覺間蛻變重生。

一個飯局 生命改變生命
傳說兩個人相處久了,自然長得愈來愈像。心理學也有個「變色龍效應」,指愈親近的人,愈容易無意識地模仿對方。這對師生,大概是先模仿後親近,連他們的友人也在余俊良的臉書頭像下留言,戲稱是「Winnie’s Lab外觀同化現象」。
所謂”Winnie’s Lab”,其實是由麥穎思成立的「多元文化及全人健康研究室」。余俊良五年前入讀中大,已在這裏幫忙,直到麥穎思成為他的畢業論文導師,兩人才開始熟絡。有次,麥穎思戴了一副丸山正宏的寶藍色眼鏡,鏡框恰似手繪的原始線條,左下框鍍金,右邊則缺了一角。對於當時一頭直髮、架上最平凡的那種黑框眼鏡的他來說,那是如此的驚豔:原來眼鏡可以這樣──這樣不規則,這樣不對稱,這樣不完整,卻這樣美。
從由副學士升上中大後,生活彷彿只剩讀書和考試,他一直想在千篇一律的規律中找新意,壓力大得想換掉整副軀殼和靈魂。眼鏡衝破了他對裝扮的想像,也打開了兩人的互通處。十幾年來,他總被罵不讀書、懶散、蠢蛋;忽然跳進中大,就被認定要學業優秀,但他自知沒有做研究的入場券。他不明白,明明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為何總被貼滿不符現實的標籤,為何一定要達標,為何不能脆弱。在這大男孩身上,麥穎思看到自己以前的影子。她憶起,自己在大學的啟蒙老師Dr. Stanley Sue當時獲獎無數,高高在上,也很用心聆聽那個沒自信又不說話、患有抑鬱焦慮症的她。
三年前某夜,她帶余俊良去了個私人飯局,席上是她很親密的外國教授。頭一回用英語跟陌生人聊天,他在餐廳裏不住搓揉雙手,撥弄頭髮,結結巴巴地吐出零散詞語,但兩雙專注的眼眸,陪他從錯誤中一步步學習,讓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溫暖和鼓勵。這天,已是研究助理的他翻開當年寫的感謝卡,裏面寫了句”That night really meant a lot to me”。

Profile
麥穎思,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學系、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臨牀心理學博士,現職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教授,「說書人」的共同創辦人,相信教育是要播種、苦心經營,等待發芽。
余俊良,曾就讀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副學士(心理學)、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哲學碩士,現職研究助理。
麥穎思=麥/余俊良=余
在台上俯瞰黑壓壓的羣眾,他們不怕;聚會時碰撞到新想法,雙眼發光。別看師生演說經驗豐富,背後其實是緊張大師,臉上謙和,內心翻湧。這次輕鬆對談,麥穎思也時而緊握拳頭,時而換手托腮。
麥:我也是很緊張的人,所以我很能包容緊張焦慮的狀態。
余:我就是個緊張的合成體,走出來就很焦慮,很多事不敢做。每個行為前,都會有一堆焦慮;每次說話前,都要在腦裏演練一遍,最後說不出話來。

我們都是容易緊張的人
麥:這方面你很像我小時候,因為我大學時焦慮到一個點,比你嚴重十萬倍。我當時患有抑鬱焦慮症,誇張得不說話。可能會亂想無限次才說出來,但還是說得結巴,最後什麼都沒說。為何我這麼印象深刻呢?因為你本性緊張,但每次做匯報,在會議上演說時,會感覺到那股自信,會覺得你好像在教書,聽得出你很熟悉內容。
余:哪來的自信?哈哈!
麥:兜個圈讚自己先,這有點相似,我平時不大說話,現在訪問就得說話。如果要匯報或去講座,我不夠膽說是上身,但感覺很有自信,看到大家認同的事,就會雀躍地跟觀眾分享。
余:等待時永遠最緊張,但走出來後,已練習到腦袋基本上不用運作。整個人很專注,就能侃侃而談。以前準備時我還是會緊張,那股緊張是,覺得自己不夠時間練習,會緊張到嘔,那真是嘔的感覺,但我未嘔過。
我很願意分享這方面。我緊張時,會先告訴別人,所以我緊張的時刻,你都數得到,如果你記得的話。當我狀態很差,失眠,說話時口顫,我就會說不想去。
麥:即使靜止的時候,我也會緊張,很明顯的。例如你會觀察到我就算坐着也握緊拳頭,整個人本來就很易緊張。但我不介意告訴別人,因為我做反歧視的工作,反污名,難道自己都不說?
焦慮是我的老朋友,間中就會找我。透過焦慮,我了解自己很多,亦因為焦慮,我變成今天的我。我很怕別人怎看我,怕會出糗,怕做得不夠好,加上完美主義和自我批判,變相會預先計劃,做事永遠會思考很多步。其實很多人有焦慮症,很普遍,毋須煞有介事說誰黐線誰精神病。長期處於抑鬱焦慮,這反而幫我做到現在做的事,令我更有動力反污名,不斷做這方面的研究和社區工作。有時這是blessing in disguise(因禍得福),如果沒這經歷,我只是個會讀書的人,也不知會否做教授,可能不知自己做什麼,變成一個沒有目標的人。
小時候舉家移民美國,遇過歧視,純粹因為膚色。又眼見其他人因為是難民,或因為稍胖而被歧視。我不斷思考,為何一個人純粹因為自己的特徵和身份,就被污名化或歧視呢?這事一直藏在心裏,我從中學已經喜歡心理學,理所當然地在大學修讀心理學,最主要是想了解自己。
余:我從副學士開始已經讀心理學,但踏入心理學的第一步,跟你完全不同。原因是我原本想讀的社工沒學位,於是要從社科院裏選擇。社科院只有三科:體育、社工和心理學。不是要我選體育吧?之後有重新選擇的機會,就是副學士畢業時,可選社工或心理學。我在副學士的那兩年,像你一樣有很嚴重的抑鬱焦慮。在這情況下,我更了解自己是個怎樣的人。第一,我非常不想接觸人,至少未必想頻密地主動接觸;第二,我對心理學真的很有興趣;第三,因為我抑鬱焦慮,有導師叫我試試冥想,那時未流行靜觀這個詞語。那時我廿四小時都被焦慮霸佔,睡不着覺,甚至只能開眼睡覺。我試着花十分鐘騰空自己,結果真的有用。這段時間我更清楚,研究心理學比起了解社會政策和做輔導,更接近我真正想做的。
「你們年輕時會覺得很樣衰,要很快做到某些事情;我們這些上年紀的人,回頭一望,多半年時間其實沒大不了,無人會記得你講錯說話或出醜,真的沒有人會記得,但這些點滴會累積成自信,令你做到更多。」——麥穎思
老師的癌症和她的頭形
(麥穎思鮮豔多元:除了鮮紅冷帽,她家衣櫃還藏着花恤衫、撞色拼布上衣,以及不同圖案的襪子。余俊良一身素色:他的衣著隨心情改變。麥穎思說:「無論開心或不開心,我都要型。」5月確診乳癌,她更打趣道:「我病了反而最健康,手術完還胖了。」對談前,學生提到老師身體狀況。記者打去慰問,當事人輕描淡寫,附上一句:你到時便知他氣管也很差,望他安好。)
余:記者問我有沒有寫過生日卡,單獨寫應該無,但我們每年都會準備一份小禮物。頭兩年,我寫研究目標,寫怎樣回饋社會。後兩年呢?「你休息啦」,「你唞多啲啦」,「身體健康」。你會感覺到這人已經chur(拚搏)到不似人形,是時候睡覺了,哈哈!
麥:我又未至於三更半夜沒睡,我是個很有規律的人。不過我開始覺得很chur,就是連周末也要工作的那種情形。起初我周末不檢查電郵,拋開這些,做自己的事沉澱一下,後來這完全沒可能發生,去完旅行,也覺得,糟了,有很多事要做,一天不回覆,就會累積很多電郵。當然我心知有些事拚得很盡……例如你寄文章給我,可能隔很久我也沒時間回覆。因為我不是hea讀的人,一看就滿江紅。
從發現自己有乳癌到做手術,整個過程,發生得很快。這個轉變頗大,由每天工作忙到嘔,變成不能工作。你一直有表達關心,叫我休息,叫我別走來走去。我很誇張,因為有傷口,要帶着一個血水袋,我不斷做運動想快點復元,扯得整個袋都破了。你就提點我不要這樣,拜託我先休息。
余:我去濟州旅行也有傳信息給你,然後一回香港就去探你,剛好是我生日。
麥:你去完旅行立刻探我,我很感動。試想想,一個後生仔,生日不去玩反而來找我?知道你生日,我請我媽幫忙買了個蛋糕,因為當時我自己沒法出門。
余:我不覺得生日去探望你是件大事,當時是回港翌日,還問你吃不吃水果,怎料你已經在吃乳鴿!
麥:應該是出院第一二天,是我自己在吃,吃雀粟的日子太久。
余:還以為你不能吃其他食物……
麥:(明知被嘲弄也在笑)我已經完全沒有戒口。當刻看到你真的很開心,感受到真的關心,而不是普通的「早日康復」。你會問,最近副作用怎樣,又會說化療很辛苦,問我什麼日子做化療,你會記住。我很感激,因為有十萬件事情要記,怎麼會特別記住這些東西?
余:你的樣子比入院前精靈,因為你本來狀態很差,平時沒休息,有很多憂慮,但手術完可以睡覺,又食乳鴿,所以那天反而是你這半年來最精神的。
麥:接受化療未至於很辛苦,但讓人好累,原來人是可以累到這個地步的,這點挺有趣。化療後我白血球和紅血球指數很低,走幾步路也會氣喘,說話上氣不接下氣,身體很痛。記得我有次跟你說,條頸痛到爆。至於失去頭髮,我不太難過,這是很大的發現,原來我這樣能屈能伸。我沒有哭,完全沒有,當頭髮一把一把地脫落時,我甚至請父親幫我全剃光了,以免瘌痢頭。照鏡子一看,咦,原來自己頭形長得不錯,哈哈!
余:唉,有人在讚自己的頭形!
麥:剃光的時候,連眉毛都沒有。但我沒太大包袱,所以今天也懶得戴帽,因為真的很熱。

社會的創傷和重生
(自己抱恙,還能談笑風生;社會病了,兩人無法成眠,連逛街的心情也沒有。然而,他們在裂縫中找到光,並期盼這是一種重生。)
余:無力感很強,無論怎樣大叫,做些什麼,同樣狀況不斷發生。
麥:對我來說更甚,因為不能出去。6月9日、6月12日,我才剛做完手術不久。我想過出去,但他們說,想都別想,掛血水袋,還想上街,不是吧?於是不斷看新聞,我也不知怎去形容,很無奈,在這刻病倒。但我覺得社會的事也好,我的病也好,都令我看到,很多事你都不能當做理所當然。人生無常,這令我更知道,假設現在有第二人生,我會想做什麼。我慶幸自己能重生,再做真正有意義、值得做、問心無愧的事。
這半年生活慢了下來,我住馬鞍山,會在海邊走走,很舒服,看日落的感覺很美好。我回想在中大十幾年,也沒有試過下班會看到太陽。你懂我的意思嗎?十幾年來從未看過!原來走海濱長廊,看日落,是這麼美。我也開始用曼陀羅填顏色,期間要很專注。那是很誇張的,我問:為什麼可以慢到這個程度?
余:這陣子,我會拿起研究以外的書,因為以前還是碩士時,我完全不想看書。打機,我也喜歡。不過,這段時間沒有買到衫褲,只是看看。
麥:我也很驚訝,這半年基本上沒有逛街,倒是有上網看鞋。
余:我也沒有逛街,有時想轉換造型,只會上網看小店或本地設計師。現在真的沒心情無目的地shopping。其他時間,看新聞直播,或者工作。基本上這半年來天天都是這樣子,其實很掙扎,把時間都投放在時事,其他所有事就停頓了,偏偏研究是需要跟時間競賽的,不能停滯,現在要慢慢追回進度。
中大一役我最痛心的,是背後的象徵意義。這是一個對學校新一代、對整個社會造成的傷痕。同樣的事,不管發生在理大、嶺大、樹大,那仍然是極端的不公義。
麥:社會事和私事,種種事情堆疊起來,真是注定要我休息。我在11月18日完成電療,25日生日,對我來說是rebirth(重生)。無論工作、自己、人際關係、對將來的看法或如何面對人生,各樣都很不同。我真的覺得是rebirth,我也不斷告訴別人這是個rebirth。
余:我這刻沒有這感覺,但過去半年每刻都覺得自己在進步。因為太多資訊,人生很少機會需要分析那麼多資訊。我不敢說這是rebirth,但在思考方面較為細緻。我覺得這是個蛻變,對於香港人來說也是。
麥:看到人性最醜惡一面,也看到人性很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在這段日子不斷萌芽,甚至發光發亮,所以我會阿Q精神地懷有一絲希望。我思考過,如何用相互依存和靜觀,去理解「互即互入」(大意是指萬物都有關聯,沒有人是孤立的)?其實沒有政府,就沒有示威者。不止這段時間,由2014年雨傘革命那時,已醞釀一羣有心人,意識到自己想要什麼。當然不同人會用不同手法去爭取,表達看法。我覺得香港已經不同了,在這幾年間一直改變,大家對社會政治議題更加關注,這是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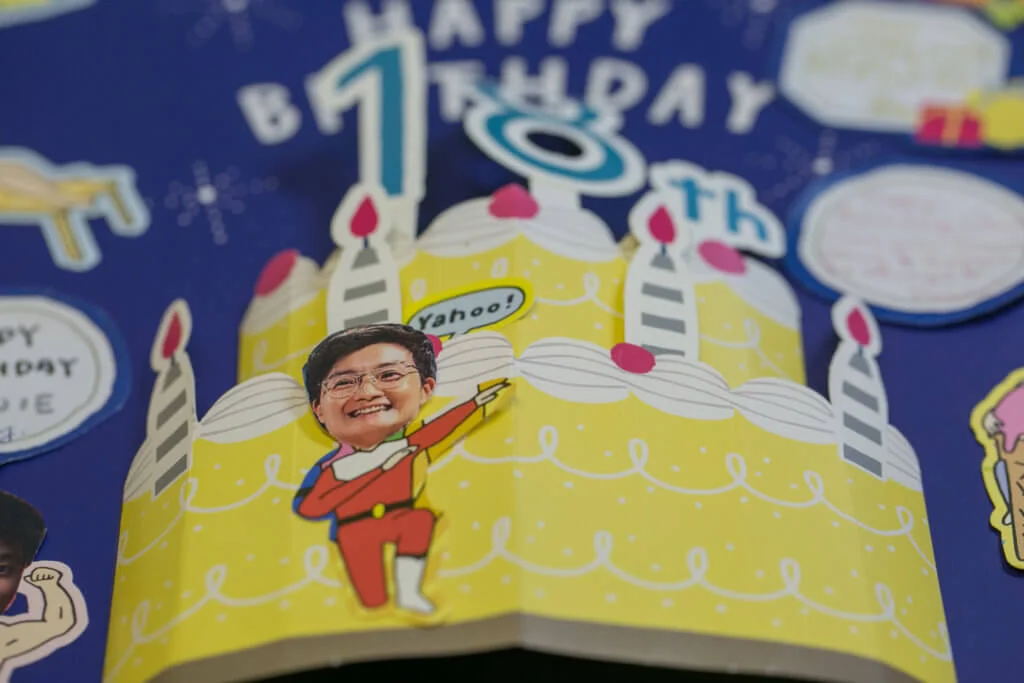
師生悄悄話
余:吃多點,睡多點,丟掉了就不要拿回,放下了就不要太chur自己。可能我跟你這些年,剛好就是你最忙的那幾年,我不覺得這是生活。既然你這刻因病而放下,就放下吧,再想想有什麼令你開心,有什麼是你喜歡做的。你最後決定想做什麼,我能幫忙的一定幫忙;如果我有興趣,我當然會不客氣參一隻腳。
麥:你很理智,會將一件事思考完,再反轉思考多次,花很多時間,不會倉卒做事。我心裏有個想法,有沒有可能有公民靜觀?為年輕人設計課程,用正念或靜觀去看世界。關懷社會、爭取公義,都要從小栽培。雖然我不做兒童研究,但如果要落地,就必須思考如何灌輸給下一代。我們要思考,如果不是小朋友,又要怎樣讓大家明白。「你好我好」很簡單,但如何放下自己,成就他人,造就他人的福祉呢?我想繼續跟你一起努力,無論你在哪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