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了幾個朋友,看看他們有沒有人見過詩人陳暉健。
朋友說,他人在國外,已棄用社交媒體,現在只有一個經常會查閱的電郵能和他通訊。
我把電郵地址抄下來,在電郵說起我們第一次交談,話題竟然關於彼此的炒散回憶。未有那場談話之前,我只知陳暉健是個年輕詩人,中大中文系畢業,著有詩集《關於以太》,知道他流浪過,在中美洲隻身當黑工,在那裏遇劫,摸過牆上的彈孔,不知他在在香港也有做炒散的經歷。

五星級酒店與勞力工廠
話題是我先帶起的。負能量大的時候,我總會想起炒散的回憶。那時穿梭不同的酒店、馬會、桌球會和私人會所。一開始必須放下自我保護的機制,把最重要的身份證明文件和近照發給你根壓不知他是誰的蛇頭,並跟着其他散工一樣,對其「哥」前「哥」後,好像那其實是你親生的兄弟,而不是一直專門抽取別人工資維生的全職蛇頭。待蛇頭看過你的近照,判定你是個正常人後,就會叫你去買皮鞋和西褲,另加申請炒散需要的強積金戶口,最後才可以推開酒店那道神秘的後門,走進五星級酒店的員工層。
裏面九曲十三彎,像勞力工廠,燈比酒店開放公眾的廁所還要黯淡。走過去,廊裏堆滿了自不同房間推出來的舊牀單、枕套和舊毛巾,有時有剛送來麵包,穿過的各式制服,堆在角落的鞋子,與一行一行似乎無盡頭的儲物櫃。
那些穿著不同制服的人會在你認路的過程中快步走過,只剩影子,經過迷路,行錯入廁所,總是要到快將遲到的時候才會找到那一間掛滿衣服的房間,並見到那個負責管理制服的阿姐。
她永遠都低頭專注地熨衫,有人叫她才抬頭打量數秒,二話不說就塞來你要的制服,然後馬上又回頭去熨她的衫。待你轉身那零點零一秒,卻又會按捺不住提你走時記得回來還衫。
換完衫,透過貨梯來到工作的酒店餐廳。僱用蛇頭,再經蛇頭僱用你的部長永遠像不知道今日會有人來上班一樣,總對炒散工的出現感到錯愕,繼後才會找出一個叫”Ada”或是”Kathy”的名牌讓人掛在心口──在這裏沒有人有興趣知道你是誰。
彷彿重重忘記自我的儀式,才終於開始工作。我很快知道場上有許多都在炒散的人,有的是缺錢的學生,有的是年輕的新移民,有的是幫補家用的媽媽,有時也會遇上已經返全職同時又兼營炒散的男人。
一門之隔 兩副臉孔
這一羣人就這樣被關在這個欺強凌弱的空間裏。
部長時常在大堂門前剛對客人卑躬屈膝,柔聲道別,轉身過來就問候炒散工的娘親與祖宗幾代,變臉如同翻書。
時常便是拉開廚房的旋轉門,你走向客人摀身拉椅,欠身微笑,退下時推開角落的另一道旋轉門,廚房裏幾個廚房佬就在講黃色笑話,逼着在場所有女性跟着陪笑。我跟陳暉健說,那陣子上班只要經過冰冷的凍櫃,見到自己的倒影,都有見鬼的感覺。他說,是的,當時他也常帶「老母」返炒散,不是真的阿媽,是那個時常被人問候自己卻不覺的虛幻人物。因而,他見過許多被罵哭的人。

一天就是一次輪迴
那時他愛挑凌晨更,為了那100蚊的補水費。最記得新年炒散,客人給他利市,到下場時間,部長馬上將其沒收,最後分發,他收100,全職收200。但撇除職場環境和人事關係不太好,他在散工工人裏認識到不少單純美好的人:有人見他新手上路,不知怎樣切菜,切完自己的轉頭就來幫他;有人陪他抬一部放了六張椅的椅車,全職員工先是讓他們抬上4樓,之後又改成抬上5樓,雞手鴨腳之際,他還不小心將凳撞到對方的腳,那人沒有一句怨言,收了工還一起坐車回新界。
「回想其實有好多純粹的事。」他說。可是,因為大家都是炒散,轉場轉得快,這個場炒完就轉到下個場,今天之後,不知幾時再次遇見,兩三日,或者一個月,也可能永遠不會再見。
當工作被零散地斬件,工人的時間一樣被斬碎。他們在這個短暫的時空,遇到一天的上司,一天的同事,一天的開心,一天的難受。這就是生活,過一天算一天。
後來,暉健終於回了我的電郵,說自己又不同了,現在簡直是居無定所的無業遊民,但一個一個國家跑着,生活彷彿變得更有密度。
他說行走也是消耗時間和煩惱的最好方法。他把做炒散的錢儲了下來當旅費,此刻人在格拉斯哥,那裏有一條長長的步道,有一片一望無際的高地以及廣袤的荒原。
在山上沒有網絡的日子,他把「那些年」記錄下來,後來,重遇網絡,就把電郵中的附件送了給我:
三種炒散工
撰文:陳暉健
籌款工
還記得那一段日子,每天清晨起牀,由屯門到灣仔,穿上有着組織標誌的風褸,把易拉架、帳篷及貨物塞入狹小的貨車後座,根據指示前往指定地點。按分類排列貨品,動物日曆、筆袋、T-Shirt,最漂亮的貓狗毛氈則掛在帳篷兩側,完成後可以坐下來呆滯地觀察人羣,偶爾喊兩句空洞的口號招引買家。只有當組長來接更的時候才可以上廁所和吃飯,是這一份呆板工作最大的挑戰。
如果突然想要如廁,沒辦法隨便喊一個途人替你看檔,最好當然是憋着憋着乃至忘記焦急的感覺,只是一般都不會如意,唯有減少喝水及進食。無論如何,時薪工作讓人能夠量化那些因此而犧牲掉的時光,優秀的籌款數字使渺小的螞蟻覺得自己仍有用處。
入夜後收拾檔攤,搬上貨車,回去公司記錄一日的銷售情況,明天按等量補貨,重複新的一天。
也有時候,一天還未完結。
馬會投注員
乘坐黃色巴士由灣仔入天水圍。入夜就當作另一個清晨,重複幾次,你就會忘記到底生命是從看到陽光的一刻開始,還是接觸到黑夜那一瞬間開始。衝入商場,穿過飽足一頓後離開的人羣,進入電話投注中心,入口有一部部比人類要高的機器,它會吐出一張紙,標示着今天的工時。
凌晨,馬在睡覺,球就在飛。在只有一堆數字的熒幕前,戴上聽筒,在組長不斷來回巡視的期間,重複說:「您好,電話投注」,切記「2」要說成「兩」。
每個夜更員工總是想坐在第一排有英超或西甲直播的位置,不斷排隊上廁所逃避此起彼落的call。每當想像到滿室白光的中心外面是漆黑的夜就覺得無盡的睡意侵蝕骨髓,因而發明一個打地鼠的遊戲(主客和→一秒之內按鍵;讓球主客和→一秒之內按鍵→地鼠消滅)消耗時光。
有時候馬迷會在凌晨打來,支吾問一下戶口結餘再隨隨便便地買廿蚊。天亮時離開有人問身邊人不如一起買M記。我曾欺騙主任說我有玩LOL(League of Legends,一個廣受歡迎的電腦遊戲),藉此攀關係,某天因為我去廁所太頻密被召見的時候他偷偷把一張紙條塞給我,是他在遊戲裏的名稱:「金翅仆街鳥」。

酒店炒散
那段時間,人生好像只固定在幾個地區,不在天水圍的日子,就是在灣仔或尖沙咀。接到蛇頭的電話,就拖着還未甦醒的屍體乘坐西鐵去做侍應,酒店就在尖東站上面,從狹窄的側門進入,經過保安認證,匆匆走入男更衣室,換上自攜的西褲以及酒店提供的上衣,隨便掛上一個名牌,某天我叫Johnny,某天我就會變成David。
開工之前大家一字排開仔細聆聽西裝經理訓話,有個自稱「江哥」的老屎忽喜歡站在我旁邊,總是掛着一副會關照我的嘴臉,於是經理在新年封的利市會先經過他的手,再由他按年資2:1分配。但事實是這裏沒有人教你,蛇頭總是說「好簡單做一兩次就識」,比如分餸,分餸之前收碟、排碟,落後的人總會莫名感到焦慮,然後站在一旁任由看不過眼的同事幫手。
第一個幫我的人說自己住在天水圍,因為那一晚我們都自願加班(由晚上12時延長至凌晨4時半)所以一起回家,忘記了他的臉只記得他的夢想是開一間餐廳於是想趁年輕多學習。第二天我就看不到他了,流水帳的人員,沒有人當你是一部分,你只是齒輪裏的螺絲,甚至有時候都記不清去過多少間酒店,多少間遊艇會,開過多少個強積金戶口,便乘坐凌晨的紅van回家睡覺。
對了,曾幾何時我們都不過是想做一隻安穩的鴕鳥。各自把頭塞入生活的大坑內期望吐出來的砂礫能砌出一個安樂的下半生。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連想做一隻卑微的順民都是一個奢侈的願望呢?
零散工 法律保障和惡劣環境下的隱身人
因為要爭取自由,就注定要遭受欺凌?
職工盟個人及社區服務行業職工總會總幹事劉家樂認為,目前零散工不被法例保障是因為這種勞力模式有利資本家,因而受到政府袒護,而且對於香港的法例、工會與勞動市場而言,多職工作和零工經濟仍是新潮流,於是大眾和機關都未知應如何面對這股新興的工作模式。
零散工風潮:寧要自由而失去保障
「零散工從前主要是一些婦女,但目前有另一批更大的羣眾,就是一些認為傳統職場環境惡劣,因而無法忍受的人。香港職場遍佈了工時長,職場欺凌嚴重,壓力大的工種,因而叫人不得不放棄全職工作。對這一班人而言,自由是很重要的,他們情願不要傳統的僱傭權益,醫療外判出現,即可見一斑,在香港的醫院中有醫管局聘請的護士,亦有透過中介公司請回來的炒散護士。時常會有一些人可能一個月前剛在A醫院辭職,但一個月後又會經由中介轉回該醫院工作,那是全職可能面對被上司針對,工時過長,精神壓力大的問題,但成為炒散護士之後,儘管是同一職場,但因身份不再是全職員工,心態因而變得輕鬆,想做什麼也看自己的心意。」劉家樂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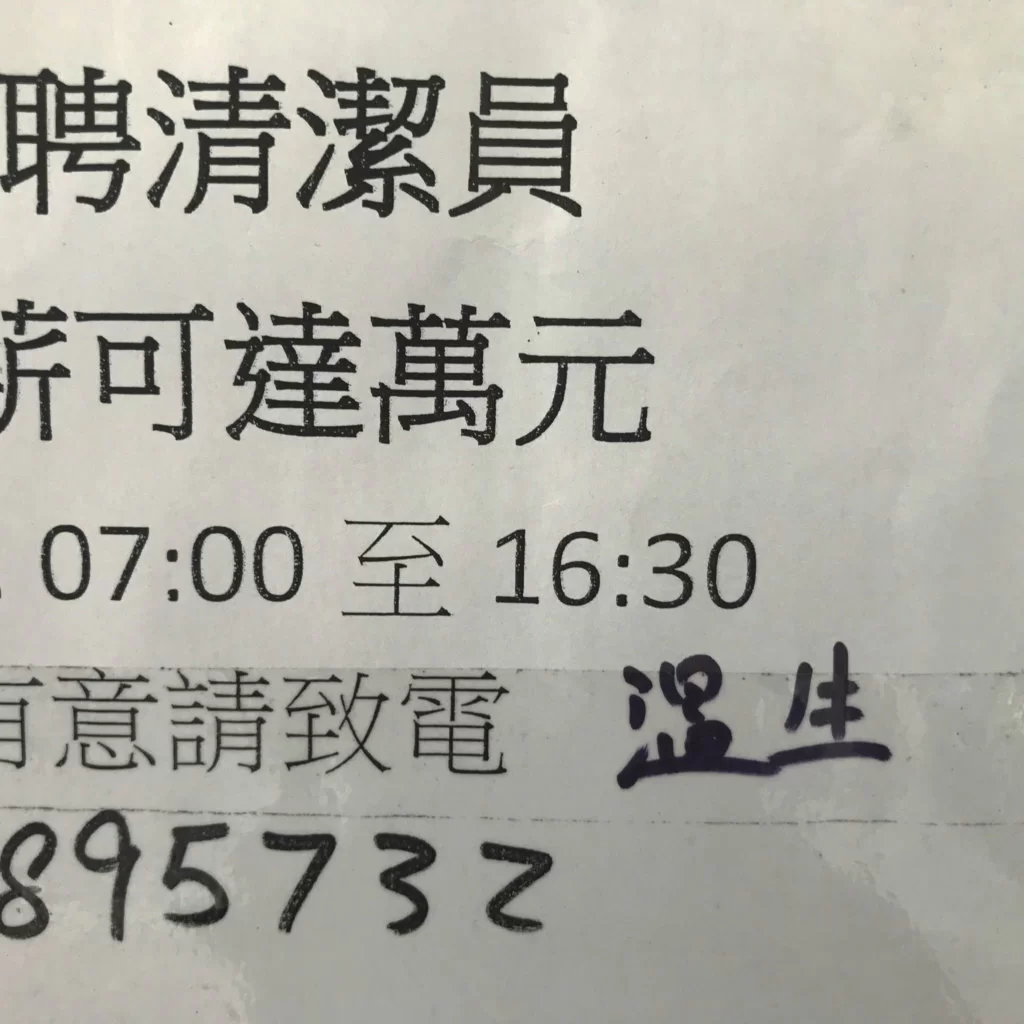
二判走數 大判有責任承擔
職工盟過去曾倡議過名為聯合僱主概念的政策,如A酒店找了蛇頭張先生,透過他找到一大班人到酒店工作,但後來張先生卻拿着工人的工資走了蛇,那在聯合僱主中,A酒店同樣都要承擔責任,因為A酒店仍然是那班散工的僱主,以保障散工者的權利。然而這種聯合僱主在目前仍止於倡議的階段,未獲政府接納。過去,香港在工程行業中卻實現了建造業中代償工資的政策,規定「建築及營造行業的總承判商、前判次承判商或前判指定次承判商(俗稱大判)須負責代其屬下的次承判商或指定次承判商(俗稱判頭)支付該判頭拖欠僱員的工資,但以欠薪期間最初的兩個月工資爲限」。
劉家樂說:「但我認為這個規定其實應該套用在任何的工種之中,可是在法例上目前只包括在地盤工程的界別上。」
當炒散成為一個現象,參與者不管是因為自由還是其他原因,他們付出了他們本來不該承受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