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問董啟章這個人懂得什麼,我會說他懂得很少,但至少他懂得打開書本。你可能會問:書要打開就打開,有什麼懂不懂的?如果只是物理上翻開一本書,當然易如反掌,只要有手就可以做到。(也許沒有手也可以的。) 這個「打開」的意思,當然是指開始閱讀,從而進入書中的世界。你可能又會問:要開始讀 一本書,有什麼難度?老實說,本來是不難的,不過對於當代人來說,覺得讀書難的人肯定比覺得容易的人多很多。這個「懂得」,就是一種小小的意願吧。
當然「懂得打開書本」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只不過是一個起步,還說不上真正懂得什麼。再深入一層的「懂」,是「懂得欣賞」, 領略到書中的趣味。對於一般讀者來說,做到這一點已經很好了。如果能從中得到一點對人生或世界的領悟,就更加是錦上添花。至於說到知識上的「懂」,也即是通透明白、深入了解一個課題,那是學問的層次,不是一般讀者需要追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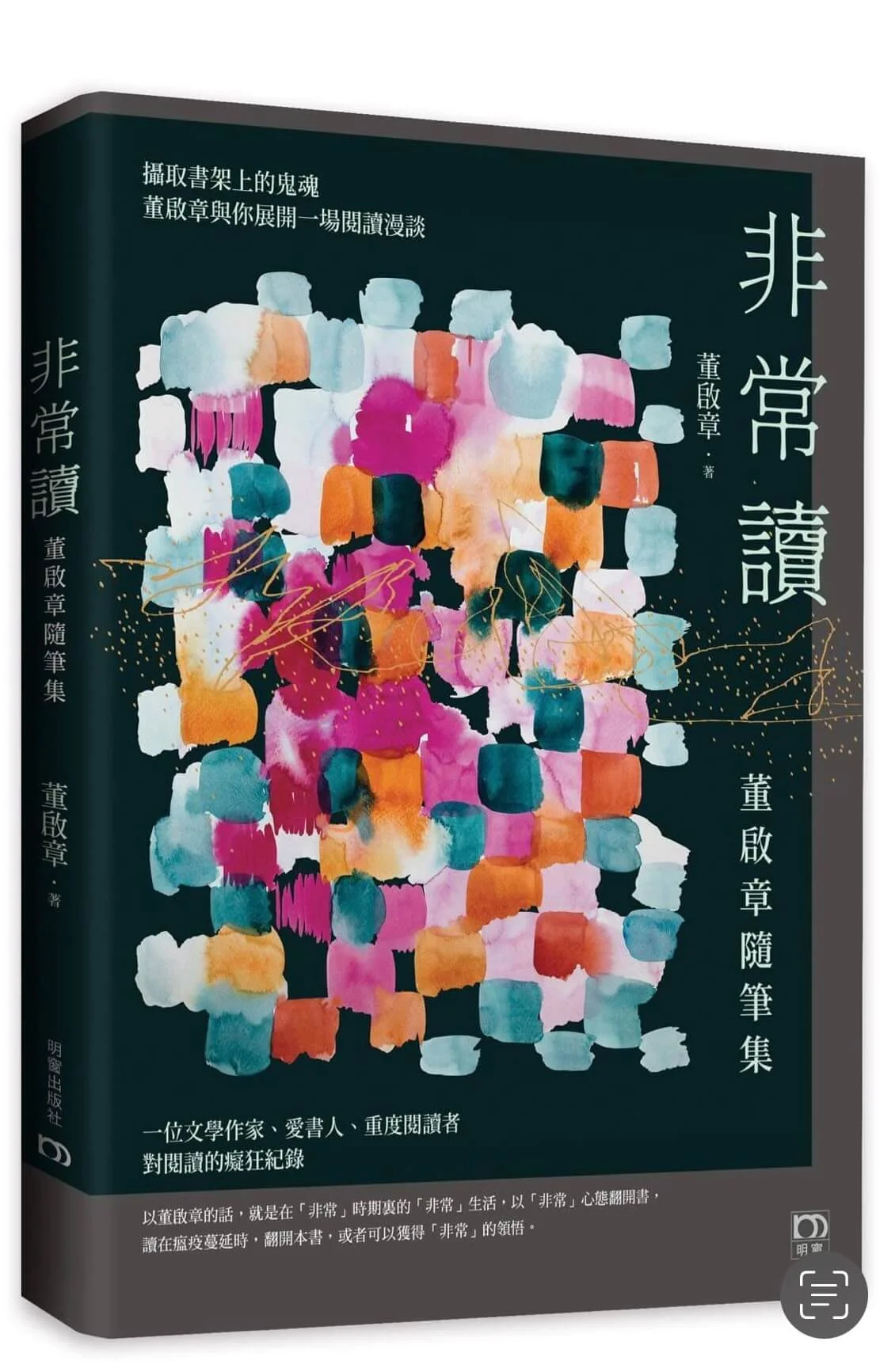
我自己讀書,大部分情況屬於中間那一種,也即是為興趣而讀。沒有任何目的,也沒有特別花力氣,正所謂「不求甚解」。也有時候對某些題目或者某個作家特別感興趣,而想知道多一點的。於是就會盡力搜集相關的書本, 在一段較長的日子裏集中閱讀。當然不會因此而成為這些領域的專家,但多少算是認識了其中的概貌和脈絡。這些集中的閱讀,有時會成為自己往後寫小說的題材,或者意念上的啟發。這又是另一層的「打開書本」的意思了。
從書到書,書與書之間互相關連,互相影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特殊形式。書本史 (書的寫作史和閱讀史)在時間中看是波動不息的流,在空間中看是縱橫交錯的網,而就個別書本獨立來看,則是流和網的結聚點。每讀一本書,就是跟所有的書發生連結和互動。這 不是說讀一本書就夠了,而是說讀書的體驗本身,存在超越個體的意義。我們不必為人類文明而讀書,但我們每讀一本書,也在不經不覺中激活這個文明的靈魂。
在這個意義下,讀書是一種廣義的通靈行為。通過閱讀,我們和無數逝去(或終必逝去) 的作者的靈魂溝通。而像我這樣寫文章去談論書本、介紹書本的人,就無異於閱讀上的靈媒 了。我打開的不只是一本書,也是一個靈界。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有一則關於城市與死亡的故事,講述優薩匹亞的居民在地底建造了一座一模一樣的翻版城。人們死後遺體會經過乾燥處理,然後運到地下城,安排他們擺出生前最愜意的時刻的姿勢,或者扮演曾經渴望從事的職業。因此地下城看起來比地上城更歡樂,更令人滿足。而把屍體搬運到地底加以安置的,是一個秘密兄弟會的成員。只有這些人能自由地上下於活人和死人的城市,地下城的情況也只有通過他們的口中才知道。據他們說,「每次到下面去時,都會發現底下的優薩匹亞有一些變化,死人在他們的城市裏有所創新」。「在一年的時間裏,死人的優薩匹亞就認不出來了。而活人為了跟上死人的腳步,也想要做戴頭巾的兄弟會員所說的死人的一切創新事物。因此,活人的優薩匹亞開始模仿它在地下的翻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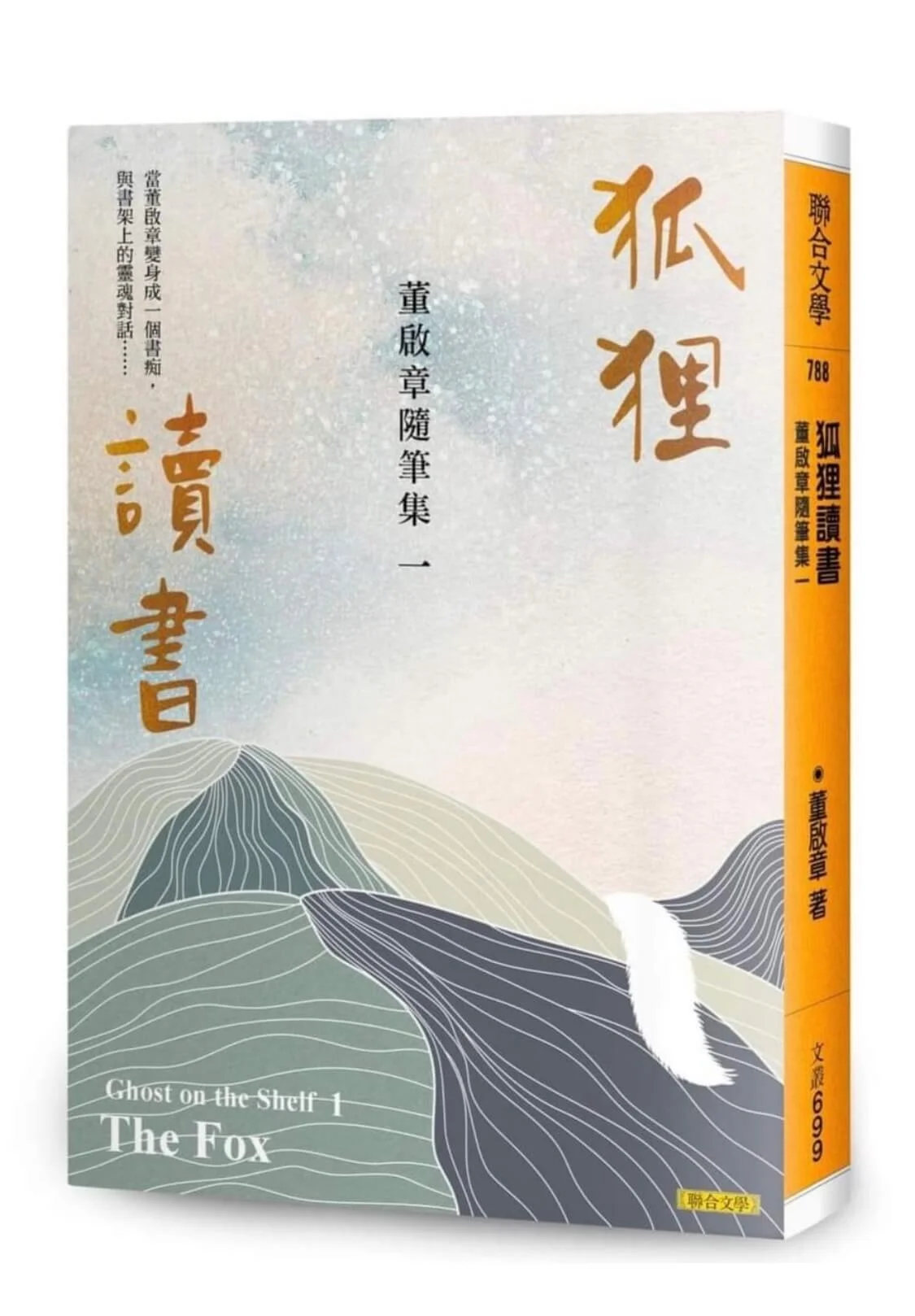
我認為這個故事可以是一則關於閱讀的寓言。書本是前人留下來的經過乾燥處理的遺體,看似固定不變,凝結着逝去的記憶和欲望。活人要了解死人的世界,就要成為像兄弟會一樣的中介人,我稱之為閱讀的靈媒,親身進入地下城,也即是書本中。進入文字冥界的人會發現,每一次重讀舊書都可以讀出新意, 足以讓後人加以學習和模仿。死者沒有停止活着,並且可以不斷創新,反過來創造活人的世 界。當我們閱讀卡爾維諾或其他已過世的作家,我們會發現他們不但未曾死去,而且還比 活着的人更活潑自在,更富有生命力。現實和寓言的唯一分別是,在閱讀的領域裏,出入於生死界並不是某些社團成員的專利。所謂的書評人或書介人只是臨時性的角色,每一個讀者都可以成為通靈者。
我父母給我改名字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這麼遠。叫做「啟章」單純是一個新開始的意思而已。而剛巧又姓「董」,自我穿鑿附會一 番,便好像有某種深意。但深究下去,自問不敢說自己懂些什麼,也肯定有令人覺得不懂裝懂的時候。雖然什麼都涉獵一下,但絕對不是博大;有些話題反覆談論,但又肯定並不精深。極其量也只能自我表白為一種趣味,對一些書本感到好奇而已。而寫出來也不能算是嚴格的評論,只是一些粗淺的介紹,或者個人感想的發揮。只希望作為靈媒的角色,並沒有把 讀者誤導到惡靈身上,或者曲解了先靈的意思而遭到怨恨和報應。
本欄自二○一七年至今,已經寫了接近五年,當中的文章早前選輯成閱讀隨筆集《非常讀》,最近又出了《狐狸讀書》,往後還會有另一輯《刺蝟讀書》。幾年來身體力行不斷買書看書,書架在舊鬼之外又增添了不少新魂。至於自己寫的書,縱使本人至今依然僥倖生存,也作為靈魂預備班先佔去了一些位置。 自從搬家之後,我在客廳中央的書架上設置了父親的靈位,在他的遺照周邊擺放了我的著作。這些印着我的名字的書,當然也是屬於父親的。區區幾本書雖然算不上什麼,但在父親心裏,應該會感到滿意和安慰。至少我沒有辜負他給我的名字,做一個懂得打開書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