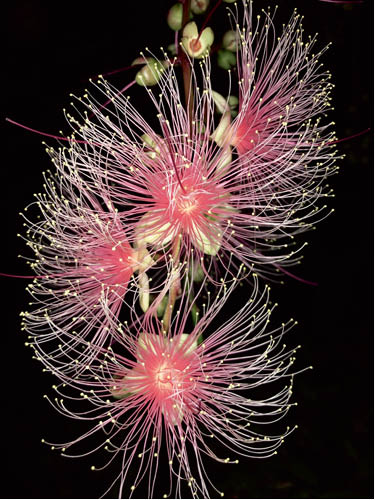
我生命中當然有太多這樣的經驗,對那些被我扭曲編織進小說裏的,傷心、驚駭、憤怒、羞辱的人們解釋:那寫的不是你啊。那只是我腦額葉開了個洞,一道黑光穿過,召喚那些地獄亡靈,人心裏最卑微痛苦的激流,它已經脫離了取材時的你,和寫小說的這個我,一起獻祭給那野牛羣狂奔過峽谷,那個故事超出我力量的衝力啊。
譬如說,年輕時我總愛拉着你讀的,井上靖的《冰壁》,和夏目漱石的《心鏡》,這好像是我的「私密二書」,靈魂(我們那時多愛說「靈魂」這兩個字啊)最清寂深哀,游到最深之淵的冷顫。前者是一對叫魚津和小坂的登山老友,他們共同的聖境,就是酷冬攀爬那「死亡之角」的奧又白冰壁,那是絕對的、純淨的所在。但這較年輕、內向的小坂,愛上了一位重要人士的妻子,那個女人美到不可思議,那種美近乎魔。然後這個深陷美之狂迷的年輕人,和這位老大哥魚津,在那同樣幻美讓人心摧的暴雷中,攀爬那反射出整片銀輝的冰壁,登山索竟斷裂摔落而死。之後整個故事,就是獨留人間的魚津,必須面對社會上對於「登山索為何會斷」的質疑:他堅持是登山索製作公司之瑕疵,但如此牽涉一大集團商譽後面巨大的聲譽之戰、律師、媒體攻防、可操控的第三方鑑定專家;或是小坂竟是自己割斷繩索,想殉情於對他們兩男子漢視為聖境的山裏;或有質疑他是在好友墜下懸吊,為了保命而割斷繩索;或僅是對他們這樣專業登山客不可能犯的低級失誤,在之前宿營曾大意以冰靴踩過那截登山索……
當然還有他也循了亡友生前曾走過的「美之震撼」,見到並認識了那位美得讓人倒抽一口氣的幻美人妻。他有沒有也被擊中最心底那「美之哀」的痛楚,背叛了他死去的好友?至於夏目的《心鏡》呢,對二十多歲的我來說,那是一個超乎當時想像力能超越的「後延的未來」的恐怖。一個年輕人遇到一位長者,和他端莊美麗的妻子,年輕人為這長者的智慧和氣質着迷,長者也常找年輕人在市郊的林中步道散步,說一些哲理。但年輕人眼中,長者和妻子,似乎籠罩在一種「從過去而來的迷霧」,一種說不出的悲愁,和現實世界的聯結總慢了半格的轉達。或是說,這位他尊稱為「先生」的長者,內在有什麼核心的、柔軟多汁的、夢幻多情的,像枇杷果肉那樣的東西,在很久以前就預先被剝空了。這不是故意,而是自然而然,從他的言談,對許多小事的態度,散放出讓年輕人迷惑但感興趣的一種「苦寂」、「空曠」。
小說最終,以「先生」留給這年輕人一封非常長的遺書收尾。事實上這封遺書的篇幅佔了全書二分之一以上,「先生」如懺情錄對這年輕人說出一個塵封多年的秘密。他年輕時,和一位K君,同為東京帝大的大學生,共同賃租在一位寡婦和她的一個美麗女兒的屋子。這美麗女兒,就是後來年輕人所見的,「先生」身邊那高雅嫻靜的「太太」。年輕時的「先生」把K君視為摯友,且深深崇拜他。K君讀非常多書:哲學、歷史、歐洲文學,是個性格憂悒但思考高出平庸常人好幾層樓的沉思者。但總之有一天,這兩個好友在郊外散步時,K君對「先生」說出自己深深迷戀那美麗小姐的痛苦,在那個對每一種人類情感與品行皆如此嚴肅看待的年代,K君把內心這個秘密對好友說出,那是重中之重。但這讓年輕的「先生」內心劇烈搖晃,因為他也在這樣像一家人─寡婦、女兒、「先生」、K君─的每日相處,深深愛上了那小姐。但他也感覺到,小姐對K君的女孩喜歡氣氛,多出對自己一些。於是,「先生」在某日K君有課沒回來,在餐桌向寡婦正式提出,想對小姐求婚的懇請,並說會讓老家的叔叔出面提親。那寡婦思考了一下,很爽快答應了。接下來夏目的深邃描寫,便在這屋裏四人關係、細微空氣的變化。K君幾天後知道了這事,臉色慘白但真摯祝福了「先生」和小姐,這之間當然最難描寫的是年輕時的「先生」,作為「不存在的背叛好友」、「現實中的行動者」,他每日觀察K君的神色是否有異,那種腦中在義理、博弈、希盼能有一場對話可解開心結、得到通透的諒解……這些像無數玻璃細管中不同油壓開降的困難運算(他那時也太年輕了),但大約幾天後,有一天清晨,他們發現K君在自己的臥室中用小刀割斷頸動脈自殺了。「先生」寫給那年輕人的遺書寫道:
「那時給我的第一個感覺,就同突然聽到K坦白他的愛情時差不多。我的眼睛剛在他房中看了一眼,便如同玻璃假眼一般失去了轉動的能力。我呆若木雞的戳在那裏。彷彿一陣黑色的疾風掠過我的身子之後,我才甦醒過來,在那一瞬,可怕的展現了我之後的全部生涯。我不禁戰抖起來。」
我想對眼前這「許多年後的W」說:
「說起來,年輕時,在那許多名字的偉大小說中,井上靖的《冰壁》,夏目漱石的《心鏡》,作為我心底秘藏之最愛,它們或不是對於我的「小說大教堂」,但卻是當時二十多歲,完全沒有感情經驗的我,像在培養皿中用鑷子小心翼翼放進菌種植株,並微調、觀測它結晶變化形態的『情感教育』,某種透明發光玻璃片上紋刻的,『愛情的大強力碰撞機的設計原型』啊。事實上我後來的妻子,也是從別人的手中橫刀奪愛,成為自己的戀人。」
「你可能覺得困擾,你的妻子,為何許多年後,還成為我演講的故事鑲嵌中的一片花瓣?但它說的真的不是你。而是我年輕時便被井上靖或夏目的小說,像催眠或種入想像最內裏的一種『三人的探戈舞』,我日後的不同時期小說,其實都迷戀於這種結構的不同變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