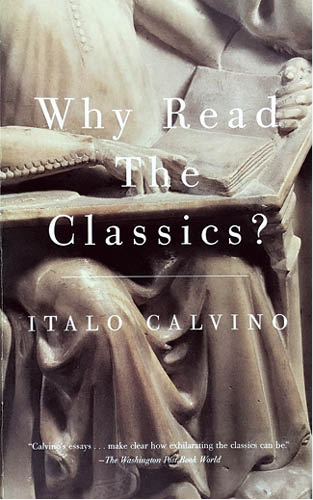
在《為什麼要讀經典》中,卡爾維諾對於「經典」下的第一個定義是:「那些你經常聽見人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強調「重讀」當然是因為害怕人家以為自己連這麼重要的書也沒有讀過,而不得不撒一點小謊以保尊嚴。這其實並不壞,因為這樣說至少是出於對經典的尊敬。
卡爾維諾之所以能這樣說,可能由於他還處身於文化教養比較好的時代。換了在今天,大概沒有多少人會介意「初讀」和「重讀」的分別。我們的第一個定義很可能要改為:「經典是你聽說過名字,但卻從來沒有讀過,也不打算要讀的書。」當然,這還不是最差的情況。我們不希望有一天,人們聽到經典的名字時,會有這樣的反應:「咩嚟㗎,未聽過喎。」
《為什麼要讀經典》是我讀過的談經典談得最好的文章。給經典下定義並不是新鮮事,但像卡爾維諾那樣下定義,才是新意的所在。如果我們聽見人說,經典是「傳統文化的瑰寶」、「偉大心靈的結晶」、「人類智慧的遺產」諸如此類,我們一定會打呵欠。這些話說了等於沒說,或者比沒說更差,因為它們令人對經典失去興趣和想像。卡爾維諾從最平庸的假設出發,逐步推演出經典對讀者的意義,最後令人不期然地想拿起一本經典開始閱讀。
第二個定義是這樣的:「經典是那些留給已經讀過和喜愛它的讀者們寶貴的體驗的書;但對於希望留待更佳的狀態下才閱讀的讀者來說,它們同樣會帶來豐富的體驗。」這一點牽涉到什麼時候讀經典的問題。應該盡早去讀?還是留待人生更成熟之後才讀?卡爾維諾的看法一貫地開放。年輕時讀經典固然好,但也會有經驗和視野的局限,只看到某些切合年輕心態的東西。相反,遲遲未讀經典並不需要感到內疚。說不定在人生的晚期,你才能更深切地體會到當中的精髓。換句話說,在人生的不同階段看,也能帶給你當階段的意義,這樣的作品就是經典。
從上面的定義,自然會延伸到下面三點:一、「經典是每一次重讀也會帶給你如同首次閱讀一樣的發現的書。」二、「經典是就算我們首次閱讀,也會令我們感到好像在重讀從前已經讀過的什麼的書。」三、因此,「經典是永遠也不會窮盡它要向讀者說的話的書。」說到這裏,我們便很容易能夠分出,哪些是只有一時的意義或用處的書,而哪些是具有所謂「永恆的價值」的經典。
堅決拒絕教條主義的卡爾維諾,繼續對經典的定義作出開拓。在所謂「永恆價值」和「普遍意義」之外(這是我的概括,他沒有用過這兩個詞),他又反過來強調「個人意義」。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必須建立「自己的經典」。這樣的說法好像自我矛盾,因為經典必然包含全人類共享的跨時空意義。「一個人的經典」將不成經典。但是,經典對每一個讀者來說,卻是一個個別的經驗歷程。沒有個別的讀者的存在,就沒有經典。兩者之間的互動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說,讀者幫助經典發掘它們日新又新的意義。
然後,卡爾維諾又把論點反過來,說:「『你的』經典是你無法保持冷漠,而通過與它的關係或對立,來幫助你自我定義的書。」也即是說,就算是你不喜歡的、不認同的書,也可能是「你的」經典。這一點尤其重要。這說明了個人的口味或取向,並不是斷定一本書的終極準則。我們必須虛心承認,有些我們不喜歡的甚至是反對的書,是具有重要文化價值的經典。更非凡的洞見是,我們往往要通過和這些書的對立或辯論,來釐清自己的取向,確立自己的價值。這種能夠對自己作出強而有力的挑戰的書,就是經典。
卡爾維諾的經典定義總共有十四點,步步推論,環環相扣,充滿啟發性,我就不一一在這裏引述了。他既是個創造力非凡的小說家,又是個思考力驚人的評論家。我個人認為,他是二十世紀下半最富聰明才智的作家。可是,他的作品能不能成為經典,到現在還是言之尚早(雖然他已去世三十五年)。他在文中也談論到,在閱讀經典作品和當代作品之間的平衡。很明顯,時間的距離是判別經典的另一重要因素。
對於創作者來說,目標當然是自己的作品有一天成為經典,但這絕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如果隨便說挑戰經典,超越經典,那更加是狂妄的心態。但是,反過來因為受到某些經典太深的影響,而變成了自己創新的障礙,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在欣賞和學習經典的同時,創作者也要懂得和經典保持距離。好像喬伊斯那樣,把希臘史詩納入自己的作品,需要的是強大的自信和駕馭能力。也有因為太愛經典,太沉迷經典,而為經典所困的例子。一些年輕時極富才華的作家,因為中年以後深入鑽研經典,而損害了自身的創造力,再也寫不出好作品,或者只能寫出經典的次等模仿品。
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經典會變成危險的陷阱。我們以為自己繼承和發揚了某種價值,以為自己復興了某種失落的傳統,但我們可能其實只是自欺欺人。當然,這危險只是關乎少數的從事創作的人而已。對廣大的讀者而言,除非盲目地把經典當作意識形態的宣傳來接收(例如民族主義),否則經典絕不會帶來任何壞處。正如卡爾維諾總結說,撇開任何具體的作用,「讀經典的唯一原因就是,讀經典總比不讀經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