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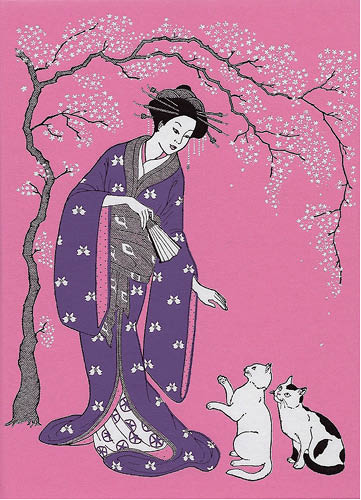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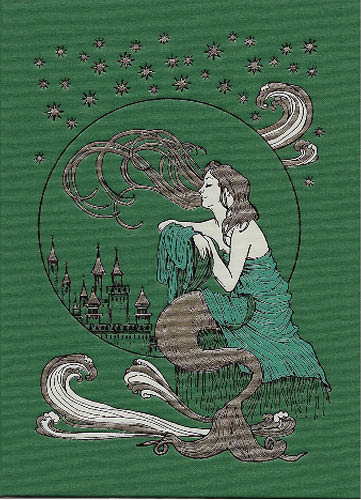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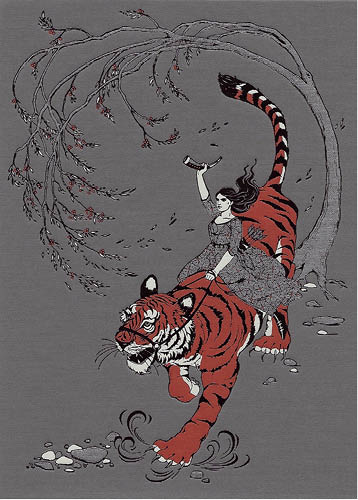

Robert Venables 配圖

Tim Stevens 配圖

Omar Rayyan 配圖

Tomislav Tomic 配圖

Kate Baylay 配圖

氣定神閒做早餐
世事此消彼長。香港和內地疫情放緩好轉,美國這邊就突變兇險。怕也沒用。紐約的瘟疫終於如同野火一般噼嚦啪啦浩浩蕩蕩漫山遍野地燒將起來,留在家中的長者只有選擇如常做早餐喝Earl Grey,努力做到氣定神閒,處驚不變。切麵包方方整整,塗牛油均均亭亭,煎雞蛋香滑完美,調奶茶銀匙叮叮;一樣樣有條不紊地按部就班做妥善了,安放桌上,看上去和諧悅目,也就產生美感,轉而導致寧靜,還真能鎮定情緒,起碼能夠引起幻覺:事情大概壞不到哪裏去;自己不是還好端端的在家中進食麼?其實外面已經天翻地覆:三月七日紐約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三月十二日聲稱緊急狀態可能會是持續六個月的危機,三月十六日州長再宣布關閉學校、戲院、酒吧、餐廳,嚴禁五十人以上的聚會。長期幫襯的古籍書店來了個電郵,說:「為安全起見,共同抗疫,決定將門市部停業,但是依然歡迎大家網上或電話郵購心愛的書籍。此時此刻,我們深切關注同情所有受疫情影響的人士,並且慶幸咱們愛書一族是多麼的生氣勃勃,充滿鬥志。」
排遣寂寞有良朋
乖巧的書商將高帽一五一十地拋送過來,我也覺得冇乜壞。正是:高帽唔怕戴,總要除得快。旁的不論,在這瘟疫蔓延的時刻,愛書人的確佔了一點優勢:我們絕大多數都是獨行俠,本來就不善交際,不愛羣居,球場劇院旅遊派對,隨你關閉停止好了。抗疫措施愈來愈嚴峻,先是禁止五十人的聚會,然後縮減為二十五,甚至十人。喜歡開舞會打橋牌的朋友難免失魂落魄。即使下棋,也要有個對手;至於書蟲,一卷在手,立即消愁。永遠不會寂寞,身邊的每一本書都是活生生的良朋,可以作永不終止的精神上的對話。話雖如此,外界的侵擾亦未能全免。話說晚飯後正打算坐下看書,突然門鈴大作;其時天色已晚,家中就只是我和老伴兩個老弱殘兵。我又沒有喝過獅子奶,哪裏來的膽子下樓應門?於是只有憑窗喝問是誰;往下望去,在暮色中那波多黎各青年依稀可辨,原來是來推銷新電視頻道的。我只道:「年輕人,我明白你是為了工作,但是在這病毒猖獗的時候,為何不戴口罩?請你快快回歸看書,方是正經 。」可不是,三天前送藥的用兩重口罩把嘴巴圍得鐵桶似的,連我用來簽收的原子筆亦用戴上透明膠手套的右手接回。
天涯美人多神秘
這一向我從郵箱取出大小郵件之後,先把郵件擱在樓下一兩天,再拆看,當然還要洗手。(一般的說法是這冠狀病毒能夠在堅硬光滑的表面上「存活」七十二小時,在紙皮上是二十四小時。病毒並非生物,還得依附在生物細胞之內方能繁殖衍生。)最近果然有消息傳出,紐約有兩名郵差因遞送郵件中招。我自己更是三十年來已經不再看圖書館的書。看書中毒的傳聞頗多,其中最離奇的是:《金瓶梅》的作者原來是嘉靖大名士王世貞,寫成此書的目的是為父報仇;用毒藥浸泡書頁,然後獻給仇人。仇人用手指沾唾液一頁頁地把書來翻看,結果中毒身亡。《一千零一夜》裏面有個忘恩負義的國王,將治好自己怪病的神醫賜死。神醫死前贈國王一本染毒的醫書;國王不虞有詐,中了死亡圈套。法國電影《瑪歌皇后》裏面的國王也是陰差陽錯因為翻看染毒的奇書而暴崩。這當然只是電影的虛擬,和史實不符;不過記憶中從前長一輩的親朋的確習慣側着頭瞇着眼,用食指沾上口水,再共拇指一起,拈起書頁的上角來翻看;也有用口水來舔郵票的;幸好如今看不到了,也幸好自己沒有這樣的陋習。試想想,書架上不乏來自天涯海角的古籍;她們可都是歷盡滄桑的尤物,理直氣壯地有很多神秘的過去;喜歡歸喜歡,也得保持適度距離。翻看舊書之際,往往有剪報、郵票、信紙,甚至照片等歷史性的小碎片從中跌出。(聞說三四十年前,在香港書店購得的舊書裏面,會夾着鉅額鈔票,甚至《永樂大典》古籍的殘頁。)在這瘟疫蔓延的時候,從巴黎或倫敦訂購的古籍翩然而至,拿在手中不禁暗自思忖:誰知道這裏面還有什麼?
彩虹系列真燦爛
至於這裏的一套十二冊由蘇格蘭詩人兼文學評論家安德魯朗格(Andrew Lang,1884–1912)編寫的彩虹系列童話故事集,卻是貨真價實的處女新書,從二〇〇三年至二〇一三年陸續出版,向Folio Society出版社直接訂購。這麼多年來枯坐書架,雖然寂寞,倒也夷然。我如今得空,將這套書依據當年安德魯朗格編印出版的先後,順序重新排列妥善;驟眼看去,果然如同彩虹一般明豔,和諧悅目,也就產生美感,轉而導致寧靜。
莫札特四歲的時候有人問他這麼動聽的音樂是怎樣譜成的,莫札特回答:「沒有什麼。我只不過是將互相喜歡的音符放在一起罷了。」彩虹系列童話採自世界各地,也有從格林姆和安徒生那裏採摘;甚至改編《小人國》。把差不多四百個風格迥異的童話放在一起,竟然也具莫札特樂章的和諧。彩虹童話初版從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〇年分別陸續推出;Folio Society這一套由十二個畫家重新配圖及設計封面,華美到極點,反而轉為樸素;童話世界裏面就有這許多的艷異和兇險,當然死亡也往往會出其不意地降臨,提醒我們童話世界和真實世界的共通之處。食物和書本能夠同樣地滋潤精神,怡情養性,對抗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