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與彼思(Pixar)動畫《玩轉腦朋友2》(Inside Out 2)創下史上全球最高票房動畫紀錄。故事講述主角Riley的大腦本由五名擬人化的情緒成員阿樂、阿愁、阿驚、阿燥和阿憎控制。隨主角踏入青春期,新情緒阿焦、阿羨、阿厭與阿尷亦進駐總部,引發連串人際關係危機。這部電影被視為心理學的科普入門電影,透過把情緒擬人化呈現,向觀眾解說人類情緒的基本運作原理,以及如何擁抱負面情緒。
按醫管局數據,二○二二至二○二三年度香港有六萬六千八百人確診抑鬱症,較五年前的數字高出近兩成。本地精神健康服務需求甚殷,然而公立精神科的半緊急新症輪候時間中位數為四周,病情穩定的新症輪候時間中位數達四十四周。
有臨床心理學家與治療師在社區推廣不同的情緒治療手法,助港人自療。當中,「內在家庭系統」(Internal Family Systems,簡稱IFS)療法,如《玩轉腦朋友》一般,相信每人內心世界存在不同部分(Parts),就如阿樂、阿愁、阿焦般肩負不同角色。我們透過理解及轉化跟各部分的關係,方能療癒與成長。
當我們不再是十三歲的Riley,又能如何應對世態無常,我們又能如何好好療癒自己?

社會高氣壓致焦慮 與自我批判聲音和解
池衍昌(阿池)是內在家庭系統實踐者(IFS International Level 2 Trained),擁有六年IFS實踐與個案治療經驗。他自二○二○年在港推廣IFS療法,上月舉辦一場《玩轉腦朋友2》映後談兼IFS共學。他原本料僅二十、三十人感興趣,卻有過百人報名。
阿池指,疫情下日常停頓,人們開始向內審視,成就IFS進入大眾視野的契機。「消費社會都是有大量的消費品讓你逃避痛苦、轉移痛苦。無論是『煲劇』、消費、吃東西,其實每人都或多或少有這些舒緩內心壓力的機制。當這些運作停下來時,人就開始要面對內心一直沒去處理的情緒狀態,或者一些人生功課。」

非心理學出身的阿澄(化名)便是主動修讀內在家庭系統的一員。「我想也關於大環境,其實都容易令到人很憂鬱啊。」她說。阿澄向來關心香港社會。她的朋友是被控涉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泛民主派初選案四十七人之一。二○二一年,本已積滿壓力的阿澄赴法院聽審,朋友留意到她近年的焦慮有增無減,便向她推薦自己學習的內在家庭系統療法。
阿澄素來理性,起初並不習慣這種向內尋找無形自我的對話模式。在此之前,阿澄已接受過四十節情緒諮詢,然而她卻一直無法坦誠與治療師分享內心鬱結。她說:「就是覺得情緒是不好的,腦內飛過很多很rational(理性)的東西,就是想人家為甚麼這樣,或自己為何這樣……其實觸碰不了最內在的感受是甚麼。」

後來阿澄掌握IFS療法原理後,開始與自己對話,更發現內在經常自我批判的部分。「我知道他(自我批判部分)在他人打擊我前,就先打擊我,是為了幫我打底。那我就不會再因為別人的打擊而崩潰。」她明白這個自我批判部分固然嚴苛,但有着善良意圖,就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傷害。經過多次不太順利的練習,有次她安坐沙灘,手放心口默想,想像自己與這個部分對話。她說:「不如由現在起我們重新出發,我們試一下對這個世界和自己信任多一點。」
那一刻她覺得自己和那部分的內在和解了。

各部分肩負責任 保護自己免受傷
內在家庭系統由美國家庭系統治療師史華茲博士(Dr. Richard C. Schwartz)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創立,適用於創傷、憂鬱治療及戒癮行為等。內在家庭系統的世界一如《玩轉腦朋友》的設定,人的內心居住着許多部分(parts)。
在 IFS 基本概念裏,主要分為「保護者」(protectors)與「被放逐者」(exiles)兩大部分。上文阿澄的自我批判聲音,也是「保護者」一種—他負責保護你,不受痛苦所傷,又可細分為掌握你日常生活、保護你避開內在傷痛的「管理員」,與每當內在傷痛被觸發時,跳出來「滅火」的「救火員」。
阿池指出,電影《玩轉腦朋友》裏樂天開朗、常掌握情緒控制台的阿樂便是「保護者」的角色,她不容許自己不開心,以確保我們可面對負面情緒。「我們做一些個案、探索自己內在時都會遇到這種樂觀的自己。」而電影裏的阿樂亦因疲於維持正能量,一度情緒崩潰。
電影中的阿焦終日構想事情最壞的後果,甚至因焦慮而失眠。當事情無法掌控時,阿焦更意外觸發恐慌發作(Panic attack)機制,讓主角心跳加速,必須大口大口呼吸。阿池指,焦慮的部分催生如此反應,可能出自擔心,認為當事人不懂得如何疼愛自己。但他補充指在IFS裏,沒有任何一個部分是不好的(No bad parts)只是他們有時會用較極端的方式保護當事人,意外弄巧反拙。

阿池解釋:「每個保護者背後都有我們所謂受傷的部分,即是小時候受傷或長大後受傷的部分,他們背着一個不開心或者創傷的情緒、part。然後保護者就是應對他們的存在。」至於「被放逐者」則是在過去創傷發生時,那些內在情緒無法被當事人處理而被流放到意識之外的部分。
IFS相信,要認清這些內在部分,並與之連結,便要進行對話。當事人安頓好身心後,便會找到自己內在世界不同部分的呈現方式(Trailheads),那可以是想法、情緒、衝動、記憶、夢境、意感(felt sense)、身體感覺、內心聲音、內心圖像,再嘗試對話,逐步梳理。
不過,阿澄記得,最初尚未熟悉 IFS 手法時,接觸自己內心那名習慣批評自己的保護者,對方並不形象化,更像是一團令人悲傷的氛圍。因此,她認為內在家庭系統其實對使用者的語言要求和情緒敏感度有一定門檻,尤其以語言準確描述情緒並不容易。

社工為自己立下邊界 助中學生處理成長焦慮
學校社工Emi(化名)是另一位 IFS 療法使用者。她在疫情期間進修治療手法時,接觸內在家庭系統。她第一次與自我對話時,寫了一篇長日記,然後在文字中整理出最少二十把來自不同內在部分的聲音,包括焦慮、工作狂、自我質疑、想被善待與心急想要成長的部分等。「我覺得那一刻很神奇,原來我的心不是只被一、兩個單純的部分去解決我的行為。我心裏面有一個很龐大的家庭,一直支持着我。我覺得這一下是一個很大的觸動。」Emi說。

她後來慢慢向內尋,觸及自己當社工後時有爆發的無名怒火。於 Band 1 學校任職的她坦言:「可能是因為我內在有很重的恐懼,也碰到一些我以前處理原生家庭的問題時,那些殘餘感受、創傷是沒處理到的。」而她體內的憤怒部分便是從她成長過程發展出來,以替她順利排解生活中恐懼,好讓她能如常生活。她笑言自己其實也很欣賞憤怒的自己,因為當社工也會遇到不公平的人和事,現在這部分讓她懂得為自己訂立邊界和發聲,而不再僅僅討好家長,並要求家長共同應對孩子的情緒需要。
在自療以外,Emi亦曾在學生身上應用IFS。她曾遇到一名女生隨身攜帶𠝹刀𠝹手,不停思考尋死的方法。女生說,腦海有一團黑漆漆的東西不停叫她去死,與一頭想她去𠝹手的惡魔,但他們一直不願在治療中與Emi對話。直至某次聊天時,Emi發現那兩個部分一直在保護一個更脆弱的部分。女生漸漸明白,那個脆弱的部分,正是儘管由小到大都很努力去做任何事情,但都被人拒絕、被人批評,卻沒有得到認同的自己。「我不是只有死。原來我還有選擇可以保護再深一層的創傷。雖然我現在不知道怎麼做,至少我看到她在這裏。」Emi這樣複述那位女生的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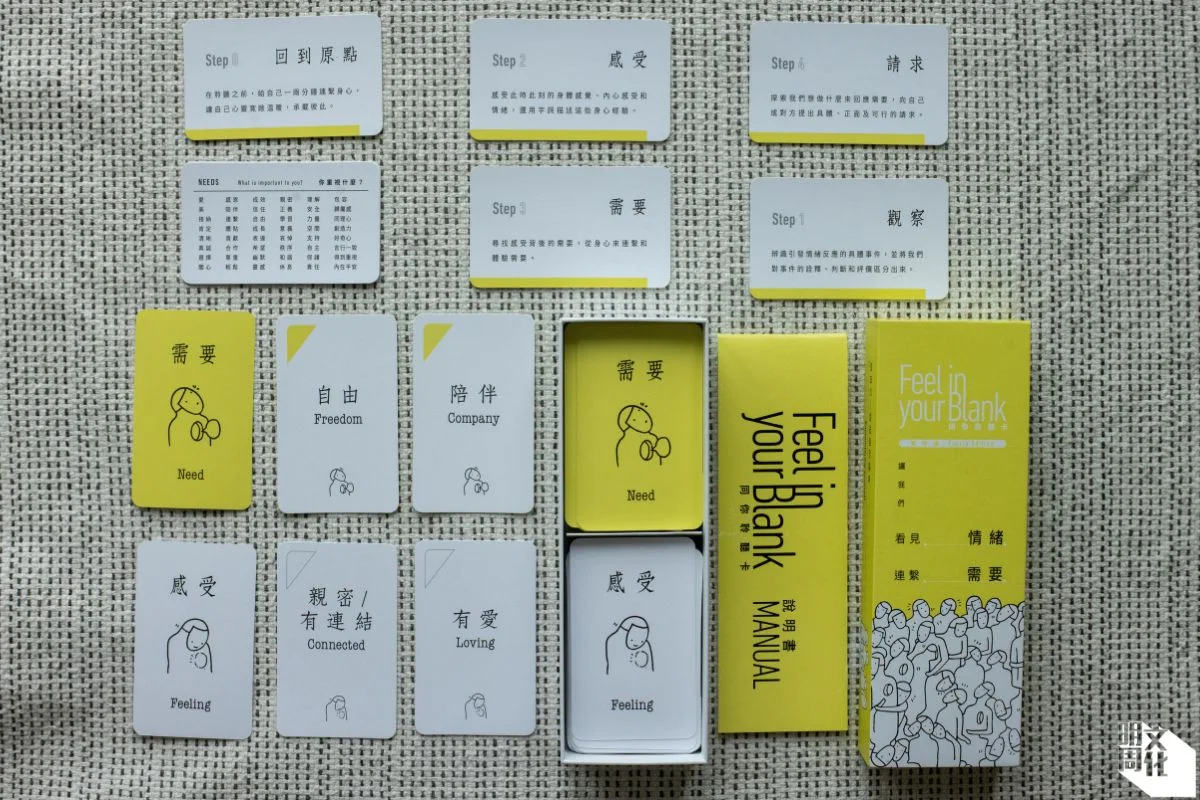
那個女生所形容的「我」,亦是 IFS 跟《反轉腦朋友》不同的地方。阿池形容主角像個木偶公仔,任由不同情緒主導。但內在家庭系統的理論具有「真我」(Self)概念,認為我們才是那個情緒控制台的掌舵人,不同情緒只是我們體內的其中一部分。
阿池指出:「我不只是我憤怒的部分,它是我其中的一部分,這個我就是電影中沒有的。這個真我就是每個人都有的狀態,每個人最核心的自己。當我們在這個狀態時我們就可以幫助、療癒在IFS裏面最核心的東西。」

察覺社會建構創傷 轉化成活下去的力量
臨床心理學家葉劍青則認為,IFS 在九十年代並不流行,直至二○○○年後社會對創傷與解離(Dissociation)的認知增加。解離症曾經被稱為「多重人格障礙症」,及後改稱「解離性身份障礙」。解離症患者會在單一個體中擁有多個完全獨立人格。而部分創傷後壓力症、抑鬱及焦慮症患者等亦有機會出現解離狀態,例如失卻生活部分時段的記憶。他認為,以不同人格部分去理解相關症狀非常重要,他解釋:「因為你接受治療,我們希望見到轉變,如果你看自己是一個死咕咕、不變的,那很大問題。」
現時社會主流心理療法是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葉劍青解釋,就是治療師會替使用者以理性思考角度看自己是否在認知層面上存在Cognitive Distortion(認知扭曲,即非理性思維模式致對現實的不準確感知),或 Distorted Belief(扭曲的信念)。「就是幫你看客觀、非客觀。但這有一個難處,就是如果你講任何事,他就跟你看客觀、非客觀」。

葉劍青近十年在港推廣另一心理療法——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敘事治療根植於後現代及社會建構理論,從尋求協助者角度理解其經驗,不依賴治療師的專家視角。當抑鬱症患者談及抑鬱的主要「問題故事」時,治療師會帶領當事人回顧過往故事中被忽略的重要情節,如當中與相同處境的友人互相扶持的友誼,讓當事人終能以新角度重寫昔日經驗。
他喜歡進行社區小組治療,因為不同小組成員之間能利用各自的經驗與能力,互相觀察彼此的人生。「在小組裏做一個羣組,(因為)大家的支持、互相的學習與理解、分享來改變。」他說。
他說現時流行說自我關懷與善待自己,但若從社會系統去看,有些創傷與焦慮可以是社會競爭太激烈、太多規範造成。他引用的著名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相信監獄作為現代社會的原型,權力透過形形色色制度在日常生活規範個體,人不知不覺內化了社會規訓,成為服從規訓和指標的人。
「我們說傅柯,就是社會有很多normative(規範性)的東西下來給你。這樣我就不達標、我不行了、我不如忍了,令self(自我形象)很低。」他說。

目前,葉劍青在社區辦治療小組,讓受傷個體透過重述自己的故事線,建立羣體之間對話,互相支援,建立聯繫,再重新找回自己。他指出,他更希望看見由社會建構而成的情緒問題,把個體拉回社羣當中。
IFS亦相信部分創傷可能由社會文化或家族祖先傳承下來,把它命名為Legacy Burden(中譯:家族世代相傳的創傷)。IFS認為,內在部分攜帶的某些情緒、想法、能量、或信念,源自於更早的祖先或社會文化。例如,IFS創辦人曾在著作中提及,美國社會有四種主要繼承自上輩的重擔:種族歧視、父權主義、個人主義與物質主義。美國治療師Deran Young以IFS治療黑人社羣跨代的歷史創傷。IFS相信,當事人在治療師輔助下深入療癒內在部分創傷時,便能卸下並轉化他們長期承襲、背負的重擔。
阿池在訪問尾段說,大家對情緒最大的誤解是,情緒會離開,沒有情緒是永久的。然而現實是創傷依舊藏於內心從沒遠離,他認為大家需要擁抱的是不同面向的自己,然後一起更好地生活。「真正講愛自己,就是愛內在這麼多個不同的自己。整件事是一點也不視他們是一個問題,不當他們是一個病,是很友善、很溫柔的。而那個力量是來自自己的。」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