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專注於長篇小說的寫作,我對三部曲的形式產生了無以言喻的執著。在九十年代末寫的四本書《地圖集》、《繁勝錄》、《夢華錄》和《博物誌》,雖然有共通的創作意念,集合在「V城系列」的名目下,但並不算是一組「四部曲」。最初寫的兩部長篇《雙身》和《體育時期》,也是獨立的,沒有後續發展。
之所以出現三部曲的想法,表面上是因為創作概念增長到一本書不足以承載的規模,必須至少用三部的分量才能覆蓋。三部小說分別建基於三本經典科學著作—宋應星的《天工開物》、霍金的《時間簡史》和達爾文的《物種源始》。由此而成為《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和《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上)之學習年代》三部長篇。三者統稱為「自然史三部曲」。到了第三部,內容顯然已經過度膨脹,要分為上和下。而未寫成的下冊,其實又分裂出好幾個題目,幾乎可以各自成書。在這種無止境的增生之下,我的腦袋終於因為超負荷而崩潰了。第三部(或更多部)終於沒有完成,「自然史」也就戛然而止了。
我以為得了這個教訓,以後便不會再陷入這種沒完沒了的深淵。幾年後,我在拋開心理包袱的情況下寫出了《心》。當時也沒有預期會有後續,只是一心把自己的精神狀態化作小說寫出來而已。沒料到很快又出現了《神》的構思,跟《心》有某些對應之處。在「心」和「神」之後,很自然就是「意」了,也即是接續的《愛妻》所寫的「意識」。連續三年的三部小說,不經意地又形成了系列性,於是我便後設地加上了「精神史三部曲」的名堂。這三部小說都很內在,呈現了某種精神病的狀態,以及隨之而來的真幻不分的曖昧,而且帶有私小說的意味。也許在我的無意識裏面,已經自動地把「三部曲」設置為意識化的模式。
往後的《命子》,在命題上呼應《愛妻》,在主題上也出現了肉體和靈魂的關係的探討,可以視為「精神史三部曲」的延伸。但就內容和形式而言,我會把它視為一部位於轉折點的小品。不過,當時其實沒有任何計劃續寫,所以轉折的說法也是後見之明。在寫作的當下,每一部小說都是因應面前的處境所作出的反應。現實中的每一個變化,也會把下一部作品帶往意想不到的方向。
《後人間喜劇》是一本跟我歷來的風格完全不同的小說。我的目標是把它寫成情節主導的、通俗性的科幻小說。當然我過往的一些習慣還是殘留下來,例如對知識性主題的長篇議論,以及真假不分的敘事越界。書中通過康德哲學和人工智能科技談到「靈魂」的問題,是《命子》中寫笛卡兒的靈魂和肉體二元論的進一步發展。小說中除了有讀取意識的所謂「靈魂書寫」,也有演化出自我意識(靈魂)的人工智能系統康德機器。

去年《後人間喜劇》剛出版,我在文化博物館看到有關香港早期印刷史的展覽,立即萌生寫一部「香港字」小說的念頭。這乍看是個歷史題材,跟之前的科幻題材風馬牛不相及,心裏完全沒有任何加以承接的想法,就好像往一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的跳躍。我開始搜集和閱讀資料,準備新作,過程中意識到自己並不想把它寫成常見的歷史小說的模樣。我無意把歷史當作外在的事實去寫,而是當作讀史者的內心狀態去寫。直覺告訴我,這個讀史者或歷史追尋者,必然是一個當代人,是活在目下時空的香港新一代。「香港字」的故事必須從這個角度去講述,才具有跨時代傳承的意義。
但是,這裏說的「傳承」是什麼意思?只是歷史的、文化的傳承嗎?如果追尋「香港字」的源由,只是通過歷史資料的發掘,那不過是知性層面的事情,也不成其為小說。在古和今兩個時空之間,有什麼可以讓彼此接通?這時候,「靈魂」出來了。在小說構思上,只有通過「靈魂」才能解決敘述上的難題。首先,「香港字」的歷史故事,是通過「字靈」的口說出來的。通過所謂的「降靈會」,女主角賴晨輝在電腦屏幕上和「字靈」展開對話。再者,我當初設想的十九世紀印刷學徒的虛構故事,也可以通過「降靈」的形式向女主角傳遞,藉着她的手重寫出來。雖然聽來帶有神秘主義色彩,但我覺得完全順理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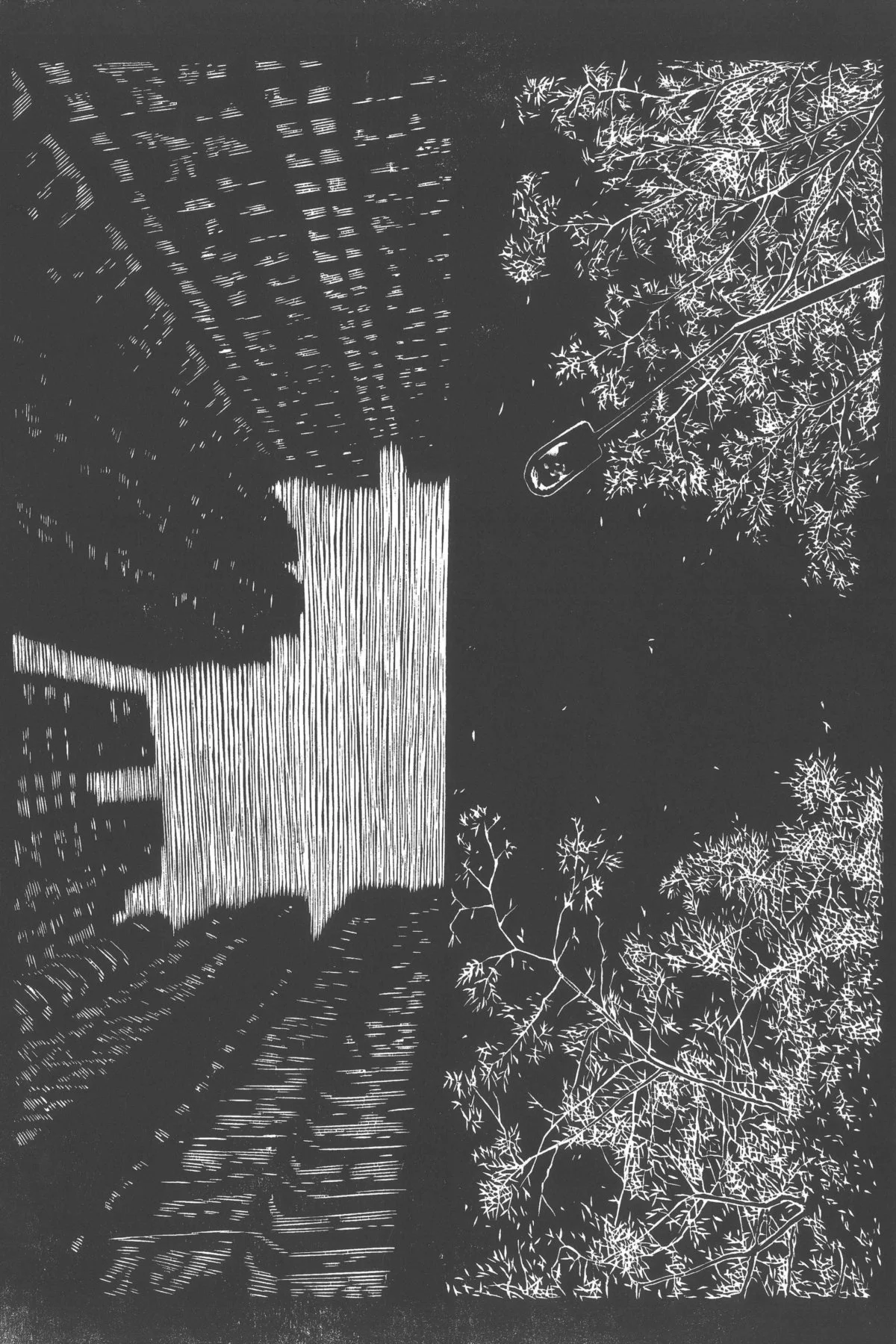
在超自然的理解之外,我們也可以把「靈魂」視為女主角的深層心理或意識世界,並且對「降靈書寫」作出現實的解讀。無論是字靈的絮語,還是十九世紀少年的書信,其實都是賴晨輝內心世界的顯影。這些顯影既是幻象,也是真實。在現實的層面,它們未必真有其事;但在意識的層面,它們具有真實的意義。這意義不是簡單地用精神病便可以解釋和打發的。我在小說中設置了「靈魂治療師」娜美,去幫助女主角和讀者更確切地把握這種精神層面的解讀。
「靈魂」的介入並不是突發性的。當中有榮格的精神分析和河合隼雄的神話學的影響。所以我才說「香港字」的故事不是歷史,而是一則神話。而這則神話除了是集體的,也同時是個人的,屬於女主角自身的。小說中的所有神奇和悲劇元素,也可以用神話去理解。在最出其不意的地方,靈魂再度出現。我於是明白到,《香港字》這本小說是「靈魂三部曲」的第二部,而第三部的靈感,亦已在我的心中醞釀。我深信,「三部曲」的模式,源自意識的深層結構。它是一種靈魂的召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