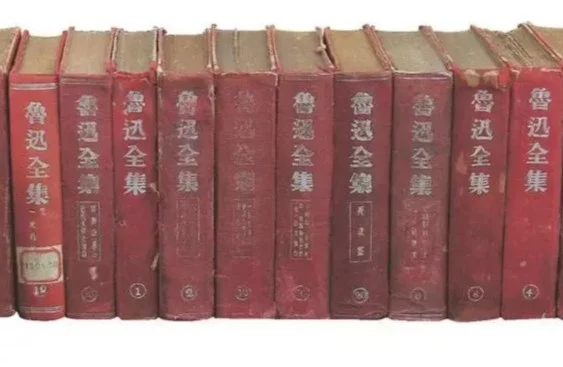學界組織「優質圖書館網絡」創會會長呂志剛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學校圖書館的館藏近年不停刪減,除涉及敏感政治議題或帶政治隱喻的的書籍外,如《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有學校更反映教育局人員巡視館藏後,指名作家魯迅的著作「鼓勵學生上街」,不應在學校的圖書館內。
魯迅曾經被中國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稱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以及「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甚至在魯迅逝世一周年的紀念儀式上,把他稱為與孔子並列的「中國的第一等聖人」。
⚡ 文章目錄
《魯迅全集》也曾是「禁書」
魯迅原名周樹人,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於浙江紹興,二十一歲赴日本學醫,後來棄醫從文,希望以文章救國,辛亥革命後,曾在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職,並在北京大學和女子師範大學等校任教。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因肺結核病逝,終年五十五歲。
周樹人用「魯迅」的筆名在一九一八年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有人認為這部小說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他本人也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魯迅全集》最早出現的是一九三八年20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九五八年推出了10卷本,這個版本在文革時被視為禁書,一九七三年推出過根據一九三八版本進行簡體字重排(兼作出若干修訂)的20卷本,改革開放後,一九八一年,推出了16卷本,到二○○五,又因為「國際和國內的政治格局和思想觀念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而推出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18卷本,這也是目前仍然能在各大網上書店找到的版本。
魯迅作品雖然受到毛澤東和中國官方推崇,但是隨着時代變遷,魯迅地位亦出現相應變化,整體而言,如作家葉德浴所言,是一種「從崇敬到惡用」的過程。魯迅在中國的地位近年大幅下降,最明顯的是,自二○○九年起,魯迅的文章在中國中小學語文教材中大量減少。有人指這是因為魯迅的文章晦澀難懂,有人指這是因為他的文章諷刺性太強,而他「筆下那些被諷刺、被嘲笑的人物似乎又復活了」,當然,也有人指,現在時代不同,提倡魯迅的反抗思想,不利團結。
魯迅與香港 可到上環朝聖百年足跡
魯迅的地位,如果來自官方,那麼,隨着官方針對時代的需要,自然也會出現相應的變化。但是作為文學本身,作品的面向,其實是廣大的讀者。
香港「國史教育中心」二○一九年公布了「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以「吾土吾民,圖強奮進」為主題,結果,由中小學生及小部分公眾人士合共約二萬五千人投票,魯迅以一萬二千多票膺選。「國史教育中心」的榮譽顧問包括劉遵義教授、張信剛教授和李焯芬教授等知名學者。
根據資料,一九二七年,魯迅曾先後三次到訪香港,並連續兩天在上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演講,講題分別是《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的浙江紹興口音很重,由許廣平即時傳譯為粵語。據當時報章報道,兩場演講座無虛設,六百多人把禮堂擠得水泄不通。
魯迅當年演講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位於上環必列者士街51號,小禮堂已改為庇護工場。
魯迅留下許多作品和名言,今天讀來,仍然值得細味,以至如何解讀,則如所有書籍一樣,每個人都可以讀到不同的觀點和立場,然後有不同的想法和領悟。這正是閱讀可貴之處。以下可能是大家從不同地方聽過或看過的魯迅名言,部分讀者可能不知道,有這樣熟悉的一句,原來來自魯迅的詩或雜文,此外,還附有魯迅當年針對民國時期大公報社論的一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大家閱讀的時候,可能喜歡,可能不喜歡,可能因為時代不同而難以明白,但也可能經過一番思考終於拍案叫好,無論如何,這就是魯迅。如有興趣,魯迅的原文,目前不難找,網上可以找到,實體書也還可以訂閱。
魯迅語粹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自題小像》,一九○三年)
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鄉》,一九二一年。)
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華蓋集.雜感》,一九二五年)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忽然想到(五)》,一九二五年。)
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這個與那個.最先與最後》,一九二五年。)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記念劉和珍君》,一九二六年,日本聯合英、美、法、德等八國要求撤除天津大沽口所有防務,五千餘學生北京抗議,結果遭段祺瑞衞隊鎮壓,死47人,傷199人,釀成「三.一八慘案」。劉和珍是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遇害時年僅二十二歲。)
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僅有一點相像。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無花的薔薇之二,一九二六年,寫作背景同上。)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無題》,一九三一年,悼念五名中國左翼作家被槍斃。)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灑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自嘲》,一九三二年。)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悼楊銓》,一九三三年悼念朋友楊銓被暗殺)
奔霆飛焰殲人子,敗井頹垣剩餓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精禽夢覺仍銜石,鬥士誠堅共抗流。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題三義塔,一九三三年。)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無題》,一九三四年)
魯迅名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按:《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是一篇針對《大公報》社論的駁論文,刊於一九三四年,背景為九一八事變三周年,有輿論指出中國人因為失掉了傳統信仰和價值所以失掉了自信力,但魯迅認為這是悲觀的失敗者論,他指對方所謂「中國人失掉自信力」,其實失掉的是「他信力」,而「他信力」失掉了更好,因為這樣才能發展真正的「自信力」,而不是一味發展當權者想一手包辦的「自欺力」。)
從公開的文字上看起來:兩年以前,我們總自誇着「地大物博」,是事實;不久就不再自誇了,只希望着國聯,也是事實;現在是既不誇自己,也不信國聯,改為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了——卻也是事實。
於是有人慨嘆曰: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單據這一點現象而論,自信其實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後來信「國聯」,都沒有相信過「自己」。假使這也算一種「信」,那也只能説中國人曾經有過「他信力」,自從對國聯失望之後,便把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會疑,一個轉身,也許能夠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條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漸玄虛起來了。信「地」和「物」,還是切實的東西,國聯就渺茫,不過這還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賴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虛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時就找不出分明的結果來,它可以令人更長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並非新東西,只不過日見其明顯,籠罩了一切罷了。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這一類的人們,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説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衊。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樑。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