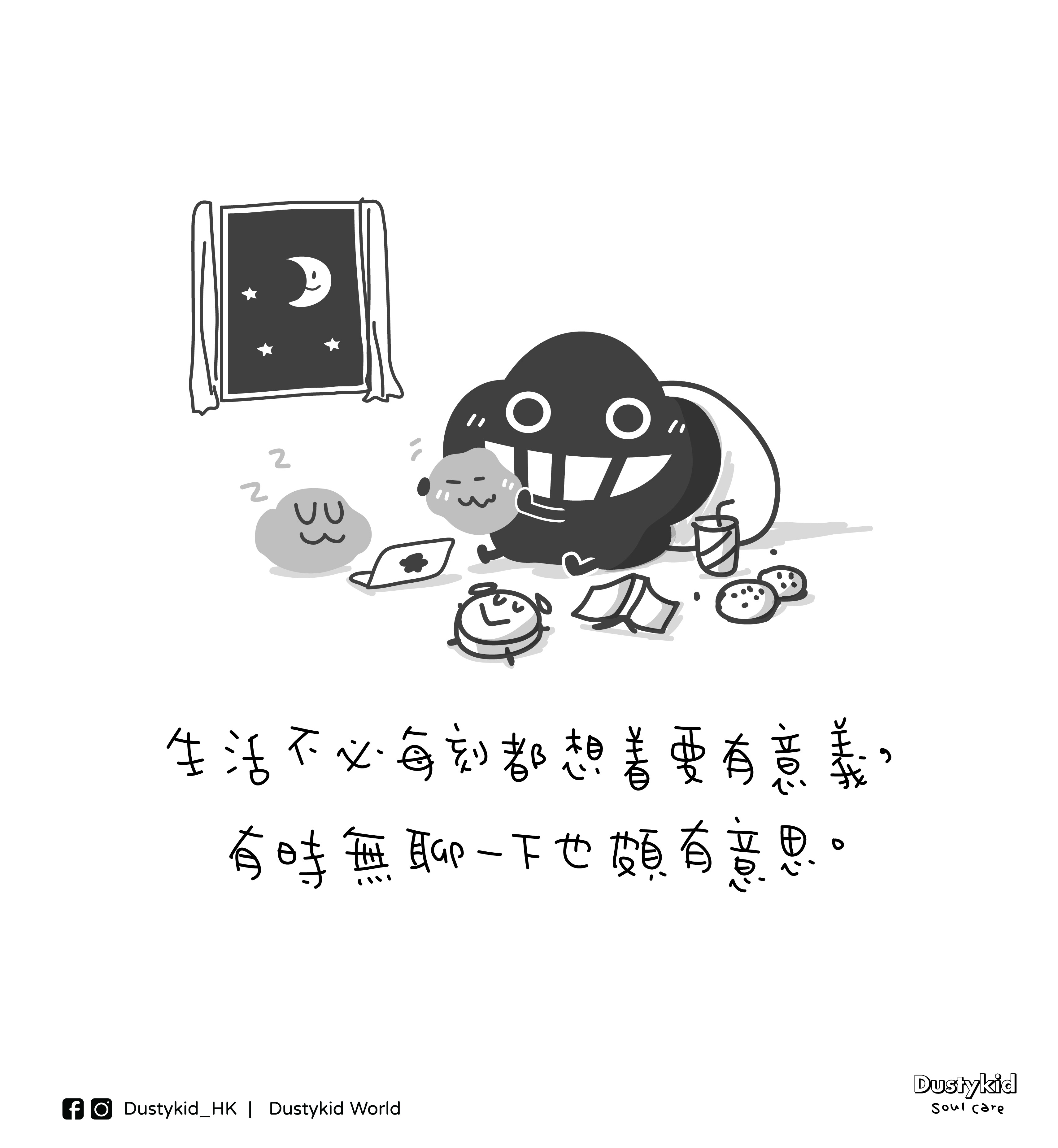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寫馬可.波羅在元大都跟忽必烈交往,向大汗講述他到過的城市。這是小說家的想像。他寫了許多個城市,但所謂看不見的城市,是唯有通過看得見的城市呈現的。借宗教家的說法:道成肉身。易經也說:「聖人立象以盡意。」形而上的道,或者意,必須通過具體的物事才得以顯現。否則就像我們小時候看的電影,片斷了,觀眾就大叫:非洲土人黑夜打烏鴉,什麼都看不見,只是烏有一片。倒過來,也可以因身因象而得道得意。得意豈能忘筌。這所以卡爾維諾寫城市的街道,寫得很仔細,那些各種形象的招牌,鉗子是拔牙店、大杯子是酒館、天秤是雜貨店(香港會令人想到法院,要不是石做的,風來時就搖搖欲墜),然後才揭露隱藏在背後的、看不見的東西:記憶、欲望、恐懼,那些人們隱藏在心裏的東西。
第一個馬可.波羅講述的城市,先描摹了城中六十座白銀圓頂的諸神銅像、鋪鉛石的街道、水晶劇場,以及一頭每朝在塔樓上報曉的金雞,──這些,對旅人來說,大多都耳熟能詳,然後,馬可.波羅觸動大家的記憶,想到九月某一個傍晚,夜漸長,小食攤的彩燈忽爾亮起,而涼臺上傳來女子的呼喊,這時候,旅人會多麼嫉妒那些曾在這裏度過一個晚上的人呢,他們曾經多麼愜意,多麼快樂。他和他,馬可.波羅和忽必烈,長者聽,少者說,兩個人不過出發向東方,走了三天罷了。一個擁有許多看得見的實體的城市;另一個,也有許多,卻是看不見的想像。一個劃定了疆界,長者的祖父,一度奪取了無數的城市,辦法是一路殺戮,但始亂終棄;另一個,從想像出發,不斷繁衍,一個生出另一個,並沒有邊界,而所到之處秋毫無犯,更不佔有。難得這個權力最高無上的長者尊者,一個靼韃人,會有耐性聆聽一些他確乎伸手不及看不見的城市。
我,在冬夜,這麼一個讀者,肯定也跟隨他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看着看着,只感覺茫茫然,迷失在城市之間,再不能辨別,儘管它們有不同的標簽,但這些看得見的城市在這位威尼斯人的講述裏,其實一直在遷移、流動,可以增,可以減,可長可短,而且可以互換。這反而變得並不真實。看得見的,都只是海市蜃樓的「現象」。而真正快樂的城市,只出現過一次,是芸芸「隱匿的城市」之一,在臨末的第九章,好像說出來,曝了光,就不再快樂了。對了,我要尋找的,正是這麼一個罕有的快樂之城。我甚至懷疑,這才是馬可.波羅引領忽必烈迂迴曲折地要到達的一個城市。
快樂要不是禁忌,也是珍密,不可張揚喧嘩?於是,一開始,在這個終於出現的城市裏,我們看到的,仍是種種不快樂的人事,「生活並不快樂」,這城市起首這樣說,我不懂義大利文,英譯是In Raissa, life is not happy,
一個中譯本是「在瑞薩,生活並不快樂」,另一個譯本則是「萊薩的生活並不幸福」,快樂和幸福,畢竟是不同的層次。快樂,會因為某些物事的逗引而開懷,但「樂」,一如快感,同樣消失得「快」。幸福則是一種較恆久的精神狀態,對生活各個方面感到愜意。幸福的人恆常感覺快樂;但不幸福的人,也可以有短暫的快樂,像被逐出城市的低端者忽爾獲得延期居留;一個口舌便給的貪官倒台,我們也會樂了好一陣,雖然防止貪腐的機制並沒有建立。至於快感,那是更低層次也更短暫的感官滿足,而且我們知道,有些快感是有害的,像毒品。
馬可.波羅告訴忽必烈在這城市生活的人,是這樣那樣的不快樂,然後,說話一轉,他說到隱匿在背後的,其實也有種種毫不起眼的快樂,從一個孩子的笑開始,這孩子看到窗外一隻狗,為了吃石匠掉下的玉米餅而跳上牛棚,他天真地笑了;石匠呢,則向一位年輕的女侍口花花地調笑。……這是生活的常態,生活原本就很簡單,但也可以有實在、單純的快樂。馬可.波羅引一位哲學家的話:在萊薩,哀愁之城,有一條看不見的線,把這一個生命跟那一個生命連接起來,瞬即又再分開,然後在移動的各點之間延伸,勾畫出新穎、快速的圖案,所以,無論任何時刻,一座不快樂的城市,總包含另一座快樂的城市。問題在你是否看得見,你能否讓這些卑微的快樂「被看見」。不是說看不見的東西得借助具體的看得見的東西呈現麼?而快樂與不快樂彼此牽連、辯證。
這些之前,馬可.波羅說了許多城市,忽必烈說有一個城市他一直沒有說:威尼斯。大汗堅持要他說說他自己的故事。波羅回答,他說的,正是威尼斯。他解釋記憶裏的形象一旦被詞語固定下來,就給刪掉了;他只怕當他提及威尼斯,馬上就完全失去她了。而他在描述各個看得見的城市的時候,已經一點一滴再看不見她了。
書末,忽必烈與波羅談話,指出地獄不在將來,它根本就此時此地「存在」,我們每天生活在其中。越獄,有兩種方法,一是接受它,成為它的一部份,這是最多人的選擇,看看此時此地的我城,就是這樣。這樣的城市,不單看不見,而是失去了,成為記憶。另一種方法,則是在地獄裏搜尋,並且學習辨認,什麼不是地獄,馬可.波羅含蓄地對統治者說:讓它們存活,給它們空間。換言之,大王啊大王,使不快樂的人,快樂起來;看不見的城市,讓大家可以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