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詩人也斯曾經提問:「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
香港歷史難說,因殖民時代志在今朝的思想植根人心,歷史檔案零碎乏人整理。今日談本土如入迷宮,不知從哪裡去,從哪裡來。雨傘運動後,一位 70 後抱恙翻看舊檔案,一切由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前途問題說起。
一個以「世代懺悔錄」為名的網上專頁,主理人叫李嘉文,生於1978年,其時香港前途問題仍未搬上政治的議程中,然而在他成長的日子裡,卻處處佈滿了80年代的痕跡。
「為何香港弄至今天田地?」是李嘉文追問的核心問題。一個不解的疑惑,促使他拼命翻看一堆過去的資料,80年代是起點,因為那是香港走到如今面貌的關鍵時期。
⚡ 文章目錄
業餘考古 拒絕失憶
李嘉文一開始便表明,自己不是從事嚴謹的歷史研究工作者,於是他自稱「業餘考古」。「我本來只想追溯,太年輕時沒有關心社會,其實也只是自己的閱讀與懺悔。那段歷史,也是我自己成長的歷史,現在睇返當時的報紙雜誌,都覺得好離譜。」沒有甚麼機密的檔案,他只是默默在整理一大堆曾發佈於 80 年代的公開資料,愈看愈不甘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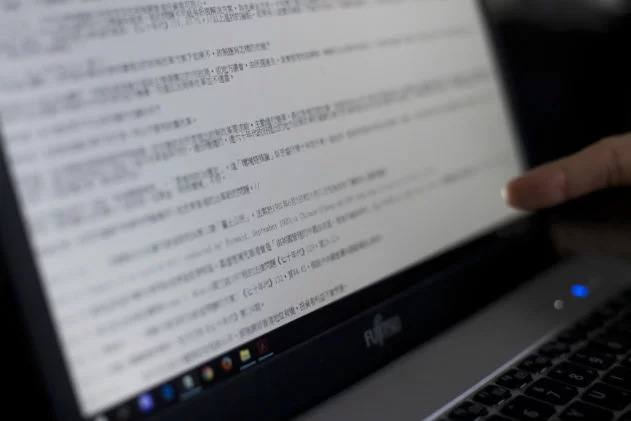
看到一些同代人對於年輕世代的指罵,也讓他忿忿不平︰「很多人指責年輕人搞事,其實做長輩有更大責任。我成長經歷前途談判、主權移交,見證中共走數幾十年,整代人無奈接受,不但無奮力抵抗,更陷於失憶,持續受騙。」
這解釋了為何說是世代懺悔,屬於他那一代人的印記,如同羅大佑在〈未來的主人翁〉一曲中寫︰「我們改變的世界將是她們的未來」,80年代曾改變的世界,她們的未來,便成了今天香港景況的寫照。
青年躁動 上一代做了什麼
資料整理的工作,大約從 2016 開始,李嘉文的身體有長期病,做起上來頗吃力,狀態好的時候,可以看上三、四個小時的資料,有時在網上瀏覽,有時走到中大的圖書館,翻看當年的報章雜誌︰「7、80年代的《百姓》、《廣角鏡》與《鏡報》等,逐份逐份去scan目錄和內文。」

沒有報酬,甚至可能沒有掌聲,為何堅持去做?也許在李嘉文眼中,這不過是個基本公民應該去做的事︰「以佛教用語來說是身土不二,這是對於自己地方有一份很基本的感情,為了自己及周圍的下一代,無理由咁易放棄,因為那是屋企。」
2015年,是他任職宣教師的最後日子。在教堂工作的五年間,他接觸到形形式式的年輕人,從而認識他們的世界︰「那時工作,看到初中生讀書讀到胃痛,又常常不回來教會,我去嘗試了解,唔係因為佢哋懶,而是新高中學制及各樣的教育改革將佢地搞到咁。」他去探尋年輕世代所面對的困局,發覺自己作為更早一代的人,原來拿取了很多的機會︰「現在的問題不只是無樓住,而是行業無出路,連講句真話都咁難。」
眼前像是死局,讓年輕一代看不見希望。李嘉文說,這對他的衝擊很大︰「原來佢哋個世界係咁。」而這樣的世界,他認為上一代有份製造出來,而身邊的朋友,又在指責年輕人如何不堪的時候,李嘉文覺得,這樣不公道。
這種不公道,也體現了在抗爭的場域裡。
「我記得 928 那天傳會出動橡膠子彈,那些作為頭面人物及社會賢達的大學校長,看似很擔心學生,但只叫人退,卻沒有去譴責政權。」以致後來年輕一輩的躁動與激進不斷遭到批評,李嘉文覺得,「好像跟現在的年代脫了節,活了在不同的世界。他們給我感覺是活在 80 年代或 90 年代,那個仍然是在玩共識政治,你好我好,信任政府的年代。」
「你記不記得 2009-2010年左右反高鐵的時候,有人說要喚醒別人去關心社會?」他問記者,話鋒一轉︰「原來這些意識早在 80 年代已經有」。他尤其關心當年香港人的參與,卻無奈地發現,香港人的聲音只能遊走在夾縫中,一直被代表。
兩雙腳的「三腳凳」
港人聲音「被代表」
根據《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在1982年中間,曾有三項較大型的民意調查,顯示出香港人對於前途問題的意願︰「(一)香港革新會,委託香港市場研究社,在三月用電話共訪問一千人,調查結果百分之九十三希望維持現狀,繼續由英國統治。(二)浸會書院在五月以郵遞方式,訪問共僱用超過十萬人的五百四十五間機構,調查結果顯示,有八成五機構希望維持現狀,繼續由英國統治三十至五十年,但主權則可回歸中國。(三)香港觀察社委託香港市場研究社,五、六月間面對面訪問一千名十五至六十歲香港居民,八成七受訪者接受由英國繼續管治。」

結果,「變咗做大部分聲音係支持民主回歸」。當時有一批「民主回歸論」的聲音,同意香港主權歸屬中國,但要實行民主的港人治港方式。李嘉文覺得,當時香港人的聲音一直被代表,在中英談判的過程中,只有兩個大國的身影,英方曾經提議香港人作為第三方一起參與,如是有了「三腳凳」的說法,卻受到中方的反對。1984 年,鄧小平曾跟鍾士元、利國偉、鄧蓮如說︰「過去所謂三腳凳,沒有三腳,只有兩腳。」看到三腳凳的那一段歷史,李嘉文悲從中來,在別人眼中,香港人是 invisible。
李嘉文續說,當年中方搬出了「港人治港」的方向後,導致本地壓力團體的聲音消於無形中,「這是一個魔咒。」

二十多年過去,他想起 8964 之後,曾有很多人誓神劈願說要關心社會,「當年有 100 萬人上街,如果真有十分一人覺醒了,從公民及政治意識上的幼稚園,今天都應該是中學畢業吧?但今天的社會卻是更加傾斜。」他慨嘆︰「我們那代人有很多資源,但卻未曾令年輕人可以好過一點,我們甚至做得不夠。」
在縱橫交錯的資料裡梳理歷史,歷史作為一種見證,他看見一代人對於另一代人在歷史上留下來的影響,作為同代人,他覺得需要懺悔。雨傘運動時候,曾有大台背景印着「命運自主」的字眼,走到今天,也曾出現形形式式自主自決的聲音,香港的故事,在斑駁複雜的脈絡裡,難以言說,但非不能言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