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跟一個老師傅出更巡邏,那時,他才剛從警察學堂畢業。換上藍色制服,要先確保配件整齊,他記得學堂長官講過,警察是紀律部隊,制服整齊就是體現紀律。
老師傅膊頭上有一條柴,亦即在任內無功無過,服務18年後自動獲象徵式晉升,人稱「傷心柴」。作為後輩,他站得筆直,等候老師傅下令出發。他卻招招手,讓他過來坐下。
「記住,當差的,犯第一個錯,就要立即認,立即解決。如果你之後用第二三四個錯,來掩飾第一個錯,這個錯誤就會變得好大。」他一時未能反應過來,他再說:「假如你抄錯市民資料,只需要道歉,通知指揮官,然後嘗試找回正確資料。但是,如果你擅自更改筆記簿的記錄,甚至作假資料,將來別人發現資料不對,你就是妨礙司法公正,萬劫不復。」
「這個道理,我一世受用。」陳先生說(化名)。
⚡ 文章目錄
沒有良知的公務員 不配服務市民
「林鄭月娥還有其他高層,可能捧住鐵飯碗太耐,曾經作為一個PC的我已經懂得的道理,他們忘記得一乾二淨。」做過七年警察,期間入過PTU,也就是着綠衫的防暴警察。如今,他是一名文職公務員。
政府幾時開始出錯?就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法案直上大會那一刻。「在香港推一條草案,是有標準程序。」的確,公務員最懂得講程序。為什麼公眾諮詢期只得短短二十日?為什麼草案在法案委員會遇上阻攔,可以跳過直上大會?「政府有沒有思考,為什麼草案會遇上問題?正正是因為爭議太大。」林鄭說,一地兩檢都好有爭議,但是立法會都通過到。「這個方法,用一次得,兩次得,她就以為用一百次都得。」
69百萬人遊行、616二百萬人遊行,之後還有許多次遊行集會,陳先生一直以個人名義出席。721元朗「恐襲」,各大新聞及社交網站直播鄉黑勾結,他在家中看得怒火中燒,得知白衣人會去不同地鐵站搞事,他顧不上危險也要去附近地鐵站現場。放眼望去,整個車站都是義載司機,他知道,許多香港人與他同一陣線。
那一晚,他徹夜未眠,翌日上班,踏着沉重又浮沉的腳步,茫然不知返工所為何事。「雖然我的服務對象是市民,但是一個如此不堪的政府,為什麼我還要仆心仆命在其中工作?到底我是為誰服務?」工作上,他一直表現專業,個人內心,卻是失望透。「就算我不想承認,林鄭月娥都是我的上司。然而,她也是服務香港人的公僕,卻放棄聆聽香港人的聲音,十八萬公務員還能如何自處?」

陳先生認為,在工作上保持中立,是公務員一直堅守的原則。然而,作為公務員,還需要有足夠的同理心,以知識、法例和各種技巧服務市民。作為一個普通香港市民,他認為在721之後,整件事已經不能回頭,已經超越良知底線。如果有人到今時今日,眼見市民遭受無差別攻擊都依然支持警隊和政府沒有做錯,他認為這種同事不配服務市民。「因為他的良知、是非黑白出了問題。一個只懂跟程序工作的公務員,如何在每一日的工作之中,切身處地體會市民的感受和需要?」
警隊名言:識人好過識字 打電話好過打字
老一輩的同事知道他曾當差,私底下問過他:「警隊為何做得咁核突?」回想當年,身邊人都支持他投考警隊。一來,他想知道警隊是一個怎樣的組織,二來,就是現實地想賺取高人工養家。入職警隊之前,陳先生已經有其他工作經驗,即使經歷警隊文化洗禮,他依然能夠保持自我。然而,其他「白紙一張」的同僚,很容易就會受警隊文化影響。警員向上升一級就是三柴,亦即沙展,是一個小隊長,需要管理幾個警員,已經算是「管理層」。
假如從學堂畢業就是見習督察,亦即白衫膊頭一粒花,一出來就是一個小隊的指揮官。一個分區警署,巡邏通常分四更,一更一隊人,視乎環頭大小,一隊人少則十多二十人,多則可達四五十人。督察,就是一隊巡邏隊的指揮官。
「有職級的話,每個人對住你都阿sir前阿dam後。」從此,就會品嚐到何謂權力,何謂階級。然而,即使高級如督察,也需要沙展和警員的支持,尤其是從學堂畢業就做督察的一批,藍衫警員在前線一定更有經驗。小至處理一宗糾紛,大至處理打劫案,究竟拘捕時有沒有足夠證據,是否跟足程序,對方投訴的話,一切都是由指揮官負責。「所謂齊上齊落,就是一隊人要保障對方安全。就算你再不喜歡下面班人,都要與他們打成一片,不然他們在日常工作好容易可以跣你一鑊。」
警隊內有一句名言:「識人好過識字,打電話好過打字。」這句說話,說明人事關係有多重要。報紙經常報導有警察為了控告犯人,不惜全隊人妨礙司法公正,下場就是「調轉頭坐」,從執法者變成犯人。
指揮官失控 下屬難以直諫
兩個月以來,警方濫用武力的情況一次比一次嚴重。沒有配戴委任證、沒有展示警員編號、水平發射各種子彈、疑似改裝警棍、刻意攻擊記者……還有許多許多,不能盡錄。既然指揮官的角色是要確保同僚合法行事,何以會發生以上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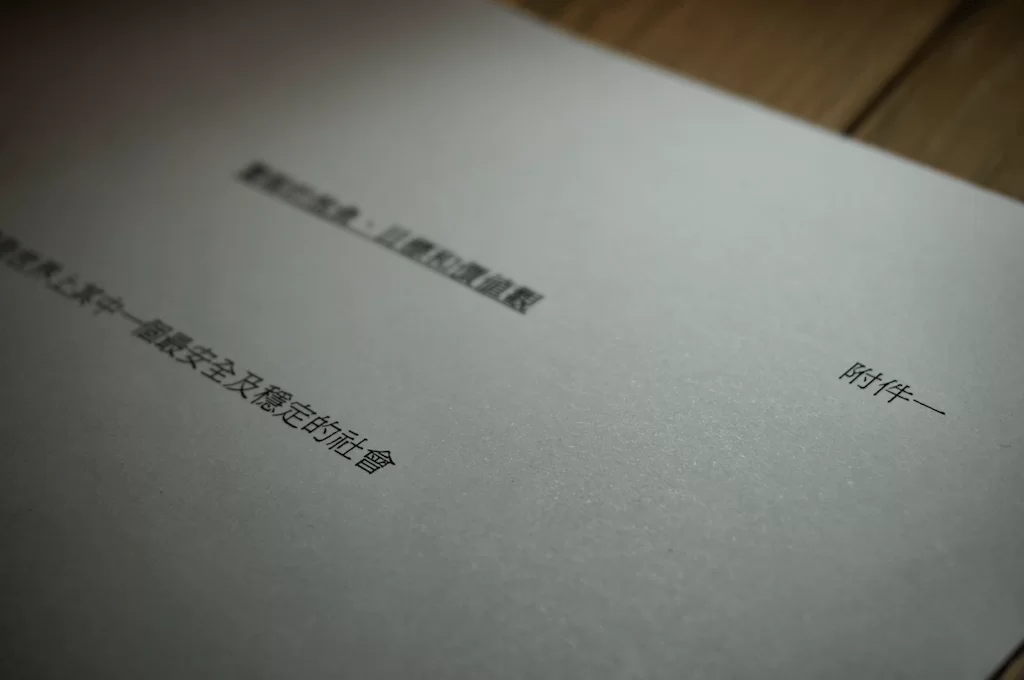
「我沒有經歷過,實在不知道,唯一肯定就是指揮官負責落命令。」前線警員一直以來都是做最辛苦的工作,抄個牌都要被人問候母親,面對壓力的訓練反而被白衫多。陳先生舉例,無論是元朗還是葵涌的衝突,都見到有柴有花的沙展和督察失控,負責拉住他們的通常是最低級的警員。「當督察要與警員一齊落場,站在同一位置,做同一行動,受壓能力反而最低,因為警員日日都受緊,佢哋冇。」
在學堂,步操訓練是重要一環,不止練體能,還要訓練警察面對高壓的情緒智商,因為一個人出錯,全隊就會一齊錯。正如一個指揮官對記者鏡頭舉中指,就等於整個警隊向市民舉中指。「我覺得自己以前堅守的原則和信念已經消失,我不知道警隊將來可以如何教導學堂的警員。」
身在前線難以獨立思考 高層命令有錯亦只能照做
陳先生記得,以前做錯事,一定要寫報告解釋。假如警棍要由上而下揮出去,警員要有合理解釋,自己或市民如何受到生命威脅。「情況混亂不是一個合理解釋,警察受過足夠訓練,決定是否使用致命武力。」例如在射擊訓練,警員面前會出現各種影像,有時是一個持槍的犯人,也可以是一個拿着雨傘的示威者。「如果對方只是拎住支花或雨傘,你開槍就是fail。」
衝突之中,常見指揮官在負責發射子彈的警員身後落命令。「如果我是伙記,我一定會好驚。我的每一個行動都有高清鏡頭影住,就算沒有警員編號,頭盔上都有編號,翻查記錄,一定會知道是誰平射,是誰headshot。」陳先生說,每一個行為,日後都有可能要上法庭解釋。問題是,前線警察有沒有意識要保命?或是說,有沒有膽量?每一次行動之後,伙記都要在筆記簿做記錄。「你照直寫,上級會覺得你玩嘢,會做你,你在隊內會俾人杯葛。如果你不幸身處一隊急功近利的小隊,你可以如何生存?」
做過兩年防暴警察,陳先生對於沙田新城市一役表示難以理解。「防暴從來都是用陣型驅散人羣,而不是用武器,更不可能衝出去打人,因為陣型一散,其他伙記會受傷。」他坦言,新城市廣場並不適合打陣型戰,警方不熟地形,襲擊可以從四方八面而來,他直言指揮官「叫伙記入去,簡直是推伙記去死。」

記者問,假如他現時身在前線,會有何感受?「被人打就一定會嬲,但是我更加嬲的,一定是點解上頭要擺我去一個如此危險的地方?」問題是,人在前線,在剎那間只能思考眼前的安全及行動是否合法,並沒有空間思考行動的最終目的。「事後睇返電視,可能會嬲到仆街,但是又不能出聲。」
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香港法治從此死去
過去兩個星期,無論是學術界、商界、政界,都有聲音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引來警隊強烈反彈,就連政務司司長疑似代警隊向市民道歉,都被逼「撤回」講法。四個警察協會去信林鄭反對成立獨立調委員會,認為此舉對警隊不公。陳先生不敢苟同,反指「如果未能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香港法治就會從此死去。」
由執法到調查再到律政司提出檢控,是一環扣一環。警察是最前的一環,負責執法,決定提出檢控的先後次序,再向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為何示威者如此快要提堂?為什麼沒有警察被查?律政司不能夠說,警方查夠示威者未,幾時先查警察?」如果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就會欠缺公信,沒有人去定義警方武力是否合理,「到最後不了了之,香港法治就宣告死亡。」
直至現在,陳先生還是不會叫警察做黑警。他有朋友在警隊工作,大家能夠保持友誼至今,是因為他知道對方不是黑警。「我相信,獨立調查可以抽出警隊的黑,這才可以還我朋友們一個清白。」
用行動告訴香港人:我哋唔使驚
明天就是公務員集會,陳先生表明一定會出席。「怎會不擔心?但是良知令我瞓唔着,良知令我行出來。」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有份參與的聲明呼籲,公務員「勿受有心人誤導,被推向前線」,集會是「以少數人的立場訛稱代表整個公務員隊伍的做法」,陳先生認為言論相當反智。
「幾千人投考公務員,只會錄取幾十人,遴選委員會的運作相當嚴謹。經過多重選拔組成的公務員團隊,怎會如此容易會被誤導?」他直言,五位召集人講得相當清楚,公務員是以個人身分出席集會,此乃公務員的權利。「別說集會騎劫公務員團隊,不出席明天集會的公務員,亦可以個人名義舉行其他遊行或集會,明天的出席人數自會說明一切。」
陳先生坦言十分欣賞五位召集人,押上自己的仕途,只為提供一個平台,讓大家表達良知。「讓所有公務員,可以作為一個香港人,表達自己的不滿。」眼下,最大的問題反而是白色恐怖。沒有人知道有幾多人會出來,沒有人知道出來之後有沒有後果。陳先生相信,人夠多,就能夠抵抗罩在頭上的白色恐怖。
如果有九成公務員出來,要怕的反而是剩下那一成。「全香港打工仔都一樣,香港人應該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和權利。我希望優秀的公務員團隊,可以用行動告訴香港人,我哋唔使驚,公務員都是同路人,都是香港人,我哋都愛香港。」
明天,晚上七時至九時,中環遮打花園,「公僕仝人,與民同行。」







